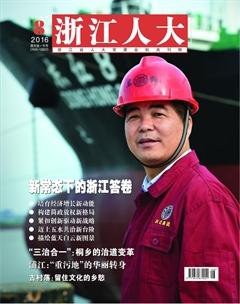古村落:留住文化的鄉(xiāng)愁
黃平
浙江是古村落保有數(shù)量較多的省份之一。業(yè)界普遍認為,保護古村落,比保護故宮還難,難在歷史的脈絡(luò)難尋,難在讓古建筑宜居,難在讓古村落真正活起來。但這樣難的事情,浙江省已經(jīng)做了4年。
2015年7月的一天,一輛黑色商務(wù)車沖開重重雨幕,從浙江農(nóng)林大學(xué)出發(fā),向著130多公里開外的淳安縣上西村疾馳而去。浙江農(nóng)林大學(xué)教授王長金、副教授彭庭松,帶著一批碩士在讀研究生,就此拉開了《千村故事》“五個一”行動計劃暑期調(diào)研活動的序幕。
村落,是傳統(tǒng)中國的基石。歷史文化村落,更是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明的載體和源頭、現(xiàn)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chǎn)。
如何讓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chǎn)重放光彩?浙江率先在全省范圍內(nèi)開展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和利用工作。從2013年起,每年啟動43個重點村和217個一般村,截至目前已啟動172個重點村、868個一般村的保護利用項目,各級投入資金達30億元。浙江農(nóng)林大學(xué)團隊的《千村故事》調(diào)研,僅是古村落保護行動中的一個縮影。
保護第一,利用第二
2016年5月25日,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等7部門聯(lián)合公布2016年列入中央財政支持范圍的中國傳統(tǒng)村落名單,我省有61個村落位列其中。至此,浙江全省共有176個村列入中國傳統(tǒng)村落名錄,傳統(tǒng)村落保有數(shù)量在全國居第3位。
一部村莊史,有時可以反映一部中國史。專家介紹說,浙江的歷史文化村落,大多形成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唐代安史之亂以及南宋遷都杭州,導(dǎo)致大量人口遷徙浙江。一次次的人口遷移,村莊規(guī)模逐漸形成,宗教、習俗、建筑設(shè)施等歷史文化“胎記”也漸漸清晰。
“對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始終是第一位的,利用是第二位的。”2016年6月初,浙江省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工作專題現(xiàn)場會在臺州召開。省委副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輝忠表示,歷史文化村落的歷史性和藝術(shù)性遠遠超過使用價值。推進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必須“義”字當頭,絕不能功利性地看問題、打算盤,把老祖宗的東西拿出來“變現(xiàn)”,這是衡量保護利用工作的“一桿秤”。
有了這桿秤,“要不要保護、要不要搶救”已無需爭議,關(guān)鍵是“怎么保護、如何搶救”。
“義”字當頭,首先體現(xiàn)在如何規(guī)劃。記者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與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同的是,浙江在歷史文化村落的規(guī)劃設(shè)計上,不求快,反求“慢”,目的是讓古村落保護精一點、細一點,避免“千村一面”。
早在全面開展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之初,浙江就出臺《關(guān)于加強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的若干意見》,將歷史文化村落分為“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態(tài)村落”和“民俗風情村落”3種主要類型,旨在因地制宜,根據(jù)不同村莊特點類型采取不同的保護利用方式,充分展現(xiàn)村莊個性。
在浙南山區(qū)的麗水市慶元縣,有一個“自然生態(tài)村落”,因村后山形如半月,村前舉溪曲似銀鉤,取名月山村。但最近數(shù)十年的村莊建設(shè),導(dǎo)致大部分古民居遭到破壞。在深入調(diào)研基礎(chǔ)上,規(guī)劃設(shè)計師著力修復(fù)“月宮意象”,將梯田、松竹、科舉文化等融入其中,重現(xiàn)月山村意象。
有了規(guī)劃,落地實施同樣重要。走進浙江的一些歷史文化村落,幾乎看不到大拆大建。為盡量保持古建筑的歷史原貌,我省以“慢工出細活”的工匠精神,始終堅守兩條底線:不扒房、只修復(fù),就地取材,保留村莊的時間痕跡;大樹不砍、河塘不填,適度調(diào)整,敬畏村莊的原有肌理。
4年來,浙江歷史文化村落通過“接筋續(xù)骨、理氣回神、養(yǎng)血生津”,一批破舊損毀的古建筑得到搶救性修復(fù),一批瀕臨失傳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和文化符號得到挽救,一批毀損嚴重的古村落重煥生機。
“凡納入省級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重點村和一般村的,古建筑及其他歷史遺存得以大量修繕、修復(fù)。在調(diào)查的124個村中,已經(jīng)修復(fù)的古建筑共1585處、324502.8平方米,分別占問卷村古建筑總量和建筑面積總量的18.2%和28.9%,其中,古民居修復(fù)1266處、209784平方米,古祠堂修復(fù)84處、28420平方米,其他古建筑235處、86298.8平方米。”浙江農(nóng)林大學(xué)研究團隊最終形成的《浙江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與持續(xù)發(fā)展調(diào)研報告》如此寫道。
見物見人見生活
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利用,既要修繕外在的“筋骨肉”,更要傳承內(nèi)在的“精氣神”,保護絕非原封不動,最好的保護是實現(xiàn)居民與建筑的良性互動,真正把歷史文化村落建成鄉(xiāng)土文化遺產(chǎn)的博物館、鄉(xiāng)愁記憶的百科全書、古今文明有機融合的美麗鄉(xiāng)村。
臺州市黃巖區(qū)潮濟村曾是水道交通和山區(qū)平原貨物中轉(zhuǎn)地,商賈云集,貨貿(mào)繁榮。20世紀60年代,長潭水庫大壩合龍斷航,基于水運的潮濟古村開始衰落。2013年,潮濟村以修舊如舊的理念,開展老街修繕工作,并延續(xù)了村里的“老底子”傳統(tǒng)。
2014年底,幾度滄桑的潮濟老街重新開街。60歲的蔡莫杰老人重拾手藝,在老街賣起了棕棚床;屠文君開了家“老屠油漆”店,生意興隆。平水廟里,頭發(fā)花白的老人坐在臺下,聽起戲來神情入迷。在這里,歷史文化村落首先是“活著”的人居環(huán)境,生活在其中的村民與來來往往的游客融為一起,再現(xiàn)昔日繁華。
“傳統(tǒng)村落是物質(zhì)與非物質(zhì)文化‘雙遺產(chǎn),具有物質(zhì)與人文‘雙形態(tài),失去了原住民及其生產(chǎn)生活方式,傳統(tǒng)村落就失去了靈魂。”浙江省古建筑設(shè)計研究院院長黃滋認為,村民是村莊的主體,文化是村莊的靈魂。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利用應(yīng)注重“活態(tài)保護”,見物、見人、見生活,激勵村民自覺參與,激發(fā)村莊內(nèi)生動力。
在蘭溪市諸葛八卦村,有明清古建筑200多幢。為了保護利用這些文化遺產(chǎn),村里把毀壞文物的處罰措施寫進村規(guī)民約,規(guī)定“對毀壞或破壞文物行為的農(nóng)戶,將中止一切福利待遇”。村規(guī)實施后成效顯著,不僅不破壞,村民還自發(fā)捐款籌措資金用于保護文物建筑。
仙居縣高遷村規(guī)劃以村里的歷史與現(xiàn)實為出發(fā)點,堅持保護與發(fā)展并舉,通過修繕保護高遷村古建筑群、傳承和弘揚耕讀文化以及無骨花燈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再現(xiàn)高遷古村落“三百年古村,耕讀立家”的特色風貌。
當然,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利用,繞不開一個敏感環(huán)節(jié),就是如何處理好保護與利用的關(guān)系。我省在保護優(yōu)先的前提下,堅持“有序發(fā)展、特色發(fā)展、融合發(fā)展”,力求“保護促利用、利用強保護”。
桐廬縣深澳村是一座建于南宋后期的江南古村,村里的徽派建筑群保存相對完好,但長年無人問津,空房閑置。最近幾年,深澳村變了:一些閑置的老房子變身咖啡廳,“民宿”一詞也開始出現(xiàn)在這個小山村。來自杭州的退休老人朱鎮(zhèn)華,在嶺源村租下一幢農(nóng)房,一租就是20年,成了這里的“村民”。
城里人回流尋找鄉(xiāng)愁,讓這個寂寞的小山村逐漸活了起來,也讓村民們萌生了用民宿創(chuàng)收的想法。
村支書申屠勇軍告訴記者,深澳村與眾不同的做法是,沒有盲目引進開發(fā)商“整村承包”,沒有變相“驅(qū)趕”原村民,也沒有讓社會資本一方主導(dǎo)、一股獨大,而是以保護利用歷史文化村落為載體,成立了“古村落管理委員會”,對閑置古建筑實行“統(tǒng)一流轉(zhuǎn)、統(tǒng)一租賃、統(tǒng)一出租”,政府、村集體、居民、社會資本共同參與。
如今的深澳,整個村成為4A級景區(qū)、全國美麗鄉(xiāng)村樣板村,休閑旅游方興未艾。2015年,桐廬全縣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達22504元,鄉(xiāng)村旅游接待516.4萬人次,同比增長99.2%。
探索建立長效機制
如果把歷史文化村落看成一個有機的生命體,那么更新是其必然現(xiàn)象。古村落的保護修復(fù)也不是“畢其功于一役”。
截至2015年末,我省確認的歷史文化村落共有1237個,但目前這些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現(xiàn)狀卻千差萬別。有的村落全村旅游收入已經(jīng)達到1億元,也有的村落3年建設(shè)期滿績效評估不及格。
對于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資金缺口依然是困難所在。許多古村落位置偏遠,歷史建筑修復(fù)、傳統(tǒng)技藝復(fù)興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重點村700萬元、一般村300萬元或30萬元的標準,對于古村落整體保護利用需求來說,是杯水車薪。然而,公共財政不可能包攬一切。
浙江農(nóng)林大學(xué)中國農(nóng)民發(fā)展研究中華常務(wù)副主任王景新教授呼吁,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亟須多元投入機制,調(diào)動社會組織和村莊內(nèi)生動力,建立長效投入和管護模式,“村民對自己居住的村莊有天然的感情,他們對自己投入的事業(yè)是關(guān)心的”。
據(jù)了解,我省已經(jīng)明確急需補齊的短板,主要包括7個方面:健全項目立項管理機制,補齊項目庫缺失短板;健全項目規(guī)劃引領(lǐng)機制,補齊規(guī)劃短板;健全項目保護機制,補齊修復(fù)短板;完善項目組織領(lǐng)導(dǎo)模式,補齊組織短板;探索完善利用機制,補齊發(fā)展短板;健全項目環(huán)境整治機制,補齊生態(tài)短板;健全項目政策創(chuàng)新機制,補齊要素短板。
為盡快補齊短板,浙江各地正在創(chuàng)新實踐,探索長效投入和管護模式。
臺州市實施上下聯(lián)動、合力共建的工作機制,“一縣一高校”“一地一智囊”。當?shù)匾M同濟大學(xué)師生團隊,對精品線路的鄉(xiāng)土化設(shè)計、鄉(xiāng)村功能開發(fā)與水源地保護、歷史文化價值挖掘等方面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劃指導(dǎo)。楊貴慶教授常年把團隊駐扎在臺州市黃巖區(qū),以“做產(chǎn)品、出精品”為理念,為保護歷史文化村落把脈問診。區(qū)委書記還與教授建立了微信工作群,發(fā)現(xiàn)問題立刻通過微信拍圖反映求解,實現(xiàn)問題“秒處理”。
溫州市引導(dǎo)工商資本、國企、熱心人士等多種主體,采取募捐、投資、合作等方式參與保護利用歷史文化村落。
義烏市出臺以獎代補政策,對單位和個人自籌資金維修古建筑予以獎勵,獎勵額度不超過工程審計總價的60%。
松陽縣則以歷史文化村落為底本,依托鄉(xiāng)土民俗文化風情,以攝影創(chuàng)作為媒介,植入生態(tài)農(nóng)業(yè)、休閑度假、文化旅游等新業(yè)態(tài),推動一產(chǎn)三產(chǎn)融合發(fā)展。
天臺縣張思村通過引進鄉(xiāng)賢力量,借勢發(fā)力,確立民營和國有資本進入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的門檻,共建美麗家園。如今規(guī)劃在建的江南園林和古村博物館,均由當?shù)刂闵坛鲑Y,帶動起鄉(xiāng)民參與的熱情。
多元投入機制的建立,調(diào)動了社會組織和村莊內(nèi)生動力,也降低了政府的建設(shè)成本。
據(jù)了解,浙江第二批、第三批歷史文化村落保護項目今年將繼續(xù)實施,第四批43個重點村和219個一般村的保護項目2016年也將全面啟動。力爭到2020年,全省入庫有價值的古村落都得到有效保護和科學(xu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