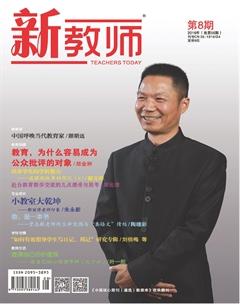教育,為什么容易成為公眾批評的對象
鄭金洲
近年來,公眾對教育的議論越來越多,批評也越來越激烈,在某些時間點上,教育甚至成為“聲討”的對象。教育受到這種“超常規(guī)”待遇,在其他領(lǐng)域比較少見,極少領(lǐng)域可與教育“比美”。由此,自然產(chǎn)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教育容易招致批評,成為公眾關(guān)注的“負(fù)面”焦點?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我看來,以下幾方面似乎是主要原因。
一、社會期望值高
在所有社會形態(tài)中,公眾都對教育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期待,期望教育完成一定的使命。而在社會轉(zhuǎn)型期,這種公眾預(yù)期會變得更加強烈。轉(zhuǎn)型,意味著還沒定型,還有變化的可能,還存在著許許多多未知的因素。大多數(shù)公眾在社會轉(zhuǎn)型期中,掌控的資源有限,支配的空間不大,自己在社會上博弈的砝碼不多,能夠發(fā)揮作用的可能非教育莫屬。大家期望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社會際遇,提高自身的社會層級,增進(jìn)自己以及家庭的社會聲譽,用我們經(jīng)常說的話,叫作“知識改變命運”。即使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其父母對子女的教育也有著很高的預(yù)期,他們也深知,沒有教育做依托,子女的路走不長遠(yuǎn),也不會走好。可以說,在教育話題上,公眾有著非常一致的心理預(yù)期,幾乎沒什么太大的分歧。這種高預(yù)期的集體心向,使教育備受關(guān)注;眾口難調(diào)等原因,使教育也難以獲得好評。
二、公眾“容忍度”低
與上述原因相關(guān),公眾對教育由于“過度”關(guān)切,對教育中的任何瑕疵、疏漏、錯誤等都洞若觀火,難以忍受。這種情況在我國表現(xiàn)得又尤為突出。中國人向來對讀書有著較高的尊重和關(guān)切,這種關(guān)注與獲取知識有關(guān)聯(lián),但不是如古希臘般為知識而知識,而是讀書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如獲取功名、“顏如玉”“黃金屋”等,這種功利觀念由來已久。所以,雖然中國不是“人力資源理論”的發(fā)祥地,但“人力資源”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國父母都對自己的子女有著較高的期望,希望子女“成龍成鳳”“出人頭地”,很少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一個普通人,哪怕這樣的生活孩子很幸福。這些因素,再加上東方文化中特有的父母子女間的親情關(guān)系,使得公眾對教育上的問題變得尤為敏感。中國人講“過日子”,其實對不少家庭來講,就是“過孩子”。房價高點,能忍;待遇差點,能湊合;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不健全,能對付;生活條件一般,沒什么;唯獨不能忍受的就是教育上的差錯和不公平。在一些地方,教育成為公共事件的“導(dǎo)火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點。
三、教育發(fā)展變化慢
教育易招致批評,當(dāng)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改革速度、力度、強度不夠,發(fā)展變化遲緩,使得教育難免受到責(zé)難。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教育和其他領(lǐng)域一樣,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改革也一直處在持續(xù)狀態(tài),公眾也比較多的有了教育成就的“獲得感”。但與其他領(lǐng)域如經(jīng)濟、文化等相比,教育觀念的更新不大,改革發(fā)展的成效也不算太突出,許多教育上的疑難問題始終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比如,我們在20世紀(jì)80年代就提出了反對片面追求升學(xué)率的問題,要求要進(jìn)一步端正辦學(xué)指導(dǎo)思想,時間過去三十多年了,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很好解決,甚至還沒有真正破題。教育發(fā)展變化慢不是中國教育獨有的問題,是全世界的“通病”。個中緣由,一是教育累積效應(yīng)明顯,每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教育都是根植于自身的政治經(jīng)濟土壤,經(jīng)由數(shù)年的層累而生成的,要“急剎車”或“急轉(zhuǎn)彎”都有著不小的困難。二是教育改革發(fā)展的成效具有滯后性,教育是培養(yǎng)人的事業(yè),它自身的變革與發(fā)展不像有的領(lǐng)域那樣一兩年見成績,三五年效果就非常明顯。教育常常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見證自身變革的成效。三是教育的依附性較強,它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自身的變革以其他領(lǐng)域變革為前提依托,沒有其他相關(guān)領(lǐng)域變革的保證,它幾乎很難深入地變革下去,這也使其變化舉步維艱。
四、發(fā)言“門檻”低
教育容易受人批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批評者都能夠提出批評意見,也都自認(rèn)為對教育有發(fā)言權(quán)。批評醫(yī)療衛(wèi)生,首先需要了解衛(wèi)生體制,掌握醫(yī)療相關(guān)的專業(yè)活動;批評經(jīng)濟活動,首先需要了解經(jīng)濟的基本運行情況,對經(jīng)濟學(xué)理論稍有認(rèn)知;批評文學(xué),首先需要讀文學(xué)著作,對著作進(jìn)行背景、旨趣、社會意義等多方面剖析……所有這些,是一般的公眾所不具備的。批評教育則不然,沒有學(xué)過教育學(xué),不掌握教學(xué)專業(yè)知識,不影響對教育提出批評。因為公眾在其日常生活中,對教育就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感知,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教育常識(至少自認(rèn)為是如此)。沒有學(xué)過教育史,但自己有著受別人教育的歷史;沒有學(xué)過教育學(xué),但自己一直參與著形形色色的教育活動,甚至在有些活動中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主角”……這種種經(jīng)歷,使公眾能夠?qū)逃F(xiàn)象做出針砭,對教育活動進(jìn)行評判,對教育中的人或事提出自己的見解。發(fā)言“門檻”低了,公眾議論紛紛,你一言我一語,就很容易形成評論的氛圍。一旦教育中的某一個或某些事件成為熱議對象的時候,也就比較容易形成批評“浪潮”,將教育中其他成分覆蓋或弱化,凸顯的是批評的風(fēng)暴。
五、意見領(lǐng)袖刷“存在感”
在現(xiàn)代社會中,信息繁雜海量,一般公眾要想獲取其中全部的信息,形成對問題的全方位了解和認(rèn)識幾乎變得不太可能。這種情況下,在人際傳播網(wǎng)絡(luò)中經(jīng)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應(yīng)運而生,他們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的作用,由他們將信息擴散給受眾,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有的信息即使直接傳達(dá)到受眾,但由于人的依賴、合群、協(xié)作心理促使他們在態(tài)度和行為上發(fā)生預(yù)期的改變,還須由意見領(lǐng)袖對信息作出解釋、評價,在行為上作出導(dǎo)向。意見領(lǐng)袖的影響力一般分為“單一型”和“綜合型”。“單一型”,即一個人只要在某個特定領(lǐng)域很精通或在周圍人中享有一定聲望,他們在這個領(lǐng)域便可扮演意見領(lǐng)袖角色,而在其他不熟悉的領(lǐng)域,他們則可能是一般的被影響者。“綜合型”,即一個人在一個以上的領(lǐng)域都享有一定的聲望,在不同的領(lǐng)域中都有自己的影響力。從教育自身來看,前一種類型的意見領(lǐng)袖在某些特定的問題或事件上會積極地傳播相關(guān)信息,造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后一種類型的意見領(lǐng)袖也常常當(dāng)仁不讓,把自己作為教育問題的行家里手,對教育活動評頭論足,在發(fā)表自己言論的同時,增進(jìn)自己的存在感。畢竟對教育活動或現(xiàn)象發(fā)表意見不是件太難的事情,同時也能引起較為廣泛的關(guān)注。
六、媒體傳播速度快
教育成為公眾關(guān)注的焦點,或成為公眾集中批評的對象,這種現(xiàn)象之所以產(chǎn)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新媒體的廣泛運用。我們現(xiàn)在處在一個新媒體時代,各種新的傳播手段如微信、微博等各種APP作為重要傳播媒介,不僅僅是一個傳播信息的工具,也是交流的渠道、互動的平臺。新媒體徹底改變了傳統(tǒng)媒體時代你寫我看、單向傳播、單次傳播的模式,極大地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格局。各種集文字、音頻、視頻、圖片、表情等多種媒介為一體的手機社交軟件,不僅帶來了社交網(wǎng)絡(luò)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還改變了人類的交流方式和社交模式。正像有人所談到的,我們永遠(yuǎn)無法預(yù)言什么樣的技術(shù)會在將來成為某種“新”媒體的特征,但可以預(yù)言的是:這些技術(shù)可以使人們更加便利地運用,更加公開公正地討論和傳播信息,更加良好和廣泛地進(jìn)行社會交往。可以想見,當(dāng)教育運行的某一方面遇到問題或產(chǎn)生缺陷時,公眾完全可以借助新媒體,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形成輿論關(guān)注的熱點,從而也給大家造成一種“眾矢之的”的印象。
七、教育自辯能力差
如果教育遇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評,教育界自身有著充分的自我辯護(hù)力量,能夠?qū)@些批評做出足夠令人信服的回應(yīng),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降低批評造成的影響。但遺憾的是,教育自身這種自辯能力不高。一是當(dāng)教育成為公眾批評的對象或熱點時,教育界缺乏明確的自辯意識,不少人覺得“清者自清”。二是教育界難以組織起有效的辯護(hù)力量,即使有辯護(hù)的話,也常常讓人覺得“隔靴搔癢”“不解渴”。三是當(dāng)教育受到公眾批評時,需要的不只是來自于教育行政部門的回應(yīng)與反饋,尤其需要公眾、教育管理部門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也就是教育理論研究者做出有理有據(jù)的評論,但教育理論研究與教育實踐研究的長期疏離,使得教育理論工作者對實踐問題了解不多,即使了解,也不愿意涉足評論的漩渦。
在世界各國,教育雖然不是“火藥桶”,但受關(guān)注程度普遍都較高,這是由教育的性質(zhì)和地位所決定的。不讓公眾批評不可能,但讓公眾少批評,或者在這其中對批評加以引導(dǎo)還是可能的。這就需要我們切切實實做好教育工作,及時了解公眾的教育需求,對教育政策等適時做出調(diào)整;也需要我們注意把握教育輿情,及時捕捉相關(guān)信息,對教育的不當(dāng)指責(zé)盡快進(jìn)行澄清。
(責(zé)任編輯:林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