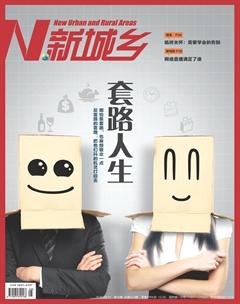黑戶 洗白之路
每個“黑戶”的背后,都有一個長長的故事,新政策的出臺給“黑戶”們帶了希望,但具體的執行結果還不盡如人意。
戶口簿,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學就業以及福利保障都與這一薄薄的戶口本息息相關。
在中國沒有戶口的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給出的答案是至少1300萬,幾乎每100人中就有一個人是“黑戶”。這比希臘總人口還要多200萬,和挪威、芬蘭、丹麥的人口總和差不多。
他們沒有戶口卡,也沒有身份證,被社會俗稱為“黑戶”。與其他弱勢群體相較,“黑戶”更顯隱秘,他們分散于社會的各個角落,社會難以感知到他們的存在,他們是行走在都市中的“隱形人”。
“超生家長群”里的“黑戶”影像
深圳的“黑戶”,主要是多胎超生和未婚生育群體,他們呈現出低齡化特征。據我們向深圳“超生”父母派發的問卷,有78%的“超生”孩子都還未到上學年齡。
至于“超生黑戶”群體的數量是多少,官方統計的數據寥寥。深圳衛計委曾對媒體透露,2016年待入學的小孩中,“屬于我市戶籍人口超生而未辦理出生登記的小孩”約有3000名。深圳小學入學年齡是6周歲,假設每年情況大致相同,則深圳有1.8萬名小孩因超生淪為小“黑戶”。
這樣的數據并非憑空捏造,我們先后加入8個“超生”家長群,其中6個是深圳本地的,經去重統計,得出深圳因超生未給孩子落戶的家長是3082人。這只是在線上抱團取暖的部分,確切數據無從知曉。
同樣通過QQ群形式集合在一起的“黑戶”群體還有未婚媽媽。我們在調查過程中,共查找到5個未婚媽媽群。這些QQ群成員比起超生家長,更為敏感而隱秘。基本要求有親子照片和語言驗證通過才能進群,且堅決不允許男性入群。
最終,我們成功加入兩個未婚媽媽群,其中一個是深圳本土的,共有89個群成員;另一個是全國的,群成員是48個00后、90后未婚媽媽。
除此之外,深圳還存在一群特殊的無戶籍信息人員,他們是被安頓在救助站的城市流浪人員。由于無法正常溝通,很難得知這部分人是否有戶口。就算有也問不出來,也有可能他們根本沒有戶口。
這些分散在深圳各個隱蔽角落里的“黑戶”,仍然生活在陽光無法到達的地帶。這些“黑戶”在醫療、教育、出行方面,處處是坎,到處是墻,每個“黑戶”的背后,都有一個長長的故事。
缺失的社會權利
1996年,畢業于華南理工大學的張強的身份證過期了,從此便開始了他長達20年的“黑戶”生涯,20年間來回于各地法院的訴訟文書壘滿了整整一書包。
由于戶口在畢業遷移中丟失,他在深圳的生活寸步難行。因為沒有戶口,他沒有社會保障,簽不了合同,考不了駕照,甚至連出門旅行、住宿都難以實現。
張強回憶起6年前最后一次回家的經歷。從深圳到遼寧營口,他和家人一共倒了8趟大巴,這段3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耗去整整一個星期。同樣一段路,坐火車只要不到30小時,坐飛機5個小時。 出行受限只是陰霾的一角,對于張強來說,每況愈下的身體使得醫保的問題愈來愈突出。
沒有戶口,沒有醫保,需要全部自費的身體檢查于張強而言是一種“奢想”,縱然他知道沒有準確的診斷就沒有準確的治療。我們發現,不敢去醫院是“黑戶”共同的特點。大都市醫院的費用讓他們望而卻步,先進準確的醫學診斷方法與他們無關。
妻離子散的慘劇更是“黑戶”的無法承受之痛。
在南山塘朗打工的鄭元峰就是一個例子。坐牢的18年間,支撐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鐵窗之外還有個女人在等他。出獄后他才發現,身份證在被捕時被弄丟,公安系統“查無此人”。
沒有戶口,他們無法登記結婚,現在分居兩地。
因為戶籍身份的缺失,“黑戶”幾乎被剝奪了扮演所有社會角色的權利。這也導致“黑戶”群體對社會的認同感普遍較低。“黑戶”往往是形成群體性事件的策源地,容易成為社會的隱患。
依然有人心有余悸
2004年,王長德的二女兒睿睿出生了。依照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個孩子屬于“超生”。她的中國公民身份,需要花費20余萬元的社會撫養費“贖買”。因為根據《深圳經濟特區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五十條規定:超生一個子女的,對男女雙方分別按計征基數一次性征收三倍社會撫養費。
盡管早在1988年,國家計生委、公安部就聯合下文,禁止將計生證明、超生罰款與戶口登記捆綁。但現實卻是,各地為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將計生與上戶口等權益搭車捆綁的“土政策”。作為改革前沿陣地的深圳,2015年12月修改的《深圳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仍規定了“上戶時公安部門應查驗社會撫養費收據和計劃生育證明”。
從2014年10月開始,為了給女兒上戶口,王長德多次往返奔波于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和深圳市衛計委,都被以“缺少《計劃生育證明》《社會撫養費繳納憑據》等材料”為由拒絕辦理上戶手續。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部分計劃外生育的孩子,會被親生父母送給他人,或者流入網絡送嬰、賣嬰的人販手里。甚至有些“黑戶”孩子被拐走后,父母卻不愿意報案。因為孩子縱然找回來了,計生委的“罰單”也就隨之而來了,很多父母都選擇了沉默。
新政策的出臺給王長德帶來了希望。2016年1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意見》,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切實保障每個公民依法登記一個常住戶口。
2016年2月23日,王長德在向辦事民警遞交了相關材料后,他的女兒終于順利上了戶。只花十分鐘,他的戶口本上終于有了屬于睿睿的一頁。為這一頁薄紙,他奔波了整整12年。
我們走訪了關外6個基層派出所,從寶崗派出所戶籍工作人員處得知,《意見》發布后前去上戶的人數明顯增多。近期,轄區內新增的上戶人數就有80余人。
但許多超生及未婚家長依然心有余悸,擔心一旦孩子上了戶,孩子的戶籍就成了計生委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證明。
此外,還有不少二孩父母,尤其是公職人員,因為擔心上戶口會暴露,最后會被追繳社會撫養費,甚至被開除公職,所以遲遲不敢去落戶。
《意見》的出臺不僅讓二孩家長看到上戶希望,“老黑戶”們更是充滿期待。
3月24日,鄭元峰欣喜地接到了原戶籍地陸豐派出所工作人員的電話,讓他過去配合調查。
25號早晨,他剛通宵上完班,就坐上了前往陸豐的班車。在大巴上,他告訴我們,他沒敢跟女朋友提起這件事,擔心又是空歡喜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