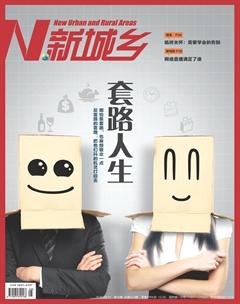從愛司頭到殺馬特,洗剪吹里看中國
鄧娟
束縛頭發(fā)的從來不是發(fā)箍或頭巾,而是政治,然后才是文化心理與個人氣質(zhì)。一粒沙里見世界,從洗剪吹可以看到每個年代的精氣神。
一個小鎮(zhèn)的洗剪吹行當,60多年前叫“剃頭鋪”,門柱通常貼著“敢問天下頭顱幾許,且看老夫手段如何”的對聯(lián),橫批一般是“頂上功夫”。
再后來,“剃頭鋪”改名“理發(fā)店”,普通青年理“小平頭”,文藝青年理“西裝頭”,二逼青年理“沖天頭”。一段時間里,最安全的發(fā)型是男人剃光頭、女人剪辮子,再戴頂軍帽,便是官方認證的“英姿颯爽”。
忽然有一天,“紐約發(fā)廊”“巴黎發(fā)廊”“倫敦發(fā)廊”“東京發(fā)廊”仿佛從天而降,理發(fā)價格像搭上了火箭,發(fā)型終于能自由生長。
束縛頭發(fā)的從來不是發(fā)箍或頭巾,而是政治,然后才是文化心理與個人氣質(zhì)。一粒沙里見世界,從洗剪吹可以看到每個年代的精氣神。
經(jīng)濟危機,催生“理發(fā)女”與“大保健”
中國人對洗剪吹的接受來得相當遲緩,對此,大航海時代的荷蘭人深有感受。明朝開放海禁后,1567 年,印尼爪哇島形成了一個3000多人的華人社區(qū)。荷蘭畫家畫下的華商形象,頭頂扎鬏,留長發(fā),穿長袍,與土著或殖民者都大為不同。
17世紀的雅加達,荷蘭人又注意到,雖然華人也上理發(fā)店,但對頭發(fā)一絲不茍的態(tài)度令人驚異,“用小針盤髻,插以龜貝梳,覆以黑鬃網(wǎng),故初見時吾人常將其男子誤認為女子。華人對此物寶貴異常,以為可代表其名譽”。
而在中國本土,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女人們才將洗剪吹從政治表達矯正為審美行為。
“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張愛玲的童年愿望清單,首先就是梳“愛司頭”,那種S發(fā)型風靡十里洋場,成為當時海派女人的符號。李泉在《花花大世界》惆悵地唱道:“彈落掉老刀牌香煙的灰燼,丁香樓已換了佳人,再沒人梳起時髦的愛司頭,再沒人約她去百樂門……”
那時的上海女人簡直用生命在燙染——把火鉗燒燙后,在頭發(fā)上夾出波浪。美麗雖然危險,女人卻樂此不疲。同為上海女作家的程乃珊說,上海女人和相熟理發(fā)師之間的關系堅貞不移,比經(jīng)“明媒正娶”的老公更穩(wěn)定。關之琳主演的電影《做頭》幾乎是對程乃珊這句話的詮釋。女主角愛妮有一段草率平淡的婚姻,好在還有一頭烏黑亮麗的頭發(fā),她把人生樂趣都寄托在做頭發(fā)上,并因此與理發(fā)師阿華發(fā)展出曖昧情感。
女人是光顧理發(fā)店的主力軍,操刀的理發(fā)師則清一色是男人。同一時期,在東南亞華人圈,因為1929—1933年出現(xiàn)新馬經(jīng)濟危機,服務業(yè)爭相聘請女工,以她們的身體招攬生意,“理發(fā)女”紛紛出現(xiàn),在當時被與女招待、舞女相提并論。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中有一段理發(fā)女的回憶:“民國十九年(1930),便開始有剪發(fā)女,先時人少,而且新奇得很,待遇也就很高,月薪每人竟有百多元,那時有人想用95元聘我,我還不肯去呢。而且當時大家都很樸素,一律是穿白衣黑裙的學生裝,工作時也莊嚴得很,顧客雖然輕薄,最多只裝作無意地把我們的衣袖碰一下,絕不敢捏手捏腳的。”
經(jīng)濟危機加劇后,“可就不同了,因為待遇好,受經(jīng)濟壓迫的女學生、家庭婦女、女工,蜂擁般撲來搶吃了。最糟的是連茶店女招待也大幫擁進來,她們素來愛賣弄風騷,理發(fā)店便成了賣弄風騷的場所,捏手捏腳的事,使我們的名譽壞了”。
鄉(xiāng)土中國,造就殺馬特和洗剪吹
1956年7月6日,一隊浩浩蕩蕩的理發(fā)師,帶著裝滿剃刀、剪刀等家伙什兒的箱包,從上海登火車,朝首都北上。
在北京飯店的招待宴上,鄧小平給理發(fā)師程寅良一本發(fā)型書,說:“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發(fā)型。”
這場遷京行動是響應“繁榮首都服務行業(yè)”號召,上海四大理發(fā)名店——紫羅蘭、湘銘、云裳、華新,抽調(diào)近百名技師,帶去10把美國理發(fā)椅,在北京開張了四聯(lián)理發(fā)店。不過,他們登峰造極的頂上功夫并沒有太大用武之地,因為多數(shù)上門的顧客,選擇的都是平頭和簡單分頭。那個年代,發(fā)式被與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出格意味著風險。至于燙發(fā),這種資產(chǎn)階級作風就更被嚴禁。
四聯(lián)低調(diào)地恢復燙發(fā)業(yè)務是在1977年,不過只面向持有單位介紹信的演藝人員,并且惹眼的波浪造型仍不被允許。
好在,春天雖然有點晚,但總算是來了。1979年的中國洋溢著一種從頭開始的氣象。那年秋天,法國設計師皮爾·卡丹在北京搭建臨時T臺,外國女模特的走秀,激發(fā)了灰頭土臉的中國人的時尚啟蒙。
隨后,日劇《血疑》和《排球女將》引進中國,山口百惠那簡潔、俏麗的“幸子頭”,以及把劉海在額角兩側扎成辮子的“小鹿純子頭”蔚然成風。
港臺劇也不遜色,瓊瑤劇作為言情擔當,黑長直、劉海中分的“青霞頭”至今是直男最愛發(fā)式。女仿林青霞,男學周潤發(fā)。許文強的大背頭造型,與“浪奔,浪流”的旋律一同成為經(jīng)典。
當時還興一種“招手停”發(fā)型,把額前的劉海長長高高地吹起,用發(fā)膠固定在蓬松起來的那一刻,由于頗像“招手”姿勢,于是被人們形象地稱為“招手停”。“招手停”的誕生可以說是中國發(fā)型界的里程碑,第一次把劉海吹得硬氣十足,受到最多女士的熱捧。與“招手停”同時流行的還有摩絲,一聽名字就知道它是舶來品,這種固定發(fā)型用的美發(fā)產(chǎn)品以傲然姿態(tài)挺進了中國。
“時尚時尚最時尚”的“招手停”男女通殺,擁護者除了標志性的貓王,還有鐘楚紅、劉嘉玲,也包括18歲那年正在上高三的高曉松。
從三七開的“林志穎頭”、五五開的“郭富城頭”,到最新“宋慧喬同款空氣劉海”,中國人的洗剪吹永遠以明星為風向標,哪怕現(xiàn)實與理想的落差塑造了一個個殺馬特。
如果說鄉(xiāng)土依然是中國的底色,那么,最體現(xiàn)洗剪吹精神的,理應是這則網(wǎng)絡段子——
“找哪位發(fā)型師為您服務呢?是Kevin老師、Jack老師、Eric老師還是Lucy老師呢?”
“我都不認識,那就Lucy吧。”
“ 好的,您稍等。Lucy老師,10號客人要理發(fā)。Lucy,Lucy!Lucy……劉繼芬!有人要剪頭!”
“啊!來了!”
(據(jù)《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