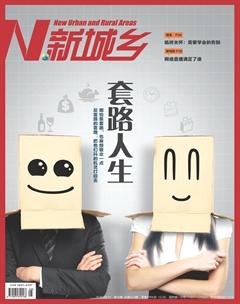城市聲音:被忽略的聽覺風景
丘濂
如果聆聽方式得當,不難發現每個城市都有它的獨特音軌。就是在全球化和同質化日益嚴重的今天,從聲音的角度去觀察城市,也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打開耳朵
聲音藝術家殷漪曾經在一次展覽上放置過一個叫“交通信號燈”的作品。觀眾可以聽到20個城市中與紅綠燈相伴的提示音。它們的音效、頻率、音高、響度都不一樣:東京是一種“啾啾啾”的高亢鳥叫,香港是“嗒嗒嗒”平穩的機械音,同樣是在中國內地,有的地方是“嘟嘟嘟”,有的城市是“叮叮叮”,還有的干脆就是一種呆滯刻板的人聲:“現在是紅燈,請不要闖紅燈。”
8年之前,殷漪開始做實地錄音,這是他從海量聲音素材中找尋到的一個有趣現象。“為什么世界范圍內,信號燈的樣子都相對統一,聲音卻各不相同?正是因為我們以一種視覺中心主義來建構周遭,對聲音不夠敏感,也缺乏標準,這反而讓我們的聲音環境有了無比豐富的可能。”
描述視覺景觀的詞匯不勝枚舉,關于聽覺內容的形容詞卻乏善可陳。視覺具有優先地位有著合理的生理學構造解釋——視覺到大腦的神經通路長約5厘米,聽覺神經在9厘米左右。視覺神經通路短,是五官感知中最為直接迅速的,可以幫助人們立刻判斷情況,做出決定。
“視覺雖然列于五感速度之首,但就品味而言,聽覺卻在視覺之前。”清華大學聲學實驗室主任燕翔說。燕翔平時愛好詩歌,實驗室的墻壁上掛著清華園的景色圖片,下面配有他題寫的古體詩。“你想想看,在古代成語中,大多文辭聽覺在前,視覺在后,聽覺的境界更高一籌。如聲色俱厲、聲色犬馬、繪聲繪色……事物一旦具象,品味的空間就會被壓縮。”
無論怎樣辯駁聽覺的重要,都改變不了聽覺受到漠視的事實。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聲學研究所所長李國棋曾組織學生做過北京市民的聲音意識調查,結果顯示年齡越大的受訪者能夠回憶出每天聽到的聲音越多,20歲到30歲的年輕人反而聽到的聲音較少。
李國棋開了一門很受歡迎的全校公選課程“音響教育”,不是為了培養專業的音響師,而是能夠提高大家對聲音環境的關注度。課上,他會給學生們布置若干練習來培養一種“具有批判力的聽力”。從最簡單的將所聽到的聲音列表在紙上來訓練一種聽取習慣,到回憶住處一些令人不快的干擾聲,看看怎樣才能將它們去除,再到如何運用各種音響的搭配,設計一個聲音美妙的公園。
一聲一城
如果聆聽方式得當,不難發現每個城市都有它的獨特音軌。
與西方相比,中國是個“大聲之國”——人們毫不介意在公共場合肆意發出巨大聲響。“一方面它嘈雜不堪,另一方面那些聲音細節也充滿了活力。對比起來,你會覺得有的歐洲城市死氣沉沉,甚至有點寂寞。”曾擔任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策劃部主任的秦思源說。2005年,秦思源發起了“都市發聲”的項目,邀請英國若干位聲音藝術家來到北京、上海、重慶和廣州四座城市,采集當地聲音進行創作。
秦思源在北京生活多年。他認為北京聲音背景的豐富性是和北京人“玩兒”的傳統相關的。全世界的人都養鴿子,可為什么唯獨北京人在意的是鴿哨?在秦思源看來,北京是六朝古都,最后一任清朝政府為八旗子弟供給錢糧,讓他們飽食安居,有大量閑暇時間殫精竭智鉆研各種娛樂玩好,這都在當代北京人中得到了繼承。“養鳥兒,聽的就是叫聲。北京人專養‘凈口百靈,所謂‘凈口,就是規定百靈要依次發出一套13種叫聲,學麻雀、伯勞、山喜鵲,還有貓叫,鷹叫……不能改變順序,要叫完一套再叫一套。”
“都市發聲”項目同時向北京市民征集“心目中的北京聲音”。除了鴿哨聲外,排名前幾位的還有平房院子里大棗兒的落地聲、公共汽車售票員的報站聲、磨刀人手中“嘩啦嘩啦”的鐵片聲、非正規的旅游拉客點往復播放的“天壇——長城——十三陵”的叫喊聲。一位叫趙雅琪的北京市民這樣解釋為什么對售票員報站情有獨鐘:“因為可以聽到北京許多奇怪的胡同名和小街道名。”并且那種包含喜怒哀樂情緒的嗓音大大區別于地鐵的廣播報站——“一種報八寶山和天安門都是一樣調調的聲音。”
去年,上海一家報紙也發起“尋找上海都市新聲”的線上活動。上海市民認為最能代表上海聲音的分別是黃浦江上的汽笛聲和海鷗飛鳴、上海阿姨“噶訕胡”(閑聊天)和24小時便利店推門進入時的音樂門鈴。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殷漪大量實地錄音收集的并非人們印象中典型性的上海聲音,而是完全日常化和私人化的聲音片段。虹口公園里的人們跑來跑去打著羽毛球——這恰恰是白天上班時間錄制的,是一個冰冷寫字樓之外鮮活的城市;上海火車站的地下通道里,一位中年婦女用機械干澀的嗓音不停地重復“發票、發票”,一天要喊一萬多遍,這仿佛是光鮮外表下見不得人的一道傷疤;隔壁鄰居家在為過世的老人做法事超度,誦經聲中依稀辨出兩個人的對話:一個說,花了15塊錢買了個東西不太合算;另一個說,這么重要的日子,就不要考慮這些了……這些聲音碎片中捕獲的生老病死與夾雜其中的精明算計,它們才是殷漪感受到的真實上海。
遠離噪音
在燕翔位于清華大學主樓的辦公室里,我們一度停止了對話。“這是一個安靜的環境嗎?”燕翔問道。仔細傾聽,室內的空調發出嗡嗡的響聲,窗外的園丁正在用水管澆灌著草皮,機動車混雜著自行車不斷從樓前的主干道經過。“這大概有45分貝左右的音量。”燕翔說。按照國內的《環境噪聲標準》,以居住、文教為主的區域,白天噪聲標準為55分貝,夜間為45分貝,我們屬于正常值之內。而如果按照美國的規定,在距離居民樓1米處進行測量,所有噪音超過45分貝的聲源都被禁止使用。我們已經處于一種過度的噪聲環境里——在“大聲之國”,人們擁有對環境噪音更強的耐受性。
噪音具有一種主觀性,最直接的定義就是“樂音以外的一切聲音”都為噪音。現代城市的交通系統是我們生活里一種持續不斷的背景噪音。北京猶如“攤煎餅”一樣,從二環向六環不斷擴張,每一圈環路上都有噪音形成的不同音景。“二環基本都是小轎車,白天處于緩行和蠕動狀態,車速不快又禁止鳴笛,因此是一種沉悶的聲響;形成反差的是六環,大型和超大型貨車喘著粗氣前行,那種聲音,像個永不停息的工地。”中國傳媒大學傳播聲學研究所的孟子厚教授這樣形容。
懷著對安靜狀態的渴望,燕翔說服學校投資建設了零分貝實驗室。這個其貌不揚的磚紅色六角形建筑,就是全中國最安靜的地方。
燕翔在這里進行了“安靜一日”的實驗,邀請不同年齡的志愿者在里面工作和休息。“剛剛進入時,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耳鳴,年齡大的人要長一些,也有極個別人耳鳴從頭持續到尾,但大多數人在20分鐘后開始享受寂靜。”實驗對象們紛紛表示,在里面工作的效率都提高了。“‘怎么才進去就吃飯了?這是因為注意力太過集中。”午睡的人在里面休息時,深度睡眠的時間達到了20~30分鐘。“過去認為午睡時沒有深度睡眠,是因為白天休息褪黑素分泌減少的緣故。其實還是白天不如夜晚安靜。普通人夜晚8小時的睡眠里,有40分鐘的深度睡眠就很不錯了。”
燕翔從零分貝實驗室得出的結果是安靜對人百利而無一害,“只可惜除了在這種特殊環境下,人們無法獲得安靜”。燕翔日常工作的重要一塊是幫助人們解決噪音問題。“都是補救性質的。沖突到一定程度無法處理,然后請我來想辦法治理。可是為什么不能提前預防呢?”曾經全國各地流行一陣來制作噪音地圖,后來就沒繼續下去。“噪音地圖”對于城市發展來說是一個“剎車”,而不是“油門”,所以注定它成為一紙空談。
(據《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