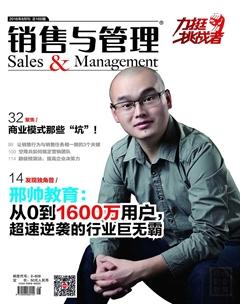“萬科之爭”本質是公司治理問題
戴險峰
在美國股票市場的發展歷史中,公司最初也主要由管理者掌控,并不重視股東權益。但隨著機構投資者開始主導市場,投資者開始重視股東權益,公司治理也開始越來越強調對股東權益的保護。這種公司治理理念及投資環境就催生出以維護投資者權益為核心的“維權投資”。
萬科股權之爭所涉及的問題看似紛繁復雜,實際上是非常簡單的公司治理問題,而且在法律框架下早已被維權投資者實踐過無數次。
他們的代表Carl Icahn,就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聯合邁克爾·米爾肯通過垃圾債市場籌資,是所謂“野蠻人”的原型。不過,1980年代的并購潮最終因高杠桿及經濟衰退而陷入困境,造成垃圾債的大量違約。
但后來的大量學術研究表明,盡管當時的垃圾債違約產生了500億美元的損失,并購潮帶來的股東收益卻高達7000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當時股東收益的來源主要是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以損害其他相關方為代價。
2001年前后開始,對沖基金行業迅猛發展,維權投資策略也開始盛行。這種投資風格在本質上屬于價值投資。只不過傳統的價值投資是被動地等待市場自行糾正股票的錯誤估值,而維權投資則以向董事會寫公開信、召開董事會、任命新股東以及罷免CEO等積極推動公司變革的方式來主動糾錯。Carl Icahn在2004年設立維權基金后,迅速入股時代華納、摩托羅拉、雅虎、獅門電影以及高樂氏等一系列著名公司,然后開始寫信給董事會提出整改建議。當他建議拆分時代華納的方案遭到CEO反對時,Icalhn 便開始努力將該CEO趕走。
盡管他沒有實現最初目標,但在Icahn持股期間,時代華納的股票上漲了30%。維權基金盡管以自身獲利為目標,但通過維護股東權益而在客觀上實現了對公司管理層的督促,迫使管理層采取積極措施來提升股東價值,并且更加關注小股東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當維權投資者試圖將該策略用于日本市場時,卻遇到很大阻礙:日本的公司治理采納利益相關方原則,建立在關系與圈子之上,交流方面注重禮貌與友好,對維權投資者咄咄逼人的方式自然是排斥的。
因此在事實上,不僅美國這種以股東權益為核心的治理體系強調股東價值,而且日本這種以利益相關方為基礎的治理體系也開始重視增加股東價值。而全球范圍的董事會更是一直將股東至上作為默認的原則。
萬科的股權之爭中,也應該強調各方對股東所負的責任。股東是公司的出資者、所有者以及風險的最終承擔者。管理層是代理人,與董事會一樣負有信托責任。
這是一切討論及協調各方利益的最基本的出發點。這個原則對萬科適用,對寶能適用,對華潤也適用。從維權投資者的經歷來看,管理層與維權投資者的對抗幾乎總會出現,但投資者作為股東的意見最終都會受到重視。
所謂現代公司治理理論認為,公司治理不應該是股東至上,而應該考慮包括供應商、雇員及債務人等在內的所有相關方。有些理論還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不完備的市場更應該實施利益相關方的公司治理。這些理論是美好的,也是理想狀況下應該推行的。
但現實情況是,這是在保護股東權益方面已經相對成熟的市場發展起來的理念,是超越了股東權益的更高要求。而中國的市場在很多時候連股東權益的基本意識都不具備,這從圍繞萬科之爭的各種辯論即可看出。
比如在涉及公司治理及法律的時候,就有試圖拋開法律而從“合理性”角度來展開的辯論。問題是所謂的“合理性”注定是主觀的,是基于特定角度和出發點甚至是基于利益考量的。A的“合理”對于B來說可能就完全不合理。法律可能不會兼顧所有人的主觀愿望,但全球各國的立法大多都是綜合考慮了各方利益之后的一個協調統一的體系,在條款和規定上是明確客觀的。
中國的公司法并不存在什么不合常理的條款。對中國市場來說,正因為市場不完備,甚至缺乏基本的產權意識,小股東權益歷來被忽視。在股東權益的意識都還缺乏時,中國市場的公司治理可能還要從最基本的對股東權益的保護開始。股東是出資方,是公司運營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如果股東權益都不能保障,何談其他利益相關方?
一個有是非觀、知道對錯、了解規矩并且按照規矩行事的社會才會減少困惑,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增加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講,圍繞萬科股權之爭的討論也是一個促進公司治理發展、建立行為規范、教育投資者的維權意識的好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