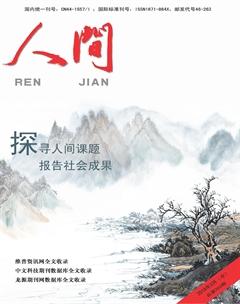淺析涼山州冕寧縣“團結話”
巴且木呷子



摘要:本篇論文以冕寧縣老、中、青年三代人的“團結話”為例,運用450個詞匯作為調查的原始數據,通過田野調查、對比研究及統計學相關研究方法,從口語和書面語兩個層面對這種特殊的語言變體的詞匯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并且把冕寧縣“團結話”的語言系統與母語涼山彝語和目的語冕寧縣漢語方言的語言系統進行細致的對比分析,描述其特點。
關鍵詞:冕寧縣“團結話”;詞匯
中圖分類號:H1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3-0150-03
引言
冕寧縣“團結話”①是涼山州冕寧縣彝族在社會交往中,特別是在與身邊漢族交往中所使用的特殊語言變體。它是涼山彝語與冕寧縣漢語方言之間的中介語,也是民族母語受到強勢語言漢語方言影響而逐步向強勢語言過渡的一種特殊的、動態的中間形式。它有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詞匯規則,其語言系統有自身的獨立性。
一、冕寧縣概況
冕寧縣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涼山彝族自治州北部,處在東經101°38′~102°25′,北緯:28°05′~29°02′之間,東鄰越西、喜德,南接西昌、鹽源,西連九龍、木里,北毗石棉。北距省會成都368公里,南距州府西昌80公里。
據《冕寧縣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②顯示, 截至2012年年末,冕寧縣戶籍人口386390人,漢族人口占大多數,達226822人,占全縣總人口的58.71%。冕寧縣境內居住有彝族、藏族、回族等19個少數民族,其中彝族人口為151289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9.15%,彝族是當地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
二、母語使用情況
彝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根據彝語內部方言分區,冕寧彝語語屬于彝語北部方言之北部次方言中的圣乍話。③
根據調查發現,在同一地區,我們發現老年人的彝語水平是最好的、中年的次之、青年一代彝語水平較弱。簡單舉個例子來說:青年間問“你吃飯了沒有?”這句話,當交際對象是彝族時經常都會用彝語來說這句話;可交際對象為漢族時,他們立刻會說“你干飯沒有?”;老年人跟漢族交流時,出現了中間夾帶有彝語的現象,如表達“我一個老人家能做些什么?”,他們通常都會說“我一個老莫蘇能做啥子?”,而這里的“莫蘇”就是彝語,是老人的意思。
三、冕寧縣“團結話”詞匯特點
(一)材料來源:本次冕寧縣“團結話”詞匯調查主要使用涼山彝族“團結話”調查團隊研究、設計的“團結話”調查450詞表。這個詞表主要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組編制的《漢語方言詞語調查條目表》,同時根據此次調查的具體情況對相關條目進行了增刪。450詞包括了基本詞匯以及部分涼山州當地特殊詞匯,并按意義分為19個小類。本調查詞表經社科院語言所李藍教授審定,雖然總體詞匯量不大,但各詞匯內部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對冕寧縣當地語言也有較強的針對性。
(二)詞匯分類。
四、詞匯對比與簡析
(一)時間、時令類
1.在稱謂傳統節日名詞時,如“端陽”和“除夕”,基本上可以說是都受了成都話的影響,而且老一輩的人比青年人更為清楚;因為彝族雖說也過春節(但過春節也只是簡單吃頓飯,沒有彝族年時那么濃重),除了春節外,彝族沒有過漢族其他的傳統節日,尤其是青年部分,他們很多人會過情人節、圣誕節等一些流行節日,因為這些原因,很多彝族青年對一些如“中元節”這樣一些傳統節日的稱謂基本上是受了普通話的影響,就拿“中元節”來說,在我們當地的漢族也是基本上沒過這節的。
2.對時間段的稱謂沒有明確的劃分,從而出現了這樣一些新詞,并且這類詞的使用頻率不高,如:把“清晨”說成了“早上”,而“黃昏”的稱呼各異,青年都說成“下午”,而部分中年和老年把黃昏說成“太陽落山”或“太陽落”。如:要表達“黃昏時,有客人來過”他們往往說成“太陽落山后,有客人來過”。
(二)農作物、植物類。
1、大多數中老年人在對部分農作物及部分植物的稱呼中存在容易產生歧義的現象。如:把“向日葵”——“瓜子”,因為不知道“向日葵”這一名稱,誤把它的果實當做了植物本身,而青年人多數接受過教育或出去打工跟漢族人接觸的較多,所以他們能輕易區分開“瓜子”和“向日葵”這一概念。
2、對一些植物的稱呼中出現了特有的新的稱呼。如:“杜鵑花”——“索瑪花”,這是受了彝民族對這種植物稱呼的影響,平日里,彝族同胞對杜鵑花的稱呼是“爍瑪”,后來用漢語翻譯過來就成了“索瑪花”,而且在整個涼山州無論是彝族還是其他民族都稱“杜鵑花”為“索瑪花”,因長期使用,自然而然形成了彝民族對杜鵑花特有的稱呼。
(三)動物、家禽類。
1.“子”、“兒”的詞綴現象:“蜂”——“蜂子”、“螞蟻”——“螞蟻子”、“公貓”——“公貓兒”、“母貓”——“母貓兒”,冕寧縣“團結話”中名詞后面加上詞綴“子”、“兒”,尤其是詞尾“子”的應用,它具有極強的構詞能力,在普通話和漢語方言中也很常見,但在冕寧縣的“團結話”使用更頻繁。“子”綴是個名詞標志,使用頻率較高,但不影響原詞匯的意義及用法。
2.在部分中年及老年人對一些動物的稱呼中出現了只有少量人使用的稱呼,因為這些稱呼大多數是市場上做生意時的一些用語,在平時的交流中又很少使用。如:“公貓”——“男貓兒”、“母貓”——“女貓兒”、“母馬”——“褲馬”、“公羊”——“騷羊”、“公牛”——“大骨牛”、“公豬”——“毛豬”或“大肥豬”等,如:“這頭大骨牛賣了好多錢?”。
(四)稱謂類。
1.構詞語素完全不同,但詞義、用法相近或基本相同。在冕寧縣“團結話”中,有一部分詞匯與普通話詞匯在詞形上完全不同,但是在詞義及用法上又基本相同。這類詞匯包括:小孩——小娃兒 道士——道師 嬰兒——奶娃兒等。
2.在11個稱謂名詞中,中老年人中間出現了很多現在的年輕人基本上沒聽說過的一類詞,部分詞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解而出現的,現在很少使用,這類詞大多只限于中老年人在使用,尤其是老年人,這種稱呼在年輕一代中漸漸消失了。如:扒手——摸勾兒(二流子) 吝嗇鬼——舍不得(計計較較) 單身漢——獨人 老姑娘——女獨人 等。
3.在老年人中出現少量容易產生歧義的的詞,只是使用率不高,這部分詞匯是老年人根據自己的理解、是在和漢族同胞交流時臨時產生的一類詞。如:男孩——小兒子 女孩——小女兒 和尚——尚尼四等
(五)身體類。
1.中老年對很多身體部位名稱沒有概念,這類詞在平時和漢族同胞交流中很少用到,有時候不得不用到,他們大多數都是用手去指具體部位,所以造成對這類詞沒有概念,沒有概念并不意味著平時不用,但在彝語中是有相應的詞匯來稱呼的。如:酒窩、后腦勺、額、嘴唇、箕(簸箕形的指紋)、斗(圓形的指紋)、手心等
2.在冕寧縣“團結話”中,部分中老年對手指的稱呼較特別,這種稱呼也是部分人所獨有的,這部分詞出現的原因有二:一是受當地漢民族的影響;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造出的。如:食指——二指姆/二指弟、中指——三指姆/三指弟/周收娘、無名指——四指姆/四指弟/王嗨角等,在這里我們很容易從中發現,部分中老年人把所有的手指都稱呼為了“指姆”,只是在前面加上“一、二、三”來區分不同的手指。
(六)一般動詞:
1、爪瞌睡/栽瞌睡:都指打瞌睡。
2、跶到:跶即是跌,意思是摔倒、跌倒。
3、濤:就是罵的意思。
4、沽:①是蹲的意思;
5、吆:驅趕、趕的意思。如,“把牛吆回來。”
6、該:在冕寧縣“團結話”中表示欠某人錢、差錢的意思,如“我還該你好多錢?”。這與成都話的詞義和用法完全不一樣。在成都話中,該有兩個義項,①是副詞,表示肯定,強調確實、的確如此,如“沒得哄你撒,我這次該是考了第一名嘛”;②是表示假設,如“該曉得這個活動是騙人的,我才不得去呢”。
7、爪:①是踢的意思,如:“爪足球”就是“踢足球”的 意思,這層意思在“團結話”的使用中最為普遍;②就是做什么、怎么的意思,如“爪哈子”就是“做什么或什么事”的意思,這層意思更多的是青年人在平時的交流中最為常見,而這層意思是受了網絡流行用語的影響。
五、結語:
冕寧縣“團結話”是彝漢中介語,是漢語方言的一種特殊變體,同時它也是一個不斷變化著的語言系統,它的發展過程是動態的、非靜止的,其特征也不是完全僵化的。冕寧縣“團結話”是一種以日常交際為核心的特殊語言變體,其詞匯的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一)非雙音節詞數量較多。
在冕寧縣“團結話”中,非雙音節詞占優勢,并且從數量上而言比普通話多得多,幾乎占到整個詞匯系統的一半左右。雙音節詞則明顯少于普通話。
(二)重疊和兒化的構詞手段使用較多。
冕寧縣“團結話”由于受西南官話成都話的影響,重疊和兒化的構詞手段使用很多,因此在詞匯系統中重疊詞和兒化詞匯所占比例很大。從詞性上看,名詞性語素、動詞性語素、形容詞性語素都可以重疊,并且重疊和兒化還常常聯用,表示一定的感情色彩。
參考文獻:
[1]朱文旭.彝語方言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12.
[2]戴慶夏.語言調查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1.
[3]四川省冕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冕寧縣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10.
[4]陳士林、邊仕明、李秀清.彝語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7.
[5]李藍.西南官話的分區(稿)[J].方言,2009,(1).
[6]呂叔湘.形容詞使用情況的一個考察[J].中國語文.1965,(6).
[7]汪坤玉、梁德曼.四川西南部彝族使用漢語的歷史和現狀[J].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1).
[8]巫達.漢彝“團結話”與彝漢雙語教學[J].雙語教學與研究(第一輯),1999.
[8]瞿靄堂.語言思維與語言接觸[J].語言接觸論集,2004.(1).
[9]朱文旭.彝語句法中的語序問題[J].民族語文,2004,(4).
注釋:
①巫達在其《漢彝“團結話”與彝漢雙語教學》(第一輯),1999.一文中認為“‘團結話是漢語的一種特殊變體,它雖然在整體上遵循了漢語西南官話的規則,但在語音、詞匯和語法各方面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彝話的‘烙印”。
②冕寧縣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③汪坤玉、梁德曼.四川西南部彝族使用漢語的歷史和現狀[J].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1)
④“——”表示對此沒有概念,但能用彝語表達出來的詞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