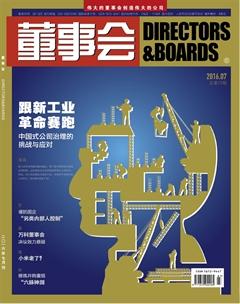合理監管,謹防手“亂摸”
劉輝
監管當局對跨界定增的監管模式,實際上有些類似于當前我國四大自貿區正在試點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僅僅是針對特定行業的定增以及特定上市公司跨界的情形進行“一事一議”,并不是全部禁止
跨界定增這種商事行為本身屬于商法商事主體私法自治的范疇,經濟法對這種市場行為的干預,必須從法律的層面界定權力運行的必要性、國家干預的方式、干預結果的評估以及市場退出的時機選擇等問題。否則,又一只政府“亂摸”的手最終捧出政府失靈的惡果絕非偶然。
原則允許但是例外禁止
也許在不少人看來,跨界定增這種市場主體的自由經營行為理所當然不應當受到法律的管制。從中國證券市場的現實情況來講,過多的政府管制也的確導致了證券市場的低效率和政府失靈的雙重惡果。不僅如此,反對跨界定增的法律規制也不無法理上的支持:因為定向增發本身屬于一種證券的私募發行行為,本質上是上市公司再融資和經營轉型的一種形式,它屬于一種商事行為。而保護商事交易的便捷、促進商事主體最大限度的營利、貫徹私法自治已然成為現代商法責無旁貸的責任,并被商法學界公認為商法的基本原則。顯然,國家對定向增發進行管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市公司再融資的效率和成功率。同時,上市公司通過跨界定增而進入其他的行業,從立足于產業集群發展、增強企業綜合盈利能力、提升行業競爭力和知名度都可能帶來一定的幫助。從傳統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理解,這當然符合商事主體“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因此,國家的干預必須提供充分的正當性論證。
筆者認為,監管當局對跨界定增的監管模式,實際上有些類似于當前我國四大自貿區正在試點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我國自貿區很好地堅持了原則上允許例外禁止的立法原則。在自貿區,外國投資者我國原則上給予市場主體準入前國民待遇,但任何國家的國民待遇都不是不加禁止地全然放開,負面清單恰恰就體現了對原則性規定的例外,在負面清單內的產業和行業,并不給予準入前國民待遇。同理,對于跨界定增,正如中國證監會在5月13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辟謠的內容一樣,監管部門會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公司進行再融資和并購重組,再融資和并購重組的政策仍然沒有變化。而僅僅是針對特定行業的定增以及特定上市公司跨界的情形進行“一事一議”,并不是全部禁止。從法理上講,跨界定增立法盡可能放開對跨界定增行為的約束和規制正好體現了商法的私法自治和保護交易便捷的基本原則。事實上,就在市場正對金融、游戲、影視、VR四個行業定增監管政策議論紛紛的時候,中國證監會依然對升華拜克收購網游研發商炎龍科技擬轉型泛娛樂的并購方案給予了有條件通過。
“社會本位”提供正當性
那么,對于跨界定增這種金融和商事交易行為,法律是否真的不需要介入呢?我們看到,不少上市公司大幅度的跨界,除了成為短期刺激股價的有效事件,長期經營來看,并未達到并購的預期,或者遠遠低于之前對賭協議約定的業績承諾。比如,鑫科材料于2015年6月5日公告收購西安夢舟100%的股權,將西安夢舟作為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納入合并報表。根據業績承諾,西安夢舟2014-2016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利潤應分別不低于1億元、1.4億元和1.94億元,三年累計業績達到4.34億元。但公司僅在前三季度業績就虧損了近億元。
因此,單純地尊重私法自治原則和保護交易便捷,并不能對跨界定增這種融資加并購的經營轉型行為進行有效的規制。在商法之外,應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由國家基于社會本位原則對跨界定增行為進行統合規制。法律的本位是指,法律對社會關系進行規范的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經濟法能夠跳出商法的私法屬性,基于社會本位,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社會關系進行規范。
就跨界定增這個領域來說,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原則的貫徹,是有效處理單純的商法規范的負外部性的良方。基于社會本位,一方面要處理好的是單個上市公司再融資與整個資本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如前所述,很多上市公司把跨界定增作為一個題材,打著“市值管理”的旗號,介入當下熱門的互聯網金融、游戲、影視、VR等行業,這顯然是加大整個資本市場泡沫的炒作行為。因此,在這些熱門的新興行業,對于一些傳統行業出于炒作動機實施的跨界定增必須予以禁止。比如,一家從事房地產的上市公司要去跨界做影視,其原有主營業務及其跨界能力值得深入進行審查。另一方面,經濟法對于跨界定增行為,必須處理好上市公司再融資與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保護的問題。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制體系主要由《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構成,現有的法律規定不夠完善,而根據中國證監會對外透露的信息,新的有關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的管理辦法正在征求意見,有望對跨界定增行為進一步進行規范。從現有制度來看,操縱定向增發的價格、定向增發中注入劣質資產、定向增發中注入資產價值虛增以及定向增發中的套現行為應成為將來需要進一步完善的重點規制對象。
“窗口指導”尚需法制化
還有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是,目前中國證監會對跨界定增實行“一事一議”的窗口指導行為的規范化問題。在金融行業,監管部門的窗口指導是市場上所熟知的一種特殊行為。從行政法基本理論來說,窗口指導屬于行政指導的范疇。行政指導起源于“二戰”后的日本,目前在歐美國家則被廣泛稱之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金融領域窗口指導的廣泛使用是有其重要原因和背景的:金融宏觀調控帶有重要的相機抉擇性特性,市場瞬息萬變,窗口指導的靈活性特征能夠滿足行政當局的調整之需。由于行政指導本身就是行政機關在其職能或職責范圍內,為實現一定的行政目的,而謀求當事人作出一定行為或者不作為的指導、勸告、建議及其他不屬于處分的行為。因此,可以看出窗口指導本身是不具備強制性的,窗口指導的行政相對人如果違反窗口指導本身并不承擔法律責任。再有不容忽視的一點是,我國現有窗口指導立法的空白也導致了行政機關窗口指導行為的隨意和泛濫。
對于跨界定增的窗口指導,我們建議,一方面應對窗口指導的基本原則通過立法的形式規定下來,因為盡管窗口指導是相機抉擇的,但窗口指導的基本原則卻是保持相對穩定性的,法律對其進行明確有利于規范監管機關的窗口指導行為;另一方面,窗口指導是“軟約束”,但這并不代表監管部門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而隨意為之,當監管部門對跨界定增的窗口指導出現偏差,導致整個市場低效率和特定上市公司及其投資者權益受到侵害時,監管部門應承擔法律責任,并給予相關主體訴權予以保障。也就是說,監管部門對跨界定增法律規制的效果需要進行監督和評估,并在適當的時機放開對特定行業跨界定增的約束。防止國家適度干預之手演變為“亂摸”的手,從合理介入演變為政府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