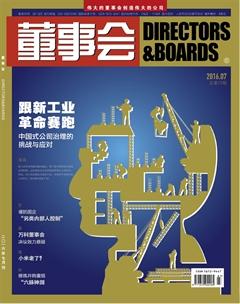“人造大企業”何時休?
馮立果
青年經濟學者。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博士后,目前重點研究大企業和體制改革
人造大企業內部的活力資源越來越少,低效無效資產越來越多,內部治理結構、激勵約束機制沒有本質改變。有的企業從單個的小型虧損企業變成大型虧損企業,甚至人造大企業的名錄就是一個虧損企業排行榜
中國人第一次知道歐美國家有大企業,大多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出現了許多行業性壟斷組織如卡特爾、托拉斯、康采恩等。當然,這些企業組織在中國人印象里基本是負面的。然而隨著社會認識逐漸加深,中國人知道國外還有一個叫做World Fortune 500的企業排行榜,里面凈是些巨無霸型的大企業,這些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做生意,富可敵國。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常常想:中國要是有這么幾家就好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確立了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后,國人對歐美國家的這些大企業也不再以過去的意識形態看待了,各地方政府都以能招商引資到這類企業為榮;國人出于民族主義感情,也夢想著國內能早日誕生幾家世界級的大企業。
從歐美國家大企業角度說,它們大多數是從小企業起步,在市場競爭中不斷成長變大,最后經過并購重組而成為世界最大500家企業的,因此它們的“大”,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企業擁有較強競爭力的反映,“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強”。實際上,Fortune 500本身是按照營業收入排名的,是世界500大,但國內在引入這一概念時,有意把它翻譯成了“世界500強”。后來國內又學習財富雜志的方法,排出了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等,實際上也都是“500大”。
直到本世紀初,Fortune 500中還沒有幾家中國企業。正在決策者和公眾都還在夢想、呼喚有更多中國企業進入Fortune 500的時候,幸福快速到來了。大概2003年前后,中國工業化進程進入以滿足“住、行”需求為目標的新階段,大規模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推進,大量重化工如煤炭、鋼鐵、化工、建材企業隨之涌現。它們紛紛上榜Fortune 500。到2008年,中國大陸企業已經有26家上榜。當然,在較長時間里,上榜Fortune 500的中國企業都是過去有行業管理職能的中央企業,直到2008年底,河北省合并了三家特大型國有鋼鐵企業,新成立的河北鋼鐵集團按照營業規模很容易就進入了2009年Fortune 500。這開啟了一個創造“世界級大企業”的“捷徑”。此后,地方政府紛紛效仿,互相攀比,把轄區內的國有大企業“合并同類項”,組建出許多“人造大企業”,比如河南煤化工集團、河北省的冀中能源集團、山西省的五大煤炭集團、山東鋼鐵集團、天津渤海鋼鐵集團等等。中央企業之間也紛紛合并重組,或者到地方兼并重組,規模越來越大。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造大企業”上榜Fortune 500。國資部門、各地方政府都以此為政績。
通過組建“人造大企業”,行政長官有了“打造世界級企業”的政績,地方政府轄區內擁有了自己的世界500強企業,很有面子。但“里子”卻一點也找不到。第一,“人造大企業”的內部整合遲遲難以完成,有合并而無重組,資源仍然分散在合并之前的各個公司,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合并起來的若干個企業只是前面的抬頭變一下,內部原來是怎么運行,合并后還怎么運行,管理效率不但沒有提高,甚至還由于管理層級的增加而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有的“人造大企業”,合并的企業之間沒有絲毫行業共同特點,歷史不同,甚至價值觀和企業文化也有巨大差異,被“拉郎配”后不但難以整合,還容易形成“獨立王國”。過去很多年這種合并重組造成了很多“夾生飯”。第二,人造大企業內部的活力資源越來越少,低效無效資產越來越多,內部治理結構、激勵約束機制沒有本質改變。有的企業從單個的小型虧損企業變成大型虧損企業,甚至人造大企業的名錄就是一個虧損企業排行榜。合并前的每個企業都是既得利益者,有活力的企業被拖垮,困難的企業更困難。第三,人造的世界級大企業,其經營范圍甚至連省的行政區域都沒跨出去,更別談國際化。華為總裁任正非說,投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式擴張,建一個鋼鐵廠,再建一個鋼鐵廠;另一種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給人類帶來火,讓人類生活實現了革命性的改變,這就是創新。許多行政長官熱衷于制造“人造大企業”,對于企業本身不會有質的改變,對所在行業的有效競爭局面、國民經濟的提質增效和創新型國家建設更不會有幫助。“人造大企業”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