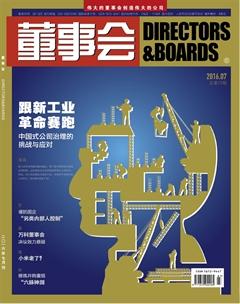藝術品市場要嗎啡,還是苦口良藥?
馬健
中國藝術品市場正處于瓶頸期。一方面,長期以來的粗放式增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形勢下被放大并凸現出來;另一方面,在互聯網發展的沖擊和藝術品金融化的過程中,中國藝術品市場也存在著轉型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只有恰當地解決短板與問題,才能引導未來中國藝術品市場良性發展。那么,中國藝術品市場究竟處于什么境況?面臨何種問題?應該如何突破?
衰敗,還是深度調整?
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這一輪深度調整屬于經歷過一輪資產重估后的正常的周期性調整,是估值中樞下調的過程。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宏觀經濟和投資市場行情表明,除了古董、藝術品和郵幣卡等另類資產,股票、土地、房地產和大宗商品等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同樣經歷過波瀾壯闊的資產重估過程。
就市場本身而言,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十余年來的高速發展,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對文物藝術品拍賣公司設立條件的放松管制——由較為嚴格的審批制變為相對寬松的登記制。一大批藝術品拍賣公司的成立就直接受益于此。另一方面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藝術品需要通過拍賣的方式進行首輪“二級市場”的大規模換手——不少備受關注的“天價”拍品就出自此輪換手潮。
供給需求彼此嫌棄
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此輪深度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給側方面出了問題。一方面,中小型拍賣公司的拍賣會越來越難辦。據不完全統計,與2014年同期相比,約一半的北京拍賣公司取消或延遲了2015年的藝術品春拍和秋拍。另一方面,拍賣公司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近四年來,北京保利、中國嘉德、北京匡時等10家拍賣公司的年成交總額基本上穩定在150億-200億元之間,同期的全國文物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則基本穩定在300億-380億元之間。這意味著,在這一輪的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大洗牌過程中,由于優質拍品資源稀缺,一些實力較弱的中小型拍賣公司已經由于拍品征集能力較弱而處于了市場邊緣。對很多二線拍賣公司而言,年真實成交額能夠破“億”已經成為決定公司前途的生死平衡點。總之,在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藝術品的首輪大規模換手潮結束之后,精品、生貨、硬貨的征集難問題已經成為了拍賣公司普遍面臨的“老大難”問題。
從需求端的角度來看,需求的結構性不旺也是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深度調整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受供給側缺精品、缺生貨、缺硬貨的影響,很多“老錢”感覺沒有可花之處。但只要拍賣公司能夠提供有價值的拍品,依然會受到市場的熱捧。精品夜場和特色專場的熱度就并未受到市場環境的太大影響。另一方面,前幾年入市的“新錢”卻普遍發現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錢并不像一些媒體和某些專家所鼓吹的那么好賺。尤其是在中國藝術品市場高位運行時抱著“短、平、快”心態入市,甚至負債投機的“新錢”,面臨著市場腰斬行情、交易成本太高、負債成本不低、回款周期偏長等一系列問題。例如,2010年曾以4536萬元創下王鐸書法世界成交記錄的“天下第一王鐸”——《雒州香山作》在2016年僅以3550萬元落槌。先吃螃蟹者的財富縮水現象當然產生了比較負面的放大示范效應。
弱市是機制變革最佳窗口期
中國藝術品市場自新世紀以來的迅猛發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可是,很多隨之而來的問題并未能在發展的過程中以發展的方式得以解決,甚至還日益嚴重,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藝術品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最為突出的有兩大問題:
一是稅收機制。中國藝術品市場多年來的高速發展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值可謂不成正比。所謂的“一級市場”幾乎收不到什么稅,所謂的“二級市場”則一方面存在重復征收營業稅的問題,另一方面存在難以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問題。這固然同目前的稅率設置和稅收機制不合理有關,但很多納稅人對納稅義務的認識也大有問題。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稅制改革,必須在考慮到行業特點、征稅成本和配套服務等諸多因素的基礎上,設定適當的稅率,提供消費者保護,從而在降低稅率的同時實現稅收總額的凈增長。
二是約束機制。中國藝術品市場是一個幾無硬約束,又缺軟約束的市場。從藝術家繞開簽約畫廊直接私下賣畫,到畫廊因市場趣味的改變而輕易毀約,再到拍賣行知假拍假但買家維權無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節點上,幾乎都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當然,藝術家或經營者本身都很難做到自律,必須有第三方機構——藝術品行業協會的介入,才可能有效實現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共同治理。總之,一個健康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必須有一套能夠約束參與各方行為的市場機制,才能保證市場的健康運行。
從邊緣切入進行“微創新”
對中國藝術品拍賣公司來說,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必須花大力氣進行創新和轉型。
一是積極擁抱“互聯網+”。網絡拍賣既是降低長期運營成本,從而降低拍品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也是縮短交易時間,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途徑。從提供入門體驗和培育潛在市場的角度來看,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不僅需要“高大上”的春秋大拍以及相關夜場和專場,而且需要接地氣、高頻次、快結算的網絡拍賣。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盡管一些拍賣公司已經敏銳地意識到網絡拍賣的重要性,并且正在積極探索。然而,為數更多的拍賣公司還處于觀望和糾結狀態。事實上,拍賣公司的“互聯網+拍賣”未必一開始就進行大張旗鼓的變革,不妨先從邊緣切入進行“微創新”。例如,藝典中國首創的藝術品交易數據的實時同步網絡報價系統——“同步拍”就是傳統的電話委托拍賣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升級版。諸如此類的微創新,不僅能夠同傳統的拍賣方式有機融合,而且可以為客戶提供更豐富、更深入、更便捷的參與式體驗。
二是積極探索“金融+”。近年來的藝術金融創新主要集中在產品上,很少涉及企業。事實上,拍賣公司既是藝術金融產品創新的最佳企業主體,也是財務投資者參與藝術品市場的最佳投資對象。首先,拍賣公司的藝術金融產品創新可以有效規避金融機構創新時所面臨的因專業門檻而產生的一系列道德風險和交易成本。其次,拍賣公司的藝術品消費信貸等特色金融服務既可以增加藝術品的流動性,從而推動和維持市場繁榮,也可以提升服務質量和增加利潤來源。最后,拍賣公司不僅是最適合上市融資的文化企業之一,而且是廣大投資者通過資本市場間接分享藝術品市場長期回報的有效渠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現行《拍賣法》的限制,最可行的拍賣公司金融化之路就是在成立包括拍賣部門、經紀部門、金融部門等在內的綜合性文化產業集團的基礎上謀求上市融資發展。
重樹“三觀”釋放市場活力
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創新與發展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三種觀念。
一是新的市場觀。在藝術品市場上,人們通常將畫廊稱為“一級市場”,將拍賣行稱為“二級市場”。這其實是生搬硬套西方藝術品市場結構的教條主義。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結構要復雜得多,遠非“一二級結構”可以簡單概括。假如市場參與者還囿于這種想象中的藝術品市場結構,或者看到一二級市場邊界正在模糊便感到疑惑和擔憂。那么,創新的高度、深度和廣度都是極其有限的。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創新必須要有推倒重來,不被固有觀念與歷史包袱所束縛的心態和勇氣,才可能有大的突破。
二是資源組合觀。不少業內人士在談到信息技術和金融機構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影響時,依然將其視為一種挑戰原有市場結構的不友好力量。事實上,無論新技術,還是新制度,都是一種資源。舉個簡單的例子,藝術家畫室有畫,居民家中有需求,商業銀行有資金,網絡公司有平臺。藝術品交易的主要條件都具備,卻未能實現供需的互通和平衡。為什么?因為要想實現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發展創新,各種分散的資源就必須被有效地組織起來。只有當各種資源被組織起來了,潛在的交易可能性才能變成現實的交易額。因此,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參與者應該以資源組合的心態看待和接受這些外來的新資源。
三是創新層次觀。創新有層次之分。從宏觀政策、中觀市場到微觀企業,都存在創新的空間和可能。從宏觀政策層面來看,需要從頂層設計的高度,通盤考慮、深入探討和仔細推敲中國藝術品市場管理的瓶頸和痼疾。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主動傾聽問題,積極調查研究,加大改革力度。從中觀市場層面來看,需要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出發,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產業智庫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綜合考慮中國藝術品市場參與各方的利益,提出經過利益整合之后具有可操作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從微觀企業層面來說,藝術品經營企業是對產業趨勢和供需變化最為敏感和最具活力的微觀創新主體。正所謂“無企業,不市場”。藝術品經營企業的不斷試錯將為中國藝術品市場探索出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作者系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創意產業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文化管理協會藝術品市場管理委員會理事、中國文化產業智庫專家、文化部文化藝術人才中心培訓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