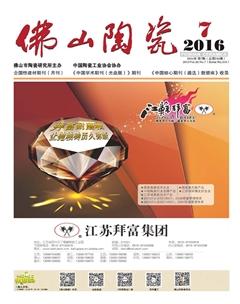淺談宜興紫砂工匠與文人藝術
許清
摘 要:作為特種工藝品以紫砂與文人的關聯最為突出名流名工會敘一起,或討論壺藝,共創新作;或以自己的書畫詩文,裝飾壺身;更有甚者直接參加了陶土的創作活動。舊話重提,只為解脫壓抑著人的機械的賞壺觀、談藝觀,讓紫砂藝術永葆青春。
關鍵詞:紫砂;名流名工;砂壺書畫鐫銘
1 前言
紫砂工以壺為身,壺以精制者言,歷來作為特種工藝品以紫砂與文人關聯是最為突出,砂壺名工受到文士的殷勤接待也是其他工匠所不能及,名工時大彬與樓東名士,徐友泉與宜興吳氏,蔣伯與項子京、陳眉公,這些都說得上交誼純篤,特別是清初的陳鳴遠,他的游踵所到之處;文人墨客,都延之如上賓,如桐鄉汪氏、海鹽張氏、海寧陳氏、楊氏、曹氏都曾設館相待,其中楊中允和陳鳴遠訂交最契。
2 紫砂工匠與文人
名流名工會敘一起,有討論壺藝,共創新作,有以自己的書畫詩文裝飾砂壺,后人譽為“名工名士,允稱雙絕”的珍品。
另外,一批詩人畫家,特別愛好砂藝,如趙宦光、董其昌、潘允瑞、鄧美、顧元慶、陳煌圖、蔣之翹、唐仲晁、鄭板橋、蔣升瀛、汪淮、屠倬、郭頻迦、瞿應紹、鄧符生、吳大徵、張繼直、任伯年、胡公壽等,都以書畫詩文傳名后世。紫砂陶與文人如此密切,那必然在砂壺上呈現出濃厚的文人味,文人味就是在壺藝中增加了文學要素,壺銘盛行就是明顯的傾向。
壺身鐫銘,按周高起曰:“大彬”,前面提及的“且吃茶”,在壺身上刻幾個字說不上文人意趣,也算不上文學要素,但文人的詩畫,刻在壺上遠遠超過了裝飾作用,而是反映了世界觀,如:六十四研齋藏時大彬壺,底鐫銘曰:“一杯肖茗,可沁詩脾”—《松研齋隨筆》。沈子澈所制菱花壺銘曰:“石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陽羨名陶錄》。
陳用卿紫砂壺鐫,“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又一壺銘曰,“瓦瓶親汲山泉水,沙帽籠頭手自煎”—《砂壺圖考》。
玉勺山藏陳鳴遠壺,底銘“汲甘泉,渝芳銘,孔顏之樂在瓢飲”,《陽羨陶說》由于銘刻盛行,書法在壺藝身上也被帶動起來,如:張示未得時大彬壺詩云:“削竹鐫留十字銘,居然楷法本黃庭”;“蒸子畦書法,有晉唐風格”; “項不損字法晉唐”;“鄭寧候書法也工”;“惠孟臣筆法,絕類諸河南”。
上述幾家在書法方面成就較高,在當時一般名手都注意書法,即使自己不擅長此道,一壺制成也必請善書者代為銘署,如陳辰(共之),汪大心諸人,均是“陶中之書君”,專門替壺工們代鐫書畫,一代風流,才會產生這些書家來。
文人不但影響砂壺的創作,而且直接參加了陶工的創作活動。清朝嘉慶年間,金石家陳曼生與藝人楊彭年合作,陳曼生幕友江聽香、郭頻迦、高爽泉、查梅史等也以與壺銘,書畫撰刻,自此稱曼生壺,自此后一度對砂壺的評價置壺藝而不顧,而發展到喧賓奪主的地步。
紫砂工藝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曾一度出現華麗工巧的宮廷風格,加王南林、邵友蘭、邵基祖、陳漢之、邵德馨、邵玉亭等都很著名,作品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
3 總結
今天不惜筆墨經驗,重說舊話,老生常談,為的是解脫壓抑著人的機械的賞壺觀、談藝觀,而讓人們返樸歸真,不去機械地對待藝術品,以歷史作鏡鑒,讓制壺者與珍賞者多溝通,多些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