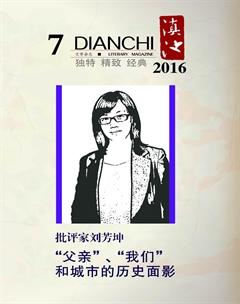麻青石 (散文)
敏洮舟
我家在城南。

溜出家門,拐出一條狹窄的小巷,就到大街了。街角有個廢棄的院子,以前是客運站,四方四正的,北邊蓋著一排八十年代的青瓦房,房前整齊地隊列著十幾棵身形蒼老的白楊樹。樹歪著頭,斜著身,擲出一片斑駁的蔭涼,里面有風,風里藏著我的童年。
有段時間縣城改造說要動遷,很鬧騰了一陣,結果客車被遷走了,可改造遲遲未動。客運站就被閑閑地空置在那里,成了一個日漸荒蕪的廢院。只有客運站鐵門上那幾個剝落了朱紅的大字依然遒勁——“城南公共汽車站”,寂寥地憑吊著已逝的繁華。其實也未空置,后來招來了一班光棍閑人、市井小販整日下棋閑侃、小倒小賣,院子反而熱鬧了。當然,時不時的,也會出現我這個“學生”的身影。
小時候去客運站,只是為了逃學。清晨起來,母親給我煎個荷包蛋,吃過之后抹抹嘴,開溜似的上學去了。母親不知道,我已經把客運站變成了專屬我的“學校”。那排樹成了我消磨時間的處所,整日爬上爬下,穿梭其間。爬上去就在樹彎里躺著,望著湛藍的天空中那一朵朵棉花似的白云,心想那要是棉花糖該多好。爬下來就坐在樹蔭下的一塊碩大的青石旁邊,聽一個老先生講古今。如果去掉這些零碎的光陰,我的童年就是殘缺的。近日忽然有所意味,以前對客運站那種莫名的親近,除了逃學,或許里面還藏著些隱秘的東西,比如是在等待一些故事的發生。
院子里最誘人的不是正午的陽光,而是白楊樹下那一溜干爽的陰涼。院子最東邊的那棵白楊長得恣肆張揚,樹旁就是那塊碩大的青石頭,夏天陽光炙人的時候,躺在上面又舒適又涼快,更湊巧的是,這棵年歲蒼然的老樹虬根外露,一截不安分的根須竟然向上生長,也不知被什么人攔腰截斷,剩余的部分像一根圓柱,剛好用來置放茶壺。這棵樹和這塊青石頭,是我最喜歡的、擅長講古今的那位老先生的專用領地。
他叫麻五十。
麻五十有一個制作粗糙的紫砂壺,有人沒人總端臥在樹樁上,像是替他守護領土。哪個不長眼的敢靠近這塊青石,保準招來一頓臭罵,被罵的人忿忿不平:這青石上又沒刻你的名字 ,憑什么給你一人霸占著?可細細一看,那油潤光滑的石面上似乎真能看出些麻五十的身影。麻五十在這塊青石頭上已經消磨掉幾十年光陰了。
不管上午下午,只要頑性一發,我就來到這院子“上學”,然后站在院子門口打量并不熱鬧的街道,一眼就可以看出誰是這院子里的常客。每天來院子“上班”,他們各自有一個固定的隨身工具,或拿著棋盤或掌個鳥籠,或倒提著板凳腿一步一晃,一串溜就從那個小巷中走出,然后優哉游哉地踱著方步朝院子走來。
其中穿著中山服、紐扣系得整整齊齊、手中托個紫砂壺的就是麻五十。雖然深藍色的中山服已經洗得有些泛白,五顆扣子中掉了再補替的兩顆顯得有些扎眼,但從他修得無一根胡茬的瘦臉,梳得連蒼蠅都趴不住的大背頭,擦得光鑒照人但嚴重走形的三節頭皮鞋上可以看出,他是個講究人。
麻五十進院子總將腰板挺得很直,闊步行走時左顧右盼,頻頻向人點頭示意,盡管別人沒有招呼他,甚至連看都沒看他一眼,但他依舊保持著多年的習慣。走到那塊青石旁,看著石面上飄落的一層薄薄的塵土和幾點凝固的鳥糞,麻五十先皺皺眉頭,然后仰天沉思一會兒,再壯壯聲嗓說:“唉,這院子真不衛生,早知道,就跟張主任喝早茶去哩。”說完慢條斯理地撣撣青石上的塵土鳥糞,再咪上一口紫砂壺,繼續仰天沉思。周圍聽了或偷笑,或鄙夷,或搖頭不理。這情景其實也持續了很長一段光陰,人們都見怪不怪了。
院子里的人最喜歡跟麻五十下棋,或者說,最喜歡“聽”他下棋。我就是其中一個。雖然到現在,我的棋藝依然很爛。下棋的時候,麻五十才愿意從屁股下的青石上離開一會兒,走到棋盤前,他總是很嚴肅地跟對手說:“手談是一門藝術,大腦的藝術,每走上一步高棋,都是在創造藝術哩,所以我希望你能慎重地對待即將出現的藝術。”
未料,走不上十幾步,他就被人一個馬后炮套殺,輸掉將軍后,麻五十又一番說辭:“唉,四下里太吵哩,藝術創造總需要靈感吧,靈感不會來這種胡里麻搭的地方。我小時候跟我阿達(父親)手談,經常坐在西安買來的純毛毯子上,旁邊白銀火盆里炭火燒得很旺,景德鎮燒制的青花瓷杯里飄著龍井的茶香。在那種環境里,我的靈感才來呢。”他說得神情陶醉口沫橫飛,旁邊的年輕人互相擠眉弄眼,朝他身上的衣服鞋子撅嘴。年長的人卻知道這不是虛假話。
更多的時光,麻五十是在青石上打發的。他盤膝一坐,偶爾從伸臂可及的樹樁上端過紫砂壺咪上一口,然后清清嗓子,繼續神侃開來。青石周圍,全是些游手好閑的少年娃,當然,也有托著下巴聽得正入神的我。看著下面的娃娃們一個個聽得悠然神往,有識相的再時不時追問上一句,麻五十就侃得更來勁了。
閑侃的內容繞來繞去都是他們麻家幾十年前的老黃歷。說他爺爺生前的生意規模大得很,光黃金有十箱,袁大頭就數不清了。他父親的時候,整個城南都姓麻。
有娃娃不信,說他吹牛,他就使勁拍拍屁股下的青石,然后很生氣地甩甩頭,說這青石頭就是證明,它是很有些來歷的。大概在清代的時候,一位縣令給小妾修花園,造假山缺少一塊巨石,某鄉紳為了討好縣令,托熟人從異鄉運來獻給了他。輾轉數十年后,清政府滅亡,這塊巨石也隨之流落民間。
有個買雞蛋的老人一直蹲在旁邊,聽到這里,他插嘴說:“不是流落,它是被人從國民黨政府大院(前清縣衙)買走的,價錢貴得很哩,值了一千個坨子(袁大頭)。買它的人姓麻,是南門上有名的有錢人。”麻青石聽后,頭昂得更高了,他接著話茬說:“青石像一頭牛一樣臥在我家院里,我先人左看右看也不知道能用它做啥哩,最后吩咐人手(下人)洗完衣裳就晾在石頭上。”說完后,他傲然拉拉衣領,抖抖衣袖,可神色之間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落寞。
后來又從別處斷斷續續地聽到,麻五十的先人將青石買回家的幾十年后,全國開展整風運動,號召“破四舊”,青石列在被破之列。“地富反壞右”,麻家榮登榜首,抄家游街,從此一夜赤貧。麻鄉紳不堪折磨,在五十八歲時丟下老來子撒手人寰,這個打小被千嬌萬寵的小兒子當時八歲,名叫麻五十。
時間飛奔一樣,轉眼就跑過幾十年,麻五十也將童顏熬成了鶴發。親戚鄰里曾讓他一起出門做些小買賣謀生,他總是把頭昂得高高的,笑而不答。旁邊,麻青石靜靜的。就這樣,身邊的親戚鄰里日漸紅火,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其中還出了幾個大老板。可麻五十依舊兩袖清風,既沒妻室,更無子嗣。偶爾有三五個熟人打趣:“麻五十,一個人睡覺,小心把炕滾塌嘍!”麻五十總是嘿嘿一笑,然后拍拍屁股下的青石說:“放心,地基硬著哩!”熟人們聽了相視一笑,或悄然嘆息,地基再硬,也是明日黃花,與你何干?
用麻五十的話來說,這塊青石也姓麻,是他的長輩。加上當地人大都知道這塊青石頭的來歷,便戲稱它為“麻青石”。麻五十數十年如一日,朝夕不離地守護著它。因此,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麻青石”也成了麻五十的另一個姓名。在年少的一輩人里,說起麻五十知道的沒幾個,但“麻青石”卻是人人皆知。
最后一次見到麻五十,我已是個四處漂泊的人,偶爾回趟家,總是不忘到那院子里轉轉,不光因為逝去的童年,依稀的念想中,總是隱約著一個鮮活的身影。回家得知,縣城改造沉寂了幾年后,終于有了動靜。城南廢置的客運站院子被列在第一批拆遷計劃中。
吃過早飯,猶如鬼使神差,我徑直走向了那院子。
在我之前,麻五十和他的紫砂壺已經散步在白楊和青石周圍。看得出,白楊樹上新發的嫩芽讓麻五十的心情格外舒暢。我走上前去和他搭訕,他不接我的話茬,只是自顧自地喃喃低語:“小時候一到開春,我阿媽都會給我穿上新縫制的質地優良的綢衫子,冬天的棉衣全讓人手拿去洗咧,洗完之后就晾在‘麻青石上。我也會坐在青石的另一面,連棉衣一起曬日頭……”說著說著,他就情不自禁地哧哧笑出聲來。與他的笑聲同時響起的,還有院子外傳來的轟轟的機械聲,麻五十的笑聲被淹沒了。
一臺挖掘機和十幾個工人進入了院子,他們對我和麻五十說“讓讓、讓讓”,然后團團圍住青石左看右看,麻五十踱著方步慢條斯理地問:“咋樣,沒見過這么大的石頭吧?”工人們頭也不回地說:“是,還真沒法挪出去,只有打眼炸碎它。”
“啥,炸?我看誰敢動?”麻五十伸開雙臂,攔在青石前面,鼻孔噴氣如老牛。
工人們面面相覷,然后互相使個眼色,一擁而上,架住了麻五十。麻五十動彈不得,眼睜睜地看著青石的渾身上下被打滿了深孔,眼淚唰唰就下來了,仿佛隨著那一錘一鑿飛濺的不是石屑,而是他的碎了的心。麻五十看著麻青石,我看著麻五十,心里閃過一絲悲戚。
一切就緒后,工人們架著麻五十朝我吆喝一聲,一起避到院子外面了。過不多時,在一聲轟然巨響中,青石粉身碎骨,麻五十隨即昏倒在地。
一個月后,院子里的那些舊瓦房已被夷為平地,連那些頗有年歲的白楊樹也受了株連,只剩一截截禿根赤裸裸地被陽光暴曬著。最粗壯的那截樹根旁邊,壘著大大一堆碎青石,個個都有狗頭大小,建筑工人們專稱這類石頭叫“狗頭石”,是打地基使用的最佳材料,和水泥沙子配合使用,術語“漿砌石”。
這一個月里,我時常去院子周圍徘徊,可再也沒有看到麻五十。陽光溫煦地照耀著城南,照耀著空蕩蕩的客運站院子。在院子里送走了無數光陰的那些茶客棋客們,郁郁悶悶地游離在院子門口,來了又走了,走了又來了。
這天早上,有個人來了就再沒有離開。他無力地斜倚在院子鐵門邊,長滿胡茬的臉頰瘦如刀削,口中怪聲怪氣地喊叫著:麻青石、麻青石……一聲高,一聲低,聲音嘶啞,聞者凄惻。他就是麻五十。沒有人知道這一個月他去了哪里,可整個城南都知道,麻五十瘋了。
責任編輯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