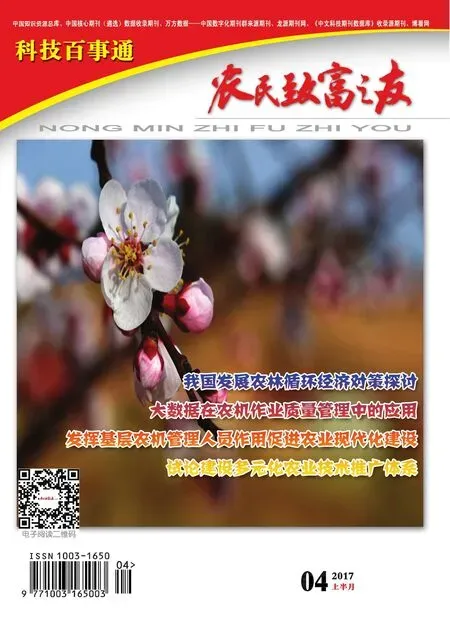制度創新 簡政放權
唐維凱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中國的《種子法》,關系到國家的種子安全、種業發展,關乎十幾億人的“口糧”問題,意義重大。2000年7月8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共和國歷史上第一部《種子法》。而后,經過2004年、2013年兩次重大修訂,2015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種子法的決定。新修改的《種子法》共94條,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本次修改可謂是我國種子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修訂過程復雜曲折,其中,品種登記制度的設立,爭議最大。其最終在《種子法》中得以確立,成為本次《種子法》修訂的最大亮點。
一、新《種子法》中的品種審定和品種登記制度
新《種子法》在第三章“品種選育、審定與登記”中創新地采用了品種審定和品種登記相結合的模式,即:
1、國家對主要農作物及主要林木品種實行品種審定制度,審定分為國家級審定和省級審定兩個級別,審定的標準“三性”為特異性、一致性、穩定性。為保證品種的可追溯性,一是設立品種審定委員會承擔品種審定責任,建立主要農作物和主要林木品種的審定檔案,二是要求種子企業對送審的自行試驗選育種子的試驗數據真實性負責。應當審定的農作物品種未經審定的,不得發布廣告、推廣、銷售。
2、國家對部分非主要農作物實行品種登記制度。根據“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證消費安全和用種安全”這三點來嚴格限制實行品種登記的農作物范圍。應當登記的農作物品種未經登記的,不得發布廣告、推廣,不得以登記品種的名義銷售。
二、單一品種審定制度的立法原意和局限性
原《種子法》規定對主要農作物品種和主要林木品種實行審定制度。按此規定,原則上,種子品種只有經審定合格才能推廣并應用于生產。種子品種登記制度的設立具有其歷史和現實原因:計劃經濟時代影響深遠,市場經濟方興未艾,出于國家農業安全之考慮,強調種質資源特殊性。采用單一的品種設定制度,體現了國家在政策上更重視對宏觀經濟的監管和控制。世界上多數市場經濟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都采取這種政策。在我國, 2000-2010 年水稻、 小麥、 玉米、 棉花和大豆等主要農作物通過國家或省級審定的品種為 6766個, 其中水稻 4058 個、 玉米 1125 個,這說明在特定歷史時期下,品種審定制度為我國種植業的發展和農民增產增收起到了相當的積極作用。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我國市場經濟進程的加快,在種子選育和推廣的實踐工作中,單一的品種審定制度逐漸體現出它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爭議,也成為了《種子法》修改工作中的焦點。
1、種質資源雖具有特殊屬性,但也具有作為商品的屬性,特別是非主要農作物種子。因此,種子的市場準入和應用方式,不僅應由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決定,更應由種子生產者自行決定。原有的審定方式,已經對種子品種的更新和整個種業的發展造成了限制。
2、種子企業作為生產者,對品種能否進入市場進行銷售、應用沒有主動權,而要靠品種審定委員會來決定,這種管理模式束縛了種子企業的手腳,打擊了其育種的積極性,限制了種子企業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大,對整個種業的發展都造成了負面影響。另外,由于企業發展受限,科研水平難以得到有效提升,育種力量分散,育種模式落后,造成品種審定泛濫的局面。其后果是育種質量下降,審定品種大量雷同,造成了種質資源的極大浪費。
3、權利和義務相伴相生。種子選育機構既失權利,義務也隨之免除:在我國,品種選育機構主要包括企業和非盈利機構兩種。其中,大量非盈利性事業單位,如科研院所、大學等,其研發行為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經費來源有一定的公有性。如果在選育品種過程中出現質量問題,其往往很難獨立承擔責任。在《種子法》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政府是制定規則的機關,也是直接參與品種市場準入管理的機關。這種管理模式下,為品種選育機構承擔了其本應承擔的風險。由此看來,單一品種審定制度已造成責、權嚴重不對等的脫節狀況,成為種子質量問題的免責牌。
三、新模式建立的意義及其帶來的挑戰
舊《種子法》經過較長時間的應用實踐,使得單一品種審定制度的缺陷逐漸暴露,新《種子法》中,品種審定和品種登記制度相結合的新模式應運而生。首先,這從根本上體現了國家立法思路額轉變:建立品種登記制度,實現了從嚴格的事前審查,到主管部門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飛躍。這是新形勢下“簡政放權”理念在種子立法實踐中的體現。實行品種登記,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規范和指導,而不是單純的行政管理,這有利于提高登記品種的市場競爭力和市場信譽,充分發揮市場的調控作用。其次,品種登記制度的進入,結合種子來源追溯制的建立,強調種子標簽的真實性,育種者對品種信息的真實性負責,迫使企業嚴把質量關,能使我國的種業市場得到有效的凈化。另外,新模式的建立能促進種子生產者對品種進入市場及應用推廣行為嚴格把關,并提升其創新意識,這能有效改善育種雷同、同質化嚴重的局面,培育出使用壽命更長、性狀更加優越的種子產品。
《種子法》的修訂引起了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集中了社會各界的智慧。其修訂過程艱難曲折,普法和執法任重道遠。一種新制度的建立,其條件的都是逐漸成熟的。在這個過程中,對于執法者而言,將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首先,應當做好學習總結,要把思想行動統一到法《種子法》的新規范上來。一是要求管理部門和管理者應當根據種子法的要求制定和修改出相應的規定和辦法,并做好相關銜接工作,做到法不授權不能為;其次,對于申請品種審定和登記者應依照法律法規辦事,做到法無禁止才可為。
第二,新制度的實施雖然意在“放權”,但隨著權力的減輕,責任卻更加重大。由于新法要求轉變政府職能,明確主題責任,明確了農林主管部門所屬的綜合執法機構和種子管理機構作為種子執法的主體,并賦予其行政強制權,故而應當切實的加強種子品種審定、品種登記制度實施過程中的執法力度,防止新法實施過程中的權力缺位。所謂加強事后監管,重在一個“查”字。新法的實施給了生產者、經營者更多自主空間,同時也拓寬了執法者的工作范圍。各級執法部門應積極研究對策,特別是過渡時期的具體工作方法,及時總結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第三、在新的形勢下,面臨執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還應加強工商、法院、綜合執法等部門的通力合作。必要時,可以采取聯合執法的方式,保證“事后監管”的及時性、有效性。
參考文獻:
[1]李艷,張曉明,梁超,等,新時期中國種業發展之路,中國種業,2013(8),5-7
[2]聶明建 張雁雯,品種審定制與品種登記制的比較分析,中國種業,201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