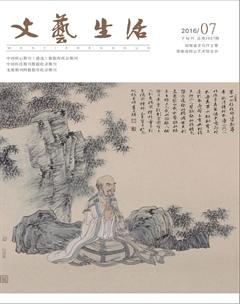影響張生性格演變的動因探究
辛梓
摘 要: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自問世以來便享有高度贊譽,它在《西廂記諸宮調》的基礎上進一步敷演而成,對其敘述情節、人物功能多有繼承。然作為不同背景下產生的兩部“西廂”作品,往往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而再創作的過程中有所創變。這種創新意識,集中體現在對人物的重新塑造上,本文將沿著從《董西廂》到《王西廂》這條線索,對張生性格的演變及其演變動因進行考察。
關鍵詞:張生;《董西廂》;《王西廂》;風魔;志誠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6)21-0003-02
一、張生形象/性格演變文本探析
在仔細閱讀對比《董西廂》和《王西廂》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張生的性格變化具體表現在人物的語言、行為和情感之中。以下,筆者將從三方面的變化入手,對文本進行探析。
(一)圓滑到天然
《董西廂》中的張生,在行事上往往表現出他很現實的一面,往往有諸多考量,甚至利己的盤算,為人處世各方面都做得圓融周到。而《王西廂》中,張生少了幾分精明,多了幾分不加掩飾的天然。這種變化,集中表現在張生初見鶯鶯后墜入愛河,欲留房緡借宿普救寺一段。
《董西廂》中,張生在座談飲茶的時候與老和尚提出要借室。他本是為了通過借宿而獲得一親芳澤的機會,卻在使銀子的時候很含蓄,反倒以借室溫書為障眼法,表現得誠懇恭謙,在僧徒心中留下“僧徒知生疏于財而重于義”的好印象。他顧慮于覬覦大家閨秀的不合禮法,進而對自身的目的性進行掩蓋,同時也使僧人避免因他借室理由有所顧慮,縱使雙方心知肚明,也不必言說。反觀《王西廂》,張生在鶯鶯離去之后,立刻對法聰說要借僧房一間,其目的顯然可見。待到第二日見長老留銀子時,見張生堅持留宿,仿佛心知肚明的說“先生必有所請”,此時張生也并未多做掩飾,唱詞道“【幺篇】也不要香積廚,枯木堂。遠著南軒,離著東墻,靠著西廂。近主廊,過耳房,都皆停當。”這種不加掩飾,正是他性格天然的直接表現,他勇于順應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順勢發聲,不假修飾、不忸怩于可能伴隨的世俗有色判斷。
(二)輕狂到恭謹
在劇情的安排兩本“西廂”大抵相同,但是對于具體行事和情節順序的先后安排卻有差異。這種差異,造成了讀者覽《董西廂》覺張生輕狂,觀《王西廂》知張生恭謹,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體驗。
此點可見孫飛虎圍寺時,張生一段言辭。《董西廂》中鶯鶯欲跳階自盡,張生在一旁大笑且譏道:“婦人女子,別無遠見,臨危惟是悲泣而已。寺僧游客,何愚之甚也!不能止此亂軍,坐定滅亡。倘用吾言,滅賊必矣。”此番言論,一則帶有性別歧視;二則帶有自視甚高的優越感。唱詞更云“亂軍雖眾,張珙看來無物”睥睨五千余賊軍如無物的言論,足見其狂。反觀《王西廂》中,張生言有退兵之策,先請眾女眷回房并加以安撫,獻策后又言“老夫人,長老都放心,此書到日,必有佳音。咱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張生的出現,救老夫人、鶯鶯、寺僧于水火之中,且他的語言行事以及表現出的恭謹態度,不以布衣身份而卑,不以救命之恩而傲,給人一種雖臨危難,但足以信任依靠的感受。《董西廂》中,雖作“請老夫人、大師待望鐘樓之上,兵必至矣”的胸有成竹之語,但流露出的全是對其計謀定成的自傲態度,且對于女眷寺僧的安撫之語并未多見,不斷渲染夸大他自己的功勞,這有違書生恭謙氣質,是一種不和諧的輕狂之態。
再如《董西廂》中,張生數次見鶯鶯便“手撩著衣袂,大踏步走至跟前”,夜聽琴時更是一番粗魯亂抱。而《王西廂》中,張生見鶯鶯只“餓眼望將穿”的翹首期盼,赴宴時候數整儀容。金圣嘆《第六才子書》評第一折《驚艷》云:“然則寫張生必如第一折之文云云者,所謂輕重均停,不得纖痕漬如微塵也。設使不然,而于寫張生時,厘毫夾帶狂立身分,別后文唐突雙文乃極不小。讀者于此,胡可以不加意哉!”此說將此間行為之輕重分析的十分精當。兩相比較,《董西廂》中行為舉止上的極不莊重,將他的輕浮而狂蕩展露無余。《王西廂》中張生知進退、不放肆,行為恭謙,更符合一名知禮書生的人物氣質。
(三)風魔到志誠
兩本“西廂”的唱詞中,都曾反復出現過“風魔”、“志誠”兩詞。筆者以為,以“風魔”概括《董西廂》中張生的精神狀態,以“志誠”形容《王西廂》中張生的追求態度可謂恰當。
《董西廂》中花費很多筆墨去描寫張生的心理獨白,尤其是自處時滿心鶯鶯的心理和行為活動,且這種活動的描寫顛三倒四、語義陳雜,語序排列體現了一種入魔一般瘋言瘋語的狀態。寫張生的生活也是“夜則廢寢,晝則忘餐,顛倒以上,不知所措”。這種具有錯亂感的描寫,帶給讀者一種現實與虛幻交叉呈現,時間絮亂難以區分晝夜界限的感受。情感上受到這種狂態的影響,具有很強的主體代入感。從張生個人的視角出發,寫鶯鶯“髻綰雙鬟,釵簪金鳳;眉彎遠山不翠,眼橫秋水無光;體若凝酥,腰如弱柳;指猶春筍纖長,腳似金蓮穩小”,運用了大量的或遠或近、或整體或部分的視角,對眼中的鶯鶯進行了掃描式的描寫。這種描寫方式,細致到近乎以眼神猥褻的地步,可以說進入了一種風魔的狀態。
《王西廂》在描寫張生對鶯鶯的思慕狀態時,所呈現的不是難以具現化的心理狀態,更多的是寫張生為了鶯鶯日漸消瘦、病入膏肓的“癡”,落筆處多在張生的外部表現上。如寫紅娘破窗紙看張生“覷了他澀滯氣色,聽了他微弱聲息,看了他黃瘦臉兒”,表現的是張生對鶯鶯忠實愛慕又不流于低俗情色的恒心毅力。他心思很專一,情志很單純,是直誠也是志誠。這種描寫程度恰如其分,故沒有《董西廂》那樣精神上的風魔感。
兩相比較,董西廂的觀感整體上很混亂,夾雜了各種或臆想或現實的情感和場景的主觀性描寫。王西廂的則更具有客觀性,能使讀者擁有獨立的閱讀視角以及不同的閱讀感受。
二、張生形象/性格演變動因探究
在“西廂”題材從《董西廂》到《王西廂》的發展過程中,這其中有諸多因素影響了張生性格的再創造。其性格的每一次重新刻畫,都有來自作者、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試論這些因素可以分為語言風格、文學形式和創作動機個方面。
(一)語言風格
《董西廂》中張生性格上給人以風魔、輕狂的感受,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唱詞的語言風格所造成的不同表現力。比如董西廂中對于張生的精神狀態常常用“狂”字,“膽狂心醉”“聞語意如狂”“便發狂言”“眼狂心熱”“一片狂心”之類的字眼。且在“風魔”一詞的使用次數上,《董西廂》比《王西廂》多了兩倍有余,這種具有情緒影響字眼的累加,使通篇文辭走勢偏急,進而造成的語言氣勢不同,帶給觀者以不同的感性體驗。
劉曉玲①指出:“作者在每一次情感波動中都設置了大段獨白語,其中否定句、問句、感嘆句非常突出。”《董西廂》以大量篇幅去渲染描寫張生的內心獨白,在潛移默化中漸漸塑造了一個以風魔狀態為主導的語言環境。金圣嘆在《第六才子書》中,批評明代以來“西廂”劇本中頗多插科打諢、無禮之言時說道:“如是而提筆之時不能自愛,而竟肆然自作狂蕩無禮之言,以是愉快其心,是則豈非身自愿為狂且,而以其心頭之人為倡女乎?”越矩而過度的言行,應可同理見于《董西廂》之中。
《王西廂》在遣詞用句上趨于范式和圓融,加之雜劇體式日益成熟,故少見《董西廂》中那樣肆意連篇的用詞。且《王西廂》“廣引成句入曲”②,句式上化用前人詩句如“有心爭似無心好,多情卻被無情惱”引自蘇軾《蝶戀花》一詞。另外,《王西廂》對于內心獨白的劇情內容也安排得當,避免過度流于精神層面而有失偏頗。綜合得之,其語言風格整體上趨于中正和平。
(二)文學形式
從《董西廂》到《王西廂》,一變諸宮調為雜劇,且將張生為主導的敘事視角變為各為其說的代言體。董西廂中張生的風魔情態,不時表現出來的“狂”與現實利己主義的行為,大抵跟諸宮調的一人唱,全篇乃張生主動視角有關。這種固定視角直接造成了張生內心獨白描寫溢出,形象的過度刻畫。致使無法與觀眾保持距離感,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表現都不分層次的鋪排。譬如老夫人賴婚時,張生內心氣憤,心中腹誹不斷,只是罵老夫人“積世的老虔婆”“打脊老嫗”“婆婆娘兒好心毒”,痛斥其年老無信,有失對長者的尊重之心。
《王西廂》中這一折設為旦唱,以鶯鶯的視角去看張生,見他縱使不快也不口生狂言,觀察他的苦澀情態,“他其實咽不下玉液金波。誰承望月底西廂,變作了夢里南柯”。從第三人視角進行描寫,就避免了張生主觀情感帶來的怨恨一類的負面情緒表現。
如金圣嘆《第六才子書》評《賴婚》一折云:“……然事一事,情一情,理一理,而彼發言之人與夫發言之人之心,與夫發言之人之體,與夫發言之人之地,乃實有其不同焉。……而知《賴婚》一篇必當寫作鶯鶯唱,而不得寫作夫人唱、張生唱、紅娘唱者也。”此說誠是。
《王西廂》中的代言體敘事方式,時而以鶯鶯視角,時而以紅娘視角,能使觀者有選擇的接受來自不同主體對張生的評價。有助于綜合各方觀點,避免主觀敘事的“一言堂”風格。
(三)創作動機
再創作后張生性格的改動,同樣受到時代背景下的文人思想和處境的影響。元代科舉的混亂狀態,文人社會地位不高又無法進仕,只能自謀出路。在這種苦悶不得志的境遇下,文人在創作劇本時,往往會選取一個對象作為寄托,為他們的心聲代言。王實甫對張生的再創作,就體現了他自身對現狀的期許。
《王西廂》在安排劇情發展的時候,有意模糊甚至摘除了《董西廂》中對張生形象有丑化之嫌的細節。例如孫飛虎圍寺時,張生道“夫人與我無恩,崔相與我無舊,素不往還,救之何益?”且無論僧人如何曉之以母女生死情,動之以君子儒生理,他都不為所動。此舉所表現的潛臺詞,與要挾無異。這一段對話,王實甫再創造的時候就予以刪除,從而保證了張生在臨危救難的正面形象性。
《董西廂》中張生雜糅了諸多社會性很強的性格,甚至還有傳統難舍功名這種很世俗的追求,使得張生的形象具有很強的立體感。兩相比較,《王西廂》中的張生雖然漸漸趨于完美和超脫的平面化,于立體感有失,但這種塑造是有其深層動因的。使老夫人在這段愛情中代表絕對的惡,張生則作為正面的一方捍衛愛情。張生對老夫人的質疑,其實是為作者代言向社會質疑。
王實甫將張生塑造成一位文人典范,寄托了諸多同時代文人的期待和追求,賦予他各種現實中難以實現的美好因素,塑造一個愛情完人的形象。這些期許是在才子佳人模式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趨于定式和完美化,一定是品性優良、忠于愛情、才思敏捷和功成名就。
注釋:
①劉曉玲.董西廂語言藝術研究[D].杭州:浙江師范大學,2007.
②袁啟明.張粵民.竟似古人尋我——《王西廂》廣引成句入曲的語言藝術[J].名作欣賞,1985(05).
參考文獻:
[1]王實甫(元).西廂記[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2]董解元(金).西廂記諸宮調注譯[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
[3]金圣嘆(明).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M].沈陽:萬卷出版社,2009.
[4]王莉.《西廂記》中的“張生”形象及其演變[J].天中學刊,2008(01).
[5]袁啟明.張粵民.竟似古人尋我——《王西廂》廣引成句入曲的語言藝術[J].名作欣賞,1985(05).
[6]陳凌娟.西廂故事中老夫人形象演變的原因與意義[J].語文學刊,2010(05).
[7]劉曉玲.董西廂語言藝術研究[D].杭州:浙江師范大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