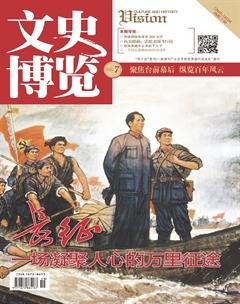故意泄密也是一種戰術
田寶貴
毛澤東曾說:軍事斗爭必須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必須十分才行。但是,由于軍事斗爭的殘酷性和特殊性,其保密過程會出現一些匪夷所思的“反邏輯”現象,即“悖論”。
因故意泄密而得勝
古人說:“成于密,敗于泄。”保密就是保成功,泄密就意味著失敗。但軍事斗爭中卻不乏因故意泄密而保密的戰例。
1800年,法奧戰爭之前,拿破侖為了粉碎盤踞在意大利南部近10萬奧地利軍隊的主力,但又考慮到法軍在意大利的軍團只有3萬兵力,便決定秘密組成一個約6萬人的預備軍團。盡管預備軍團在組建和訓練過程中嚴格保密,但英、奧等國的間諜還是發現了其中的蛛絲馬跡,并將消息公之于眾。
拿破侖意識到,要對預備軍團做到絕對保密已經沒有可能,如果公開“辟謠”更是欲蓋彌彰,于是斷然決定,干脆將組建和訓練預備軍團的消息,諸如編制、實力等經過“有意”加工之后泄露出去。
1800年4月拿破侖又在巴黎放出風聲:法軍已經組建一支預備軍團,且正在法國的第戎地區集結。他將親自檢閱這支新的生力軍。但同時,拿破侖卻將該預備軍團的主力秘密轉移到便于隱蔽的新的集結地,嚴格注意保密,積極強化訓練。而第戎地區只是一些老弱病殘的官兵在裝模作樣地訓練,而且在保密方面也做得煞有其事。
法軍在第戎地區近似烏合之眾的預備軍團,被當時國內外的公開媒體當作笑料而反復刊載。但當奧軍統帥梅拉斯率領軍隊對法軍這支雜牌部隊發起進攻時,卻做夢也沒有想到法軍真正的預備軍團竟然出現在奧軍主力的后方。奧軍大敗,并使第二次反法聯盟趨于瓦解。
因意外泄密而得福
如果說故意泄密是一種策略,常被軍事家、謀略家所慣用的話,那么意外泄密則是保密之不幸、兵家之大忌。但是,事物及其運動總是有其特殊性。陰差陽錯、因禍得福的“悖論”也會在軍事保密領域奇跡般地出現。
1942年美日中途島之戰前,美國小羅奇福特領導的一個特工小組,成功地破譯了日本人的軍事行動密碼。這樣,他們便對日本海軍暗地里進行的情況洞若觀火,并將計就計地部署了自己的各項準備活動。就在這個時候,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芝加哥一家報紙竟將這一機密作為獨家新聞給捅了出去。這令美國軍方非常緊張不安。
按說,這一新聞應該會立即引起日本情報部門的高度重視,進而考慮到更換密碼。但對新聞時常失控、假信息太多的美國報紙,日本的情報部門已經熟視無睹、習焉不察,真的情報也當成假的來看待,最終釀成日軍在中途島戰役中的慘敗。
因刻意保密而失誤
“竊密無孔不入,保密滴水不漏”“保密千條萬條,嚴格落實第一條”。說到保密工作,無不強調嚴之又嚴,慎之又慎。但在實際保密工作中,也會出現因過度保密、刻意保密而導致失、泄密甚至陷入被動失敗的局面。
1869年法國陸軍在預料要和普魯士發生戰爭時,研制了一種新式武器——后膛裝多管機關槍,射速每秒300發,有效射距500碼。這在普遍使用單發步槍的時代,無疑是一件決戰決勝的利器。但拿破侖三世出于保密的考慮,在沒有經過操練的情況下就把這個武器裝備給了炮兵。由于這種武器比較重,必須裝在輕型炮車上,外形也和火炮相似,不明就里的炮兵就將它們當成了火炮,放在離敵步兵較遠的地方使用了,結果沒有打到敵人,反而被敵人的火炮消滅得干凈利索。
同樣的悲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一次發生。二戰前,波蘭政府對不懷好意的德國裝甲部隊有所覺察,并且研制了一種反坦克步槍。同樣出于保密的考慮,這種步槍裝備部隊時,箱子上注明了“偵察設備”和“烏干達”等字樣。這讓人信以為是出口到烏干達的軍品。結果波蘭軍隊還沒來得及開封,就被德軍繳獲。后來,盟軍也繳獲了幾支這種步槍,發現其性能非常不錯,希望盡快仿制,可惜還是因為保密的原因,波蘭政府已經將相關技術資料銷毀得一干二凈。
最終戰爭的結局是,普法戰爭中法軍慘敗,拿破侖三世不僅做了普魯士的俘虜,還要割地賠款。而波蘭則成了德國閃擊戰最早的犧牲品,亡了國。當然,拿破侖三世的慘敗和波蘭的亡國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但這兩件因刻意保密而導致的失誤對整個戰局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影響。
我軍在歷史上也有類似的失誤。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由于博古、李德領導和指揮的錯誤,對于中共中央紅軍為什么要退出中央蘇區、當前的形勢和任務是什么、到底要到哪里去等基本問題,始終是秘而不宣。原因之一就是擔心泄密會影響作戰行動。因此,許多黨、政、軍的高級干部都不知道,對戰略轉移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或準備很不充分,以致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的初期成了大搬家,全部作戰部隊成了掩護部隊。整個中央紅軍一度方向不明,思想迷茫,指揮不力,行動遲緩,其中還經歷了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
軍事保密戰中出現的“悖論”是由矛盾的特殊性決定的,但決不能因此否定保密工作的普遍規律。“保密就是保生存,保戰斗力”。保密斗爭中出現的“悖論”從另一個角度更加說明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嚴格性和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