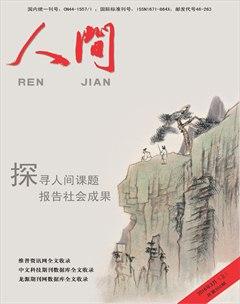“善”與“惡”的化身
摘要:《白鹿原》中,陳忠實塑造了一系列父權制主導下的悲劇女性形象,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則是一位被千夫所指但實際上卻是真正具有著獨立完整心理人格的現代女性——田小娥。她的性格特點最為鮮明對立,因此也最具代表性,其中既有著淫蕩墮落的變態復仇心理,又有著敢愛敢恨、追求自由的反叛精神。因此,本文將從“善”與“惡”的兩個角度對田小娥的形象進行立體分析,進而深入探尋造成這種性格的原因以及其中留給后人的啟示性意義。
關鍵詞:田小娥;悲劇形象;獨立人格;反叛精神
中圖分類號:I207.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3-0000-01
在《白鹿原》這部以男性為主角的作品中,作者陳忠實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塑造了一系列悲劇女性形象,但其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還屬田小娥這一悲劇人物形象,她集善惡于一身,在男權統治的年代,由于受到傳統封建禮教觀念的束縛,即使具有奮起抵抗,追求自由愛情的勇氣,但最終依舊難逃命運的悲慘。
一、“惡”之悲
田小娥性格的鮮明之處首先體現在她異于白鹿原上其他女性的“惡”,這個“惡”的含義并不是道德意義上的大惡,而是指她在傳統男性霸權意識掌控之下,追求一個生而為人的正常女性應有的自由、平等與尊重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不自覺的對傳統封建禮教的抗爭意識。小娥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大“惡”之人,十七歲的田小娥最大的愿望無非就是找一個愿意疼惜她的男人安穩地度過一生,踏踏實實地當一個名正言順的農村小媳婦而已,但就是這樣一個樸素的愿望也被“吃人”的封建禮教所不容。
黑娃的出現喚醒了她追求自由的本能,但正是這一叛逆的舉動,使得她背負上了一個“蕩婦”的罪名,到死,她依舊被認為是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最淫蕩墮落的女子。這一系列對女性的凌辱與損害激起了她的復仇情緒,使得她開始近似變態和瘋狂地報復,以這種自我墮落的方式來宣泄對現實人生的反抗與不滿。然而,田小娥的報復并未隨著她的死而消失,隨之而來便是一場橫掃白鹿原、奪去了無數人性命的瘟疫,這場報復來的更加瘋狂與激烈,以至于多年以后,這么一朵綻放在黑暗中的人性之花依舊被認為是“惡”的象征。
但站在現實的角度加以剖析,田小娥的“惡”是在當時那個封建世俗的環境下,被認為是“惡”的,而并不是其自身有著不可饒恕的“惡”。因此,如果非要按照善惡的標準來進行批判,那最應當被推上斷頭臺的應該是“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小娥的死是封建禮教最終對反叛女性的徹底性泯滅與吞噬,不管小娥是多么的與世無害,她都會遭到世人的鄙視與唾棄,不管男性對小娥怎樣不合理不人道地踐踏,反而都被視作理所當然。傳統宗法制對一個弱女子的道德評價標尺竟是如此的荒謬與炎涼。由此可見,小娥的這種被傳統封建宗法制的枷鎖逼迫出來的“小惡”與宗法制本身的“大惡”相比,是多么的輕如鴻毛,這樣的“惡”里,充斥著太多的悲涼與無奈。
二、“善”之美
小娥本身是善良溫情的,即使被拒入祠堂,不能以一個合法的身份進入白鹿村,她依然無怨無悔地跟在黑娃身邊,即使受到眾人的輕蔑,她依然心甘情愿地與黑娃棲身于村外的破舊窯洞里。她并未主動去加害過誰,沒有偷盜過誰家的任何東西,沒有辱罵過一個長輩,沒有欺負過一個孩子,但依舊逃不過宗法文化的批判,這就是違背傳統“三綱五常”的女性為人所不恥的必然結果。
小娥的“善”是美的,但卻美的太過凄涼,她的悲劇源于其自身對封建宗法制度以女人的貞潔與婦道為評判標準的屈從,在強大的禮教文化的主宰之下,任何逆流而上的反叛行為都會預示著悲涼的結局。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小娥性格中過分的善良與懦弱,使得其在強大男權意識的支配下微不足道、毫無存在感;其次是由于在缺乏正確啟蒙理論指導的情況下,無知淳樸人民對傳統封建道德的反抗具有著根本的不徹底性,這也從另一個方面體現出封建宗法制下的男權文化對女性意識及女性生存具有著強大的殺傷力。
三、結語
應該說人的正常生理情欲是與世俗道德互不相干的,但從客觀的角度來說,卻與當時的傳統道德理念站在了截然對立的兩個方面,所以雖說小娥追求自由情愛原則上來評判并沒有錯,但卻客觀上挑戰了男權文化的底線,最終導致悲劇。深入探尋其中的原委,我們可以歸納出兩點原因:第一,時代的動蕩;第二,文化的沖突。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極其動蕩黑暗的時代,黑暗到可以掩蓋一切毀滅人性的不合理行為,黑暗到可以扭曲一個正常人的性格心理,為了生存免受威脅,妻子可以作為商品隨意買賣,女兒可以作為禮物加以贈送,男人為了獲得社會地位,為了賺取財富,不惜把女人作為可以犧牲的籌碼。女人的生命是如此廉價,甚至到死都沒有說不的權利。
究其根本,還是由于時代文明沒有進步到關注女性需求的境界,因此,悲劇命運的背后,時代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這是時代的悲劇,同時也是文化的悲劇,中國封建傳統禮教以嚴格到沒有人性的方式對女性的命運加以禁錮,女性只能以克己的形式按照文化上規定的軌道前行,當她們委屈顫栗地走到了老年,成為被人尊敬的長輩的時候,又反過來成為幫助鞏固男性權威的迫害者,例如白嘉軒之母白趙氏,這種行為對于女性來說,本身就是一種悲劇,然而卻打著文化的旗號,美其名曰仁義道德,殊不知這更為文化本身涂抹了更多的悲劇色彩。
因此, 《白鹿原》的深刻啟示意義就在于,它從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受到文化沖突的影響,女性的自我覺醒意識被喚醒。現代文化從心理層面上在進行著對人性自由的呼喚,但同時,由于長期以來封建桎梏的限制,導致男女價值體系失衡,現代文明的前進依舊舉步艱難,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實現中國婦女的自由解放,還需要真正領略到現代“以人為本”的文明意識的真諦。
參考文獻:
[1]陳忠實.白鹿原[ 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2]田煒.孟慶千.男權意識下女性的悲劇———淺析《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J].菏澤學院學報,2008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4]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手記[J].小說評論,2007
[5]許官智.從《白鹿原》看女性自我解放意識的覺醒.畢節學院學報,2011
作者簡介:鮑俊杰(1992-),女,內蒙古包頭市人,民族:蒙古族,內蒙古師范大學,學歷: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