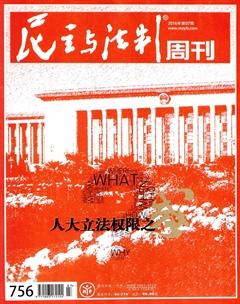要立法民主還是要立法效率?
阿計
民主與效率的兩難選擇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失衡現狀,從表面看是立法權限劃分不清的制度設計不足所致,其實質卻是立法民主與立法效率的深刻沖突。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曾經指出:“立法權力是屬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屬于人民的。”在現代國家,立法權是國家權力的起點,也是制度安排和政治治理的前提,而“主權在民”原則和代議制民主體制,則是奠定立法正當性的基石。在我國的政體框架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相對于其常設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行使國家立法權無疑更能體現“主權在民”原則,更符合立法的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邏輯。
但問題在于,按照當下的人大制度設計,全國人大每年僅開一次會,會期僅在半個月左右,卻需要完成審議“一府兩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審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預算報告等法定議程,承擔梳理議案、討論國是等繁重的議政職能,換屆時還需選舉重要國家機關領導人,如果再加上立法修法任務,更是不堪重負。并且,全國人大代表多達三千人左右,在短暫的會期內,人均發言時間僅約兩分鐘,能夠分配至法律案討論的時間更是寥寥無幾。其困窘正如一位學者所言:“一個巨量規模、多人云集的代議機構,要么陷入眾聲喧嘩、議而不決的困難境地,要么淪入集體失語、指望他人的公地悲劇。”可以說,無論是時間配置、代表素質、參與程度等,全國人大都難以勝任量大面廣、高度專業、程序精細的立法任務。
相形之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般每兩個月開一次會,每次會議均可設置立法議程,可以使立法處于范圍廣、常態化的狀態。同時,改革開放后的歷屆常委會組成人員僅為一百多人,均未超過兩百人,且依法不得在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任職,具有人數有限、相對專職化等優勢,也必然提高了議事效率和質量。這是1982年新憲法正式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正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在憲法修改草案說明報告中所言,全國人大常委會“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
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正式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國家立法權,其首要目的正是為了破解全國人大立法能力不足的困境,以高效、多維的立法,引領法治方向,肯定改革成果,并及時調整轉軌期不斷突顯的社會矛盾。其后的立法實踐,正是沿著這一邏輯不斷演進。比如,截至2011年6月,常委會對全國人大1980年制定的個人所得稅法已作了6次修改,不斷提高個稅起征點,惠及民生利益。再比如,最近十多年來,以簡政放權為導向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此起彼伏,而每次改革方案成型后,都由常委會以“打包”方式對相關法律作出一攬子修改,及時為改革頒發了合法性通行證。不難想象,頻率如此之高的個稅、行政審批等改革,倘若都由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立法修法,勢必遲滯改革進程,進而阻礙民生權益和經濟活力。最近的一個典型例證則是,2015年年底,常委會修改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從而使“全面兩孩”的生育新政以最快速度及時落地,同樣不難想象,倘若修法任務交付今年全國人代會,盡管只有三個月的拖延,也可能耽誤千萬人的生育權利。
歷史已經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廣泛而頻密的立法活動,有效滿足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需求,對構建現代法律體系、推進依法治國居功至偉。但同時應當看到,立法權在現實行使中向常委會的過度傾斜,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稀釋了立法的民意基礎。民意基礎是奠定立法正當性、合法性的基石,而代議機關人數與選民的恰當比例則是民意廣泛性的保障。一百多位常委會組成人員與約三千名全國人大代表相比,其代表性顯然大打折扣,由其代表13億多人口經常性立法,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容易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真實意愿、智慧和經驗相距更遠。”而在立法實踐中出現的越權立法等問題,更是當下法治發展亟待解決的重大挑戰。
一方面,全國人大行使立法權能最大程度體現“主權在民”原則,但又無力應對立法需求;另一方面,常委會行使立法權能有效加快立法步伐,但又難免民意性不足的隱患。立法民主與立法效率之間的內在緊張和深層矛盾,正是當下立法實踐所面臨的一個兩難選擇,也是國家立法權內部權限沖突、混淆的深層原因所在。
“限權”與“放權”的改革難題
如何既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的實現,體現全國人大的主導作用,使立法最大程度地反映人民意志,同時又立足現實國情,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足夠的立法權限,以適應改革和法治的進程,是當下法治建設不可偏廢的雙重價值追求。這就需要合理平衡立法民主和立法效率,但要實現這一平衡,殊非易事。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學界圍繞國家立法權內部權限劃分所發生的討論爭議、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大致可分為“限權”和“擴權”兩個方向。
所謂“限權”,是指通過劃清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各自的立法權限范圍,對常委會立法權作出嚴格限制。比如在修法權方面,明確基本法律原則上只能由全國人大修改,常委會只能在特定情形下修改一小部分基本法律,并且必須得到全國人大的授權。
而“放權”方案,體現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思路。一些學者主張,全國人大只保留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權限,將其他立法權限完全剝離出來,全部賦予常委會。歸納其理由主要是,在國家立法權層面,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的都是“一級”立法體制,而我國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同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模式,將原本完整的中央法律人為分割成不同層次,形成了事實上的“二級”立法體制,由此必然帶來立法權限混亂不清、法律沖突難以解決等諸多困惑。與此同時,在立法實踐中,常委會不僅承擔了大部分立法工作,即便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法律草案的前期準備工作也是由常委會主導,并且事先經過常委會的審議程序,最終是否提交全國人大也由常委會決定,全國人大的審議、表決在很大程度上只具程序意義,其“廣泛的代表性”往往流于形式。基于常委會事實上行使了全部立法權,不如承認現實,將國家立法權徹底向常委會傾斜,將“二級”立法體制改造為“一級”立法體制。如此,不僅立法實踐中的諸多難題將迎刃而解,全國人大也能騰出時間和精力更好地履行其他法定職能。
但無論是“限權”方案還是“放權”方案,都面臨著現實的矛盾和難題,需要對當下人大制度作出相應的變革。
就“限權”方案而言,不僅存在著國家立法權內部權限難以厘清的理論困惑,而且意味著全國人大需要更多立法,勢必進一步加劇全國人大難以勝任立法任務的現實困境。這就需要大幅增加全國人大的開會頻次,延長每次開會的會期,以保障立法權的行使。同時合理縮減代表人數,使代表從目前的兼職化轉向專職化,并設立立法助理等制度,以適應立法的效率和專業要求。
就“擴權”方案而言,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彌補代表性不足的缺陷。這就需要適當增加常委會組成人員的人數,以擴大民意基礎。同時在立法壓力加大的情形下,需要明顯增加常委會的開會頻次和時間,強化專門委員會等機構建設,使常委會進一步成為一個常態化、專業化運作的立法機關。
顯而易見,上述改革不僅牽扯到增加立法成本、代表性的增減合理度難以把握等問題,而且屬于系統的改革工程,短期內很難完成。可資佐證的是,早在1982年制定新憲法時,就曾有過大量減少全國人大代表的設想,甚至提出了代表人數由3470人減為1200人的改革方案。但是我國十多億人口、五十多個民族、兩千七百多個縣的現實,卻決定了各民族、各地區、各行業均需有其利益代表,因而大幅減少代表人數的設想難以實施,最終轉而采取了更加符合國情的擴大常委會職權的方案。
以監督促平衡
在人大制度短期內難以作出大的變革的現實語境下,國家立法權的行使如何合理平衡立法民主和立法效率之間的沖突,需要尋找更為務實的改革方案。
首先,當下立法實踐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全國人大立法權的虛置,因此,進一步激活全國人大的立法功能乃是當務之急。除了最大程度細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各自的立法權限,對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普遍性規范意義的基本法律,以及關涉公民權利和民生權益的重要法律,應當堅守由全國人大行使立法權的底線原則,并盡可能厘清應當由其立法的具體事項范圍。同時,對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全國人大立法的修改權,亦應盡可能作出更加明確的規范和限制。
同時,基于常委會仍然必須承擔大部分立法任務,為了有效緩解立法民主與立法效率之問的矛盾,應當著重考慮如何對其立法活動加強監督。
在外部監督方面,需要進一步強化和完善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立法聽證等公共參與機制,以促進公民立法權利的實現,使常委會立法最大程度地接受民主制約,有效彌補民意基礎的不足。
更需推進的是全國人大對常委會立法的內部監督。常委會獨立行使相當大的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對常委會立法的監督卻始終是一個薄弱環節,如何建立相應的制度、機構等,對常委會立法實施有效監督,應是改革的重點所在。
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是,重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限的裁決機制。明確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等在效力上高于常委會立法,并詳細規定全國人大撤銷常委會不適當立法的程序,以及全國人大立法與常委會立法發生沖突的爭議解決機制,從根本上扭轉常委會自我裁決、自我監督的不合理弊端。
尤其應當通過詳盡的制度設計,對全國人大監督常委會立法的內容、方式、程序等作出規范。比如,為了有效約束常委會的修法權,應當建立相應的審查制度。如果常委會對全國人大的立法作出了修改,需要在翌年的全國人代會上增設特別議程,由常委會報告修法理由和情況,由代表大會通過審議、批準、備案等程序實施監督,如經審查發現有違憲、違法之處,全國人大可以改變或撤銷常委會的不適當立法。如此,既不延誤修法時機,又能確保修法質量。
而為了應對全國人大每年僅開會一次、不便經常性監督的瓶頸,可以考慮在全國人大內部設立監督委員會之類的常設機構,負責日常裁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限沖突,并對常委會立法的合憲性、合法性進行即時、動態的審查,以實現對常委會立法的常態化監督,防止越權立法等危險。
國家立法權是法治建設的基礎,只有盡力劃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限,并構建有效的監督機制,才能正本清源,確保立法同時行進于民主、高效的軌道上。以此為基點,還將促動人大的組織機構、權力配置、議事規則等向更為科學、合理的方向演進。這既是提升法治質量的必然要求,對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亦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