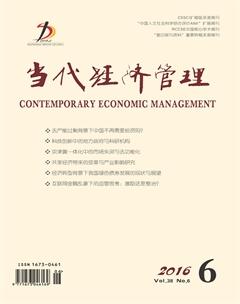德國哈茨改革對緩解我國結構性失業的啟示
徐磊 陳浩
摘 要 “就業難”一直是困擾我國的老大難問題,近幾年,隨著企業轉型升級速度的加快,“用工荒”的問題也在一些企業開始凸顯。“就業難”和“用工荒”所形成的人力資源結構性矛盾成為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德國從統一后的20世紀90年代開始也出現了結構性失業的問題,經過21世紀初的針對勞動市場的重大改革,德國的失業人口在金融危機中屢創新低。德國的哈茨改革為我國刺激就業、提高勞動力素質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經驗:進一步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民間職業介紹機構,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配置。同時,加大力度改善優化就業創業環境,既要保障低收入工作者、高齡工作者以及失業再就業人群的根本利益,也應重視勞動市場的公平性和財政投入的合理性。
關鍵詞 結構性失業;哈茨改革;刺激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6-0092-06
人力資源的結構性矛盾一般是指勞動力結構與企業的求人結構不一致而導致的勞動力供需矛盾。“就業難”一直是我國勞動市場的老大難問題,近幾年隨著國家促進就業政策的相繼推出,以及企業彈性化用工和勞動者的理性求職,更有國家宏觀經濟擴張上行的推動,我國的就業形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總體仍處于加劇的趨勢。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升級對人力資源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的人力資源結構的動態調整并不能與產業升級的發展速度相一致,近幾年出現的“用工荒”就是這個問題的凸顯。而青年勞動者、農村富余勞動力以及下崗失業人員更加劇了我國人力資源結構性矛盾。
與此相似,德國在1990年統一后,面對外部急速發展的全球化和內部加速推進的產業結構調整,國內勞動市場也出現了惡化的趨勢,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與同樣處于較高水準的求人率成為困擾德國政府的勞動力結構性問題。面對這樣的結構性矛盾,德國政府在21世紀初對勞動市場實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07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2009年發酵的歐債危機雖然也波及了德國經濟,但是德國的失業人口卻屢創新低,居于歐洲最低水平。德國勞動市場的成果被認為與21世紀初的改革有很大的關聯性。本文以德國的哈茨改革為研究對象,重點分析哈茨改革在緩解結構性失業的問題上的成果和不足,借鑒德國的經驗,本文重點關注我國的青年勞動者、農村富余勞動力、低技術人員就業問題,對我國勞動市場提出政策建議。
2003年,施羅德政府推出名為“2010年議程”(Agenda 2010)的長期結構性改革計劃,該計劃是德國社會安全(福利)體系改革與勞動市場改革的重要計劃,幫助德國避免陷入高社會福利支出導致的國債危機,亦重塑了德國經濟競爭力。計劃最重要的內容,甚至10年之后仍最熱門,影響德國社會安全與福利制度最深遠的的改革議題,即所謂的“哈茨一到四方案”。
2002年,德國總統施羅德任命大眾公司董事哈茨負責起草德國勞動市場的改革方案。德國政府對勞動市場改革的目標就是提升勞動就業機構的效率和失業者的就業欲望以緩解結構性失業,同時降低失業者人數以減輕財政負擔。施羅德政府以哈茨委員會的提案為基礎,在2003年1月頒布了“哈茨改革法案第一部”和“哈茨改革法案第二部”,2004年1月,“哈茨改革法案第三部”和“哈茨改革法案第四部”也相繼出臺。
由于政策具有時效性,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沖擊,所以本文主要以最后改革方案出臺的2004年與危機前2007年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哈茨改革的效果。
一、哈茨改革的經驗做法
(一)改善高齡勞動者的就業狀況
哈茨改革法案第一部重點關注改善高齡失業者的雇傭環境。2000年,55歲~64歲的高齡勞動者雇傭率是37.4%,2007年提升到51.5%①。
(二)為失業者提供過渡性補助和創業補助
過渡性補助和創業補助實行以后,工資補貼(為了推動失業者盡快就業,政府對勞動者的工資進行補貼)的領取者明顯減少。如圖1所示,領取過渡性補助的人數從2000年的4萬人倍增至2005年的8萬人,領取創業補助的人數也從2003年的4萬人大幅攀升至2005年的24萬人。與此相反,領取工資補貼的人數從2000年的12萬人降至7萬人。工資補貼領取人數的減少,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三)進一步創造和鼓勵低收入工作
哈茨改革實施以前,從事低收入工作的群體約有484萬人,哈茨改革實施以后,該群體的人數截止2005年12月上升至652萬人。
(四)發放工作介紹代金券
所謂工作介紹代金券,就是失業時間超過3個月的失業者向政府的雇傭服務機構申請的代金券,該代金券可以作為民營職業介紹機構的中介費使用,民營職業介紹機構在成功介紹工作以后可以用該工作介紹代金券在雇傭服務機構換取現金,而換取現金的額度取決于再就業的時間長短。因為對申領工作介紹代金券的失業者的資格認定比較嚴格,工作介紹代金券的發行量逐年減少,從這一點來看,政府的財政支出減少的目標已經達到。
(五)轉變聯邦雇用廳的職能
根據哈茨改革法案第三部的要求,聯邦雇用廳的職能從政府的指令下達部門轉變為雇傭服務的指導部門。聯邦雇用廳的職業介紹人員與求職者的比例從2004年初的1∶450改善為2006年初的1∶270②。改革也進一步促進聯邦雇傭廳的補助支付和就業支援等業務更加透明化和效率化。
二、哈茨改革的成果和不足
(一)哈茨改革的成果
1. 有效降低了德國的失業率,提高了抗金融危機的能力
在2002~2004年間,德國失業者人數平均每年增加11.5萬人(以11月為觀察點)。哈茨改革措施的實施,有效降低了德國的失業人數和失業率。2007年11月的德國失業者總人數為337.8萬人,與2006年同期比減少61.7萬人,相比2004年11月的425.7萬人有了大幅下降。從失業率來看,2007年11月的失業率8.1%,較之 2004年的10.3%降幅明顯。
2008年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主要發達國家的勞動市場,全球主要國家經濟下滑趨勢明顯。但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德國的失業率相對較低,甚至出現了改善的趨勢。德國的哈茨改革,采用緊縮財政,降低福利的辦法,有效地幫助德國提高了抗金融危機的能力。2008年經濟危機時,德國經濟增長1.7%,而英國、法國和美國分別增長1.1% 、0.9%和1.4%,可以說,幾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差不多處于同一水平。而到了2010年就看出了差別:德國GDP增長3.6%,而英國只有1.3%、法國為1.5%。即使情況較好的美國,其經濟增長率也僅為3.1%。
2. 低工資勞動者數量的上升,拉動宏觀工資下行,降低了企業勞動成本
1996年德國低工資勞動者130萬人,2012年數量翻了一番,達到了270萬人。低工資勞動者數量的增加拉動宏觀工資下行。2000~2012年間,歐元區國家的勞動成本上升率為1.8%,而德國僅為0.7%。
3. 結構性失業改善明顯
哈茨改革實施以來,勞動市場的改善的跡象也是明顯的。如圖2所示,哈茨改革后的2004年年底開始,失業者人數逐漸下降,企業提供的崗位逐漸增加,從2007年開始,德國結構性失業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哈茨改革發揮了顯著的效果。
(二)哈茨改革的不足
1. 哈茨改革的實際效果距離其設定的理想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哈茨改革關注的核心失業者群體——長期失業者和低技術失業者群體就業狀況變化不大。2004年長期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分別為56.3%、11.9%,而2007年為56.6%、11.1%,基本沒有變化。
2. 勞動者工資較大的下行幅度加劇了城市貧困化
德國實行的是自由靈活的雇傭制度。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雇主;企業也可以根據企業生產經營的實際需要任意招收和解雇工人。因此,勞動者很難得到勞動合約的保護,同時勞動者的工資彈性波動特別是下降幅度較大,加劇了貧困化。據統計,1999年,德國相對貧困率為10.3%,2011年達到了15.1%。其中,大城市的相對貧困率更是高達19.6%。有研究者認為,正是因為中低工資勞動者相對集中于大城市,才導致這些大城市如此高的相對貧困率。
3. 高齡工作者雇傭率的提高以企業和政府的額外支出為代價
哈茨改革法案第一部的出臺改善了高齡失業者的雇傭環境,提高了高齡勞動者的雇傭率。但是這種成績是建立在企業和政府按照全職工作的工資和社會保險的標準雇傭只工作一半時間的高齡勞動者的基礎之上,因此,改革的實際效果被認為十分低下③。
4. 失業者的低收入工作機會被以低工資工作為副業的全職工作者擠占
哈茨改革的初衷是,創造低收入工作崗位,給失業者提供進入正式工作崗位的過渡機會。而從實際數據可以看出,以低收入工作為副業的勞動者成了該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而僅以低收入工作維持生活的勞動者依然沒有機會進入正式工作崗位。真正全職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數僅僅是從414萬人上升至475萬人,增幅僅為15%,與此相比,以低工資工作為副業的有全職工作的人數從70萬人飆升至178萬人,約占該政策受益群體的65%④。同時,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勞動者享受社會保險金減免的優惠,導致政府社會保險金的減少也成為該政策的軟肋。
5. 代金券的管理和使用不規范,其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但是,因為民營職業介紹機構重視短期的就業成功率,對勞動者的就業安定性的關心不足,因此實際上持有工作介紹代金券的失業者的再就業成功率依然不高,2004年僅僅為10%⑤。此外,工作介紹代金券也可以作為失業者的培訓費充抵學費,因此被一些民間機構濫用換取現金,這部分的代金券高達63%⑥,這也是接受培訓的失業者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2000年的34萬人降至2005年的11萬人)。
三、哈茨改革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啟示
當前我國就業面臨著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的局面,城鎮需就業的勞動力年均2 500萬人,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業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部分地區和企業“招工難”與“就業難”問題并存,是我國就業領域結構性矛盾的突出反映。據調查,“招工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型行業,但有向內地蔓延的趨勢,缺口比較多的主要是一線操作工和技工。“就業難”則突出表現在“4050”人員就業、大學畢業生就業和低收入群體再就業等幾個方面。
針對這一問題,人社部在2010年年底下發了《關于采取有效措施緩解當前部分地區就業中結構性短缺問題的通知》(人社部發[2010]110號),提出了6項具體措施。各地也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但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勞動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我國就業問題總量之大、矛盾之復雜,是任何國家都未曾遇到過的,因此,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就業的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的局面仍將持續。李克強總理在多個場合說過:“經濟政策‘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就業是最大的民生。這一點政府須臾不敢松勁。” 這意味著目前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仍是以保就業為主。如何緩解結構性失業也成為了政府亟待解決的課題。
參照德國哈茨改革的經驗,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定程度上緩解我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一)轉變政府職能,牢固樹立明確的公共服務行政理念
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政府職能缺越位、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現象屢見不鮮,已經嚴重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對就業也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指出,穩增長、促發展從根本上講是為了擴大就業,“促進就業“應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政府機構、各類職業中介機構的運轉都圍繞“促進就業”而展開。
作為行政服務型機構,人社部也應努力實現兩個轉變:由指令下達部門向雇傭服務的指導部門轉變;從“失業保障”到“促進就業”理念的轉變。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勞動用工、職工技能培訓服務,為創業者提供全方位的創業服務。進一步優化服務流程、放棄“官本位”意識和不良作風、強調服務和監管、釋放市場主體活力,提高工作效率,促進就業工作的穩步推進。
(二)簡政放權,改善優化創業環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建立政府激勵創業、社會支持創業、勞動者勇于創業新機制做出了全面部署。同時,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提出了就業優先戰略,依靠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
與德國相比,我國的創業環境不令人滿意。而注冊難則是創業者面臨的第一道也是最難逾越的瓶頸,突出表現在:行政審批程序繁雜、工作效率低、時間成本高等。這和我國現行的行政審批制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指出,要以簡政放權促就業,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簡政放權的突破口,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則是政府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改革的第一步。2013年3月1日,國家工商總局開始在深圳、珠海進行試點,不要注冊資金,不要注冊地址文件,不要注冊費,不年審,承諾三天時間完成公司注冊。
除此之外,面對創業的資金困難,一方面,完善扶持創業的優惠政策,整合發展國家就業創業基金。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德國經驗,對于失業者自己創辦的企業,可以給與開業補助金。如果企業里雇傭別的失業者,將可以得到更多的補貼。
(三)提升失業者的就業欲望,對失業者進行職業能力再開發
失業時間與就業可能性成反比,失業時間的延長意味著失業者的技能退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會相對縮小。隨著失業時間的增加,失業者往往會逐漸適應失業的狀態,年紀越大就越容易適應,甚至當就業市場條件改善時,他們也不愿意再出去工作。而失業者不斷增多也會加劇經濟困難并造成惡性循環。因此,人力資源公共服務部門應加大就業創業的宣傳力度,提升失業者的就業欲望,為失業者提供更有針對性、更有效,也更人性化的服務。有條件的可以提供“一對一”甚至“多對一”的咨詢服務,包括進行評估、測評、提出建議等,比如是否知識老化、是否缺乏某方面的知識或技能需要培訓、是否更適合某項工作等等。
對有就業愿望的求職者,政府可以進行資助,由專業人員對其進行素質技能測評,結合崗位需求,進行崗位技能強化培訓。也可以借鑒德國的“替換工作制”的做法,安排企業在職人員參加職業訓練,在此期間空缺的崗位由失業人員來頂替,由各地的人才交流服務中心負責提供一部分頂崗失業人員的工資費用。對于那些以頂崗人員被錄用的失業者來說,通過實際工作,掌握了工作技能,而且還有被企業直接錄用為正式員工的可能。
(四)既重視高齡勞動者的就業,也重視勞動市場的公平性和財政投入的合理性
在我國,政府也很關心高齡勞動者的就業問題,針對高齡勞動者的就業難出臺了一系列的就業優惠政策和刺激政策,例如針對“4050”的就業支援政策。但是參照德國哈茨改革的經驗,高齡勞動者的雇用崗位應該盡可能不占用正常的工作崗位,否則有可能導致就業渠道的不暢,影響勞動市場的公平性,進一步提升失業率。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片面追求高齡勞動者就業率的增長,在財政上過度加大對高齡勞動者的就業投入,這樣即破壞了勞動市場的公平性,也可能降低高齡勞動者的就業欲望,更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有必要在重視高齡勞動者就業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就業的渠道,增強勞動者的就業欲望,降低政府財政支出,例如鼓勵高齡勞動者自主創業就是這方面的探索成果。
(五)鼓勵低收入工作,對超低收入工作者提供補貼
在我國城鎮低收入群體中,下崗失業人員占相當比重,這類人員學歷不高、勞動技能差、年齡也偏大,在勞動力市場上為弱勢群體,難以獲得二次就業機會。即使就業,也多集中于“非正規就業”且收入水平較低的建筑業、制造業、社會服務業等行業。這類群體就業難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社會上仍然有一些勞動條件較差報酬又低的工作沒有人愿意做,為了緩解這種尷尬的就業形勢,我們也可以借鑒德國的“美茵茲模式”,即對愿意從事這種超低收入工作的再就業者,政府定期提供額外的社會保險補貼。同時,適當減免其所應繳納的稅收和社會保險金。這一模式在以“美茵茲”為首府的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取得成功,因而得名。目前情況表明,這一措施在德國國內得到了大量失業者的認可。
(六)加強人力資源市場的調控與監督,規范民間職業介紹機構
我國的職業介紹機構可分為非營利性職業介紹機構和營利性職業介紹機構兩大類。其中, 由各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舉辦的公共職業介紹機構是非盈利職業介紹機構的主體,向求職者和失業人員提供免費就業服務。這些機構按職能分工,以部門、行業管理權限劃分。各自為陣的做法使得信息不能及時得到共享,最終導致就業信息流通不暢。
不可否認,民間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也是政府和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民間私人職業介紹機構發展較為迅速,但是快速發展的背后也出現了許多隱患:如各類職介機構魚龍混雜,市場混亂,求職者很難甄別其資質和資信狀況;機構設立不規范,沒有人才(職業)中介執業證書甚至不具備法人資格;守法狀況不佳,運作不規范,信譽較差;立法管理存在漏洞和缺陷,執法力度不夠;缺乏行業自律和行業評價標準等。應對這種混亂局面,政府應大力加強人力資源市場的調控與監督,深入開展人力資源市場清理整頓專項活動,依法打擊黑中介等違法違規行為;推動相關立法和法規的及時出臺;推動行業協會組織發展,建立行業評價標準,加強行業自律。
(七)充分發揮市場在人力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配置
為了保證公共服務的優質和高效,應進一步發揮市場在人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實現公共服務的配置由原先的公共機構提供向市場化配置轉變。可以以發包公共服務項目的形式,向職業中介機構購買公共服務。同時,建立健全對民間職業介紹機構的工作效率評估機制,每年組織專門人員對各類中介機構的服務質量進行評估,對介紹成功就業率高的機構,根據推薦就業率給與經費補貼。這一點,我國《就業促進法》中有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職業中介機構提供公益性就業服務的,按照規定給予補貼”。
從德國的經驗來看,政府將部分就業推薦業務委托給職業中介機構,中介機構成功介紹工作后將獲得政府向失業者提供的2 000歐元就業券。這樣,公共服務的配置完全通過市場上各類職業中介服務機構之間的競爭來得以實現。一方面,在魚龍混雜的民間職業介紹機構市場形成了鼓勵競爭、優勝劣汰的機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公共服務配置的效率和質量,有效促進了社會就業。2007年,德國私營職業中介機構共介紹68萬人就業。
(八)強化社會監督,嚴格用人制度,杜絕“吃空餉”現象
“吃空餉”是指占用低收入工作的指標,但是卻在從事其他工作,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基層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這一現象仍然存在。目前來看,“吃空餉”主要有以下形式:“曠工餉”、“病假餉”、“多頭餉”、“冒名餉”、“死人餉”和“違紀違法犯罪人員餉”等。“吃空餉”現象嚴重違背了社會的公平原則,嚴重侵蝕了公共財政資源,助長了腐敗行為,損害了政府形象。
2013年,河南、河北、安徽、廣西、廣東等省區加大力度治理“吃空餉”。河北省清理“吃空餉”2.76萬人,涉及金額1.3億元;安徽省清理“吃空餉”,查處相關問題642個,清退人員248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和組織處理48人;湖南省清查出各類“吃空餉”人員4 262名。僅河南一省,2013年治理“吃空餉”,省直機關清理87人,查糾違紀違規資金63.8萬元;省轄市清理22 280人,查糾違紀違規資金達11 843萬元。
應進一步強化社會監督,嚴格用人制度,杜絕“吃空餉”現象。首先,盡快落實編制實名制,公開編制,嚴堵編制漏洞。嚴格按照核定的人員編制數額及編制性質,配備相應的工作人員,實行定編到人,并將編制性質和配備人員名單向社會公示。這樣,可以有效防止超編進人、混編混崗和超職數配備領導干部等問題的發生。同時也有利于發揮干部群眾對機構編制管理工作的監督權。其次,要完善人事管理機制,實行一把手問責制,對提供吃“吃空餉”者加大懲責力度,上升到行政問責,甚至可以定性為腐敗或瀆職,給予更高的處分。
德國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結構性失業,與我國目前的就業現狀有相似之處,德國哈茨改革較好地刺激了就業、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我國也可以借鑒哈茨改革的經驗,從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入手,規范民間職業介紹機構,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配置。同時,進一步改善優化就業創業環境,既要保障低收入工作者、高齡工作者以及失業再就業人群的根本利益,也應重視勞動市場的公平性和財政投入的合理性。
[注 釋]
① 資料來源:Eurostat。
②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ドイツにおける労働市場改革―その評価と展望―,労働政策研究報告書,2006,No.69,P.26。
③ 哈茨改革法案規定:55歲以上的勞動者可以在退休以前享受勞動時間減半的優惠。經營者為這樣的臨時勞動者繳納工資的20%作為社會保險金,其余的部分由政府補助(如果是全職需要繳納90%)。此外,這樣的勞動者雖然勞動時間減半,但是可以領取相當于全職的70%的工資(OECD, Economic Surveys: Germany,Paris:OECD Pubilished,2008, pp.87-88。
④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ドイツ、フランスの労働·雇用政策と社會保障,労働政策研究報告書,2007,No.84,P.59。
⑤ 蔡和平,哈茨改革能否扭轉德國勞動力市場的頹勢,中國勞動,2007(2),29頁。
⑥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ドイツにおける労働市場改革―その評価と展望―,労働政策研究報告書,2006,No.69,P.64。
[參考文獻]
[1] Bachmann Ronald,Bauer Thomas K.,Kluve Jochen,Schaffner Sandra,Schmidt Christoph M. Mindestl hne in Deutschland Besch ftigungswirkungen und fiskalische Effekte[Z]. RWI:Materialien Heft 43,2008.
[2]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Arbeitsmarkt 2000:Amtliche Nachri-chten der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Z].2001.
[3] Ebbinghaus Bernhard,Eichhorst Werner. Employment Regulation and Labor Market Policy in Germany,1991-2005[Z]. IZA DP No.2505,2006.
[4] Eichhorst Werner.Der Arbeitsmarkt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Strukturreformen und sozialpolitischem Reflex[Z]. IZA DP No.3194,2007.
[5] Jacobi Lene,Kluve Jochen.Before and After the Hartz Reforms: The Performance of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in Germany[Z]. IZA DP No.2100,2006.
[6] 斎藤純子.ドイツの格差問題と最低賃金制度の再構築[M].『外國の立法』第236號,國立國會図書館,2008.
[7] 土田武史.ドイツにおける社會保障改革の動向[J].クォータリー生活福祉研究,通巻54號 Vol.14 No.2,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2005.
[8]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ドイツにおける労働市場改革―その評価と展望―[R].労働政策研究報告書,No.69,2006a.
[9]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最低賃金制度の導入をめぐる議論[Z].海外労働情報(2006年6月),2006b.
[10]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ドイツ、フランスの労働雇用政策と社會保障[R].労働政策研究報告書,No.8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