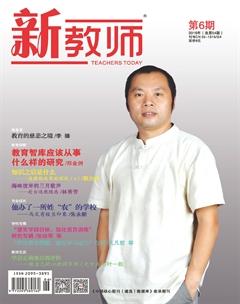教育智庫應該從事什么樣的研究
鄭金洲
自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后,新型教育智庫的建設也成為教育界熱議的話題,各地也開始創建或已經建成了這樣或那樣的教育智庫。“智庫熱”在教育界一時興起。與其他綜合性智庫相比,教育智庫屬于專門智庫,主要就教育領域中的相關問題進行決策咨詢。它作為智庫,有著一些不同于學術機構的特殊要求,在研究形態和方法上,也有著特定的取向。一般來說,作為教育智庫應該主要從事以下幾種類型的研究。
決策研究
智庫是“智囊”,體現的是智慧。這些智慧的指向應該是教育決策,圍繞教育政策或決策進行研究,是智庫最為重要的職責所在。決策研究,至少有四種基本的形式。一是前瞻研究。決策總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的,領導的判斷也總是帶有預見性的,毛澤東同志說過,領導就是預見。坐在指揮臺上能看到地平線上普遍出現的東西不叫領導,看到地平線上剛剛出現的東西也不叫領導,只有能看到地平線上剛出現的又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東西才叫領導。前瞻性研究就是研究者謀全局、看大勢所做出的預測性分析。而要做出這樣的分析,常常需要研究者頂天立地——既洞悉決策層的要求,又了解基層的實踐。二是前審研究。這類研究不同于前瞻性研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決策者有了決策的意愿之后,提請研究者予以深入調查和論證。研究者研究后形成分析報告,對該項決策的可行性及不可行性做出說明,幫助決策者下決心出臺或不出臺相關決策。三是復審研究。決策已經出臺,但出臺后到底效果如何,各方有什么樣的反響,是否認同,執行中遇到哪些問題,這類研究常常也由教育智庫來承擔,實施的是對決策或政策的復審。四是糾錯研究。教育智庫不僅可能扮演教育決策制定、執行中的“啄木鳥”角色,也有可能扮演“醫生”的角色,對教育決策中存在的謬誤在察覺和深入把握的基礎上,提出改進性建議。四種形式的研究,從決策的不同環節和角度切入,形成自身的智慧產品。從以往研究情況來看,國內教育智庫對第二、第三類問題研究較多,而對第一、第四類問題研究則相對較少。
跨學科研究
決策的一大特點是具有非常強的綜合性,領導的一個基本要求是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豐富的經驗。因而,為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領導者提供的知識產品,一個核心的要求就是要跨學科、跨領域、跨界,綜合地、整體地、多角度地認識和分析問題。在教育實踐中,大概沒有哪一個問題是靠教育專業的單一知識可以解決的,甚至沒有哪一個問題純粹屬于教育領域自身范圍內的。教育領導者在決策過程中,或者是考慮出臺某一個教育政策的時候,總是要“瞻前顧后”,預估“左鄰右舍”的反應,從“四面八方”的角度來作出判斷。這樣,也就要求教育智庫提供的教育產品,跨學科的“成色”要足,教育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哲學等都會成為分析的視角和工具;跨界的“特點”要突出,既要有來自于教育理論界、實踐第一線、教育行政部門三方視角的考量,也要注意吸納政府、企業、社會、文化等相關部門或領域的意見。有人說,決策是平衡和妥協的產物,這話雖然并不見得完全正確,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多學科的視野、多角度的分析、多立場的匯集,才有可能形成科學、客觀的教育決策。
實證研究
形成教育決策的重要參照物,或者直接成為教育決策,大概不會是純粹理性思辨的結果,大體都是建立在扎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教育問題雖然有些是理論問題,但歸根結底是實踐問題,具有明顯的實踐特征。這就要求,教育智庫在探討、分析、解決教育問題時,必須在充分進行理論分析、思維加工的同時,積極參與實踐,必須在實踐中促進思維能力的進一步發展和認識的深化,在實踐中檢驗思維成果的正確性。沒有實踐,思維的發展就失去了動力,對問題的探討也就失去了意義,求異性就會變成主觀中的多樣性,跳躍性就會變成臆想中的胡亂聯系。所以,教育智庫的研究成果,需要實證研究作為基礎。教育實證研究以實地觀察分析、調查、測量、實驗為基本手段,得出的研究結論一般來說,對教育決策、教育實踐比理論分析和思辨研究更有參考和借鑒價值。西方不少的實證研究成果,最后都能導引到重大的教育決策部署之中,成為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之下,我們的教育實證研究雖然在一些教育行政部門得到了應用,但成果不多,影響也有限。當然,教育決策部門缺乏對實證研究的關注也使得這類成果的應用受到限制。
獨立研究
智庫之所以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決策有借鑒意義與作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客觀公正的立場、獨立開展的研究。智庫是要為政府服務,但如果完全與政府坐同一條板凳,或者與政府捆綁在一起,其研究成果也就難以體現獨特的優勢和價值。智庫開展獨立研究至少有這樣三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與政府相關部門保持一定距離。智庫要關注政府需要什么、關心什么、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么,也要了解政府的運作程序、行政規范、職責分工等,但須與政府的立場等保持一定的張力。距離不只是產生美,也會讓智庫以旁觀者的姿態客觀審視決策的方方面面,得出適應發展趨勢與規律的正確認識。第二,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智庫雖然有時會接受某些機構的捐款,有時也為某些利益集團承擔相應的研究項目,但是,在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咨詢時,必須要保持立場的獨立與客觀,不為任何利益集團代言。智庫如果歸屬于某一利益集團,也就成了這一利益集團的傳聲筒,不僅會讓“完全客觀”成為一句空話,自身的公信力也將不復存在。智庫是要超越各利益集團的,而且是把各利益集團作為研究對象,深刻剖析他們在教育決策中的利益博弈,在利益的博弈與均衡中做出獨到的判斷。第三,積極打造獨立運作平臺。獨立不意味著封閉,更不是孤立。教育智庫在研究中,要注意打造獨立運作的平臺,通過舉辦論壇、研討會,發行期刊,發布報告,運用現代化信息手段發布信息等,定時不定時地傳播研究成果,進而影響決策。
國際比較研究
與其他研究相比,智庫開展的研究更注重寬廣的視野,對國內外相關情況了然于胸。開展智庫研究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與國際“對標”,也可稱之為“對標研究”。想出一個建議要思考國外同行的相關做法,思考一個決策要根據國際通行的相關標準,尤其要把握世界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在教育教學上的成功經驗。對標研究的結果,并不是借用或使用他們已有的東西,而是只有在國際視野中才能更好地把握研究事項的定位,把研究恰當地固著于歷史的時空框架內。在國際比較研究中,還有一個方面不能忽視,就是對教育智庫也要注意進行比較研究。一些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教育智庫已經運作了上百年,已經有了一些成熟的做法,而我們的教育智庫建設還處在初創階段,搞智庫建設也只是近三年的事情,許多東西還不明就里。比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智庫,這樣的智庫“特色”在哪里?“新”在何處?只有對國際同行的實踐有深入了解,才能對“特”和“新”有更好的把握,“特”和“新”也才有依據,有基礎。
智庫建設研究
智庫搞智庫建設研究,也就是研究自身,研究自身的建設與發展,研究自身的相關工作。從國際范圍來看,關于智庫的研究成果還不多,研究教育智庫的成果更是鳳毛麟角。我國自己的教育智庫剛剛起步,許多問題都有待探索,需要借助于研究,以明確智庫后續發展方向。這些問題林林總總,似乎現在都還沒有答案。比如,教育智庫建設的目標定位到底是什么?總體來講,是要咨政、啟民。但兩者如何把握,如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比如,在我國,教育智庫類型復雜,有官方、半官方、非官方三類(國外的教育智庫幾乎都是非官方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智庫”)。怎樣處理好三者的關系,如何形成三方的合力,如何扶持社會智庫的發展?比如,教育智庫如何才能吸納各方人才,如何進行隊伍建設,如何建立起適合智庫發展的人才管理體制機制?比如,智庫的運行機制如何完善,現有的科研制度、經費報銷制度、課題立項制度等與教育智庫建設存在哪些矛盾,怎樣才能克服?比如,教育智庫的成果如何發布,怎樣才能進一步增強智庫自身的影響力(如果沒有影響力,智庫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義)?比如,教育智庫的發展需要什么樣的外在支持,建立起什么樣的支持系統才能推動智庫健康發展?再比如,教育智庫如何運用大數據,如何讓自身的研究報告建立在扎實的數據分析基礎之上。類似的問題,不一而足,都需要花大氣力研究。
(責任編輯:林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