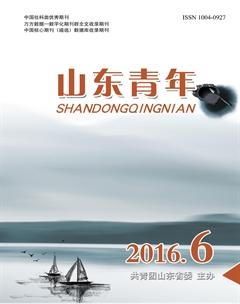勞動爭議裁審關系中當事人訴訟請求問題之探微
于雷
基于我國目前勞動爭議案件中勞動仲裁前置的制度設計,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糾紛案件過程中對仲裁裁決事項與訴訟請求相異部分的審查,就顯得尤為重要。實務中處理,不僅要考慮仲裁裁決效力的認定及不告不理原則的運用,更要兼顧當事人的心理預期與裁審程序應有作用的發揮。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多元所有制經濟結構的逐步形成,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發生了深刻變化,法院所受理的勞動爭議類案件逐年增多,在法院內部勞動爭議也隨之成為當前一個比較突出的審理熱點與難點。筆者所在地區派出法庭,雖為當地城鄉接合部,但大中型企業聚集較多。僅2014年上半年,派出法庭受理勞動爭議類案件就已超過100多件。在審理這些案件的過程中,筆者對勞動爭議案件中的仲裁與審判之間的銜接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體會,亦想借此文章發表一些個人粗淺認識,以資討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規定,我國對勞動爭議案件主要采取“一調一裁兩審、仲裁前置”的處理模式(部分勞動爭議案件實行的一裁終局在本文中暫且不論)。而仲裁機構與審判機關相互之間并無隸屬關系,兩者分別行使仲裁權和審判權,如對仲裁裁決事項不服,勞動者(為便于參閱,本文所提訴求以勞動者一方為例)到法院繼續就勞動爭議起訴的案件,不在少數并且案件一般均相對復雜,在審理過程中,審判機關(法院)對于勞動者訴訟請求的審查或者說認定,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于決定著案件審理工作的成敗。
圍繞著仲裁委的裁決事項和勞動者在法院所提訴訟請求,兩者間關系,主要有如下規定,一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之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委部分裁決事項不服,向法院起訴的,則仲裁裁決整體不發生法律效力。二是該司法解釋第六條同時規定,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后,當事人增加訴訟請求的,如該訴訟請求與訟爭的勞動爭議具有不可分性,應當合并審理;如屬獨立的勞動爭議,當事人應申請仲裁。于此,在此需要討論的則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事項不服后,向法院起訴時,所提起訴訟請求的處理。
第二部分、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后,在庭審過程中,當事人增加訴訟請求的處理。
就第一部分而言,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應理解為只要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則原仲裁裁決整體不發生法律效力,至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時止,仲裁裁決書失效。而勞動爭議案件一般案件較為復雜,利益糾葛較多,當事人訴訟請求少則幾項,多則甚至于近二十余項。在相當一部分案件中,當事人所提訴訟請求與仲裁裁決事項是有所差異的,在仲裁裁決事項整體不發生法律效力(或者說是失效)的情況下,如何理順與訴訟請求間關系,在實務操作中存在一定爭議或盲點,這就給了后續的審判工作帶來了難題與困境。下面,以實踐中較為常見的案例予以說明。具體而言有,以仲裁裁決事項有A、B、C三項為例,雙方當事人所提訴訟請求僅限在仲裁裁決事項范圍內,如:
案例一、勞動者一方所提訴訟請求為A、B、C三項,用人單位未提訴求。
案例二、勞動者一方所提訴訟請求為A、B、C三項,用人單位所提訴求也為A、B、C三項。
案例三、勞動者一方所提訴訟請求為A、B兩項,用人單位所提訴求僅為A一項。
依上述案例,逐一闡述:
案例一之情況,因勞動者對仲裁事項全部提起訴求,法院依法對其訴訟請求(即前仲裁事項)全部予以審理并判決,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雖因勞動者之起訴,仲裁裁決已失效,但在訴訟請求范疇內,因用人單位沒有在訴訟階段提起請求,故應視為用人單位對原仲裁裁決事項之默認或服判,則如在法院審理期間,認定用人單位應給付的款項比原仲裁結果低的,應視為用人單位認可仲裁結果,按原仲裁結果判決。如計算款項高于原仲裁結果,則當然以新款項數額為準。在此處重點討論問題是,對一方當事人對仲裁事項未提起起訴,視為認可仲裁結果之認定,此結論雖目前無明確法律依據,僅在部分地方法院會議紀要中有所體現,如2012年7月廣東惠州中院、惠州市勞動仲裁委《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第七條之規定“勞動仲裁機構就當事人的請求作出某一具體裁項后,當事人未就該具體裁項依法起訴,一般應視為認可該裁項。仲裁裁決作出后勞動者起訴,用人單位沒有起訴或申請撤訴的,人民法院認定用人單位應給付的款項比仲裁裁決的結果低的,視為用人單位同意仲裁結果,應按仲裁裁決的結果作出判決。仲裁裁決作出后用人單位起訴,勞動者沒有起訴的,人民法院認定用人單位應給付的款項比仲裁裁決的結果高的,視為勞動者同意仲裁結果,應按仲裁裁決的結果作出判決”。從當事人普通的思想認識及心理預期看,從裁審關系的有效銜接講,確認此論點成立,符合廣大群眾對仲裁、審判兩者間關系的一般理解,可使法院的審理工作建立在仲裁裁決的結果之上,避免了仲裁結果的空洞化,使仲裁結果對法院判決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一定的拘束力,亦可使裁審間二者的銜接更為緊密,并,可以說是不告不理原則的一種運用。
案例二情況,雙方均對仲裁結果提起訴訟,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一條之規定,雙方互為原、被告,則法院對原仲裁結果(即訴訟請求)全部予以重新審理,判決結果不受原仲裁結果任何限制,可高于或低于原仲裁結果。
案例三情況則要復雜一些,對于雙方當事人均所提訴求A項,法院重新審理,依法判決,不受原仲裁結果限制。對于勞動者一方所提B項請求,依前述觀點(視為用人單位對B項裁決結果已認可),法院審理結果受原仲裁結果之限制,就高不就低,高于原仲裁結果則可判之,低于原仲裁結果則按原仲裁結果數額判決。而案例三的關鍵問題在于,雙方當事人均沒有提及的原仲裁結果C項,該如果處理?雖有觀點認為,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仲裁裁決后,當事人對勞動仲裁裁決中的部分事項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后勞動爭議仲裁裁決效力的確定問題。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七條之規定,在審判工作中,應對勞動仲裁裁決的全部內容進行審理并作出處理。\+①對此觀點筆者不能贊同,依前文所言,在絕大大數當事人對仲裁結果不持異議(未起訴,視為認可)的情況下,不審查當事人起訴請求范圍多少,就對原仲裁結果全部予以重新審理,作出與原仲裁結果相比,或多或少的判項,于法于情于理,皆不合適,其結果必然會造成仲裁裁決結果的虛化,乃至于最終架空仲裁裁決這一前置程序。筆者贊同之論述為,當當事人在向法院起訴時提出的請求少于仲裁裁決事項時,法院審理中應嚴格遵行不告不理的原則,對當事人未提起訴訟的事項不進行審理。\+②而對沒有起訴的C 項最終處理,筆者認為一般來說,因雙方當事人均不持異議,此處的C項往往是與雙方當事人利益聯系不大或數額不多、雙方關注度不高的內容。故而審判實踐中,最好的處理方式是,在庭審過程中,向雙方當事人予以釋明,在征求雙方一致同意的基礎上,將C項內容寫入判決書的判項之中。否則,該C項內容就會因仲裁裁決書失去法律效力,而在法院執行階段失去依法強制執行之基礎。
在第二部分中,主要情況在于法院庭審中訴訟請求的增加。舉案例四來說明:
案例四、勞動者一方所提訴訟請求為A、B兩項,用人單位未提訴求。但在法院庭審審理過程中,勞動者一方才提出C項及新的D 項訴求。
此案例四,系庭審中增加訴求之情形,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后,當事人增加訴訟請求的,如該訴訟請求與訟爭的勞動爭議具有不可分性,應當合并審理;如屬獨立的勞動爭議,當事人應申請仲裁。結合案例,應看到,勞動者所提C項訴求,已經原仲裁裁決,在立案階段未提訴求,而在庭審階段才提出,就法院審理階段而言,應屬于新增加之訴求,此處所言新訴求,不僅應是與訟爭勞動爭議具有不可分性,而且還應為“未經過原勞動仲裁裁決的事項”。因為從表意角度上來看,所謂增加的訴求,即是要與原仲裁裁決事項、與法院立案階段起訴的訴訟請求均有不同,才能為增加的訴訟請求。同時,為了限制范圍,需要強調增加的訴求與原勞動爭議事實的依附性,在2009年8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第8條就規定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后,當事人增加訴訟請求的,如該訴訟請求與訟爭的勞動爭議具有不可分性,應當合并審理,該條款中的‘不可分性是指增加的訴訟請求與仲裁的事項是基于同一事實而產生的,相互之間具有依附性”。作此理解,實際上也變相契合了當事人對原仲裁結果不訴即視為認可原仲裁結果之論點。這樣,既維持了仲裁裁決的權威性,又發揮了仲裁分化、過濾勞動爭議糾紛之功能。故,案例四中C項訴求,因為在原仲裁裁決階段已作過裁決,不屬于“增加的訴訟請求”范疇,在法院審理階段應予回避,不作處理。而對于D項,因沒有經過原勞動仲裁裁決,如具備與訟爭勞動爭議的不可分性,則可合并審理并予以判決。
綜上所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勞動爭議仲裁裁決事項的效力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要依當事人是否對之提起起訴而定,雖有諸多不便,但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內,對審判實務中的操作,仍只能是竭力辨析法理、唯法圖之,力求在裁審間找到最符合法律規定之本意、契合當事人心理之預期、回應社會關注之裁判方法,以維護最廣大勞動群體的合法權益,并對裁審間相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能有所助益。
[注釋]
①司 偉 : “勞動爭議裁審銜接中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3年總第53輯,第105頁。
②王林清:《勞動爭議裁訴標準與規范》, 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491頁。
(作者單位:撫順市東洲區人民法院民一庭,遼寧 撫順 1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