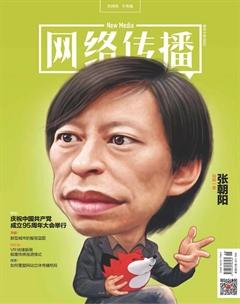VR結緣新聞 顛覆傳統報道模式
秦蘭珺
2016年,“VR(Virtual Reality,即虛擬現實)”一詞炙手可熱。VR技術是一種可以創建和體驗虛擬世界的計算機仿真系統的技術,用戶在體驗該技術應用時,能夠沉浸到畫面中并有身臨其境之感。那么,當VR技術與新聞結緣,將會如何?當VR技術應用于傳統會議報道,又會帶來哪些變革?
試水:兩會報道應用VR技術
1938年9月,袁牧之和吳印咸帶著成套設備來到延安,促成了延安電影團的誕生。電影團拍攝了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代表的革命歷史紀錄片,不僅為中國革命史留下了珍貴的紀錄,也開創了會議影像報道的先河。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影像事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會議報道開始的。一方面,七十年來,會議報道形成了成熟的影像語言套路,堪稱影像表義的典范程式;另一方面,每一次媒介技術的發展,又總會被最先應用到會議報道中。
如果說2014年是媒體融合元年,2015兩會報道新媒體元素的比重明顯加大,那么,2016年則堪稱另一個元年——VR元年,而VR又是最新的媒介技術之一,這就不難理解,為何2016兩會報導的一大亮點會集中在VR的大規模應用上。據不完全統計,《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網、中青網、澎湃新聞、新浪新聞、網易新聞、《財經》雜志、優酷土豆、樂視網等媒體均開始試水VR新聞。
其實,在VR新聞方面,2016兩會報道并非先驅。新華社在“九三閱兵”中就已經開始嘗試VR全景報道。而美國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則分別在2015年9月和11月開通了自己的VR新聞頻道,報道內容多是災難、戰爭、游行等新聞現場,將VR如此大規模地應用在會議報道中是中國媒體首創。
創新:360度的機遇和挑戰
全景鏡頭又稱360度鏡頭,幾乎能360度無死角地捕捉影像。雖然所有影像在本質上都是二維畫面,但當環面不斷延伸,就被縫合成了一個自洽的球形空間。全景影像建構的是一個以攝影機為中心的影像之“境”,而非特定視角下的有限之“景”。這意味著觀眾在360度影像的包圍中,好像并非僅在屏幕前觀看,而是在環境中游走,也更容易讓其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
其實,現有的大部分全景新聞,看中的就是VR在制造現場感上的潛力。一方面,還原新聞現場本身就是新聞報導的一大訴求;另一方面,因身臨其境才能帶來感同身受,這無疑更能促進觀眾對報道對象產生認同感和同情心。因此,災難、貧困、戰爭和游行等題材才會成為VR新聞的首選。試想一下,如果讓觀眾“走入”震后廢墟、貧困鄉村、戰爭難民營或是游行人群,感其所感,見其所見,而非僅僅在屏幕前的某個外部視角觀看,報道的情感效果將會大大加強。也正因如此,全景兩會報道更能完整地復原記者的參會經歷,讓觀眾“走入”人民大會堂,感受每年一度的兩會盛況。
另一方面,我們并不能因此斷言“限定性”和“扁平性”這兩個影像的根本特征就消失了——雖然它們不再是影像本身的特征,卻依舊是觀眾視野中影像的特征。因為,觀眾不能像全景鏡頭那樣長出滿頭“眼睛”,所以最終還需自己操控視角,在影像建構的環境中選擇觀看什么及如何觀看。換言之,傳統鏡頭就像“框定”有限信息給讀者閱讀的書籍,而全景鏡頭則是360度全方位捕捉信息的互聯網。從傳統影像到全景影像,不止“眼睛”多了些、畫面多了些,更展現了信息時代的氣質。
與此同時,如果從傳統到全景,“景”的捕捉變成了“境”的捕捉,那么分鏡和剪輯產生的畫面銜接,將變成立體空間的銜接;如果“畫面銜接”尚符合眼睛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接受方式,較易被建構成一個具有時空連續性的事件,那么“空間銜接”則超越了我們的日常體驗,帶來的將是一種時空傳送的奇幻穿越感。所以,比起傳統影像,若非為了特地制造以上效果,現在的全景拍攝實踐往往會選擇大幅度減少“分鏡”和“剪輯”。
取景、攝影機運動、分鏡和剪輯是傳統影像表義的基本手段。現在,它們有的需要被重新定義(取景),有的被讓渡給了觀眾(推、拉、搖),有的需要大幅度減少(分境和剪輯),但最終發現,最符合全景拍攝技術特性的拍攝模式,竟然是最為“省事”的“固定長鏡頭”!如果在看什么和如何看的問題上,觀眾的決定權越來越大,而制作者的決定權越來越小,又如何保障影像語言的表義效果呢?
這個問題在會議報道中同樣存在。會議影像有其一套獨特的鏡頭語言,何時推、何時拉、從什么地方開始搖、又朝著哪個方向移都很有講究。鏡頭的秩序配合著會議的秩序,而會議的秩序又象征著社會的秩序,鏡頭、會議和社會構成的是一個秩序井然的隱喻系統。那么,如果用全景報道會議,就難免要把傳統報道中相當于鏡頭運動的“權利”讓渡給觀眾,讓觀眾自己決定觀看的先后和方向、聚焦的時間和范圍,這又如何保證會議報道的影像表義呢?
融合:秩序和多元的并存
新華網VR兩會報道之傅瑩新聞發布會是全景會議報道的優秀案例。針對會議過程的報道約140秒,除去傅瑩回答慈善法(31秒)、二孩政策(24秒)和“十三五”規劃(21秒)的三個長鏡頭,剩下60余秒的報道由7個鏡頭剪輯而成,這些鏡頭又分別來自位于同一會場的3個不同機位。拍攝者在由多個鏡頭構成的360度鏡頭之中規定出了一個“默認”鏡頭,如果觀眾僅僅像觀看傳統新聞那樣觀看該報道,那么整個視頻的“默認”影像則按照這個“默認”鏡頭框定的畫面編輯而成,最終的報道呈現依舊是由這三個機位提供的分境剪輯而成的傳統會議報道。可以說,它遵守的還是會議報道的鏡頭語法和剪輯模式。在這樣的鏡頭語言中,會議室是一個有視覺中心的空間,會議是一個由秩序建構的會議,而發布會則是以制作者的視角展現出來的會議過程。
但如果觀眾拖動鼠標操縱自己的視角,以“非默認”的方式觀看報道,那么他們看到的就不僅是默認鏡頭中的發言人,也可能是轉換視角后的觀眾;不僅是默認畫面中認真作記錄的觀眾,也可能是正在自拍甚至拍全景鏡頭本身的觀眾……這樣一來,會議室就從一個秩序空間變為探索空間,會議也立刻由秩序建構的會議變為具有某種互動自由度的會議。換言之,會議在其“默認”觀看方式之外,增加了觀眾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實現的個性體驗方式。這不僅體現了會議報道的視角變得更加多元,而且意味著觀眾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報道本身,更體現了會議報道的視角變得更加多元。
不難看出,正是互聯網和新媒體促進了報道的多元性,在這層意義上,VR全景報道不僅要在技術上是新媒體的,而且在文化和理念上也是新媒體的,才真正符合“媒體融合”的要求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