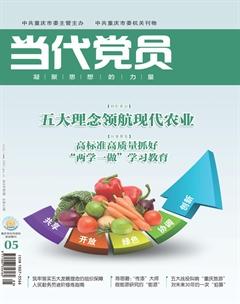陳思碧:“傳漆”大師
唐余方
她是一位92歲的老人,聽力退化,腿腳不便,但精神矍鑠,仍然堅持漆器創作。
她是重慶目前唯一健在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漆器的傳承是她心頭一個難解的結。
“做漆器對我來說就像吃飯一樣,我真是舍不得這個東西。”陳思碧說。
摯愛
2015年11月17日,記者在渝中區陳思碧的家中見到了她。
身材瘦削的陳思碧穿著紅綢外衣,屈腿坐在紅木椅子里。因聽力嚴重退化,她不得不將頭前傾,才能聽清對方在說什么。
陳思碧與漆器的緣分似乎是命運使然。她生于1924年,長于動蕩時代,幼時的她,唯一的愛好就是畫畫。
小時候看著母親鉤花,她不用人教便能自己學會;初中的圖畫課,讓她一頭扎進藝術的世界……
“畢業時,其他同學都選擇去當老師,只有我選擇了上美術學院。”1942年,陳思碧考入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現四川美術學院)。
在這里,她師從李有行、沈福文等名師,學習最苦最難的漆器專業。
“漆器創作苦,很多人都不愿意學,生漆從樹上割下來,有的同學過敏。還好,我通過了考驗。”她說。
這是全國第一個開設漆器專業的學校,當時僅有七名學生,陳思碧便是其中之一。
陳思碧學習起來很玩命:從底胎的骨架到設計造型,再到裝飾,幾十道原本分開的工序,她都能獨立完成。
對于作品的藝術效果,她的要求也極為嚴苛,常常會為了一種理想的顏色而整夜調試。
“當時沒有‘丹紅色,為了這個顏色,我就自己出錢買材料來燒制。”陳思碧說。
“你要做這個顏色,就得一直守到起燒哦。”老師提醒她。
“守就守。”她硬是寸步不離守到了次日早上。
陳思碧始終對漆器創作保持著高度的熱愛,如果不是因為這份愛,她現在也許還能下樓遛彎。
“漆器廠下面有個石洞,里面涼快,溫度正好適合漆器自然風干,我就喜歡沒日沒夜地在里面干活。”洞里潮濕,很多人都得了關節炎,與陳思碧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去看了醫生,但她忙于創作,總抽不出時間去看病。
“腿上的病根就是那時候落下的,這病跟著年齡走,年紀越大就越惱火。”陳思碧低頭拍了拍自己的腿。如今,她已經無法再靠這雙腿走路了。
大師
毫無疑問,陳思碧是學校里最優秀的學生。令人意外的是,畢業后她卻沒能繼續從事最愛的漆器創作。
“我被分到四川資陽教美術,后來又去了其他地方教書。”學生們很喜歡美術,覺得新奇,但這并不能填補陳思碧內心的失落。教書之余,陳思碧就在家里埋頭創作漆器。
看到書上有人將蛋殼鑲嵌在漆器上,她覺得有趣,便開始研究。
“我看著看著就覺得不對,只有白色,太單一了。”于是,陳思碧搜集了各種顏色的蛋殼,首創了漆器“彩色蛋殼鑲嵌技法”。
上世紀50年代,國家號召“技術歸隊”,陳思碧選擇回到母校,作為專業人才,進入學校開辦的漆器實驗工廠(即現在的重慶美術漆器廠)工作。
人人都知道做漆器很辛苦,可陳思碧樂在其中。她雖負責設計,但每個制作環節都積極參與,并且掌握得很好。
“構圖嚴密精整,表現出絕高的藝術造詣。”原國家輕工部所編《輕工史話選編》如此評價陳思碧的作品。
曾經,廣州某單位想高薪聘請陳思碧去任教,但她斷然拒絕了。
幾十年來,欲高薪聘請陳思碧的單位又何止這一家,但全被她一一拒絕。
“我是在重慶起頭的,要把手藝留在重慶。”這是陳思碧的心愿。
陳思碧的一生中有許多重要時刻,大都與漆器相關。
1957年,她的漆器作品《蛋殼嵌鳳盤》,獲得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美術競賽銀獎。
這是一次國際比賽,有100多個國家的藝術家參賽。憑借這個銀獎,陳思碧成為當時國內為數不多獲得國際大獎的藝術家。
1988年,陳思碧成為重慶市第一位高級工藝美術師,四川省工藝美術大師。
1990年,她被評為中國漆藝家。
1992年,她成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
1993年,她被評為第三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重慶獲此殊榮的僅有三人。
2009年,陳思碧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漆器髹飾技藝代表性傳承人。
傳承
斗轉星移,時光流轉。陳思碧守著一顆純粹的匠心,躲過了戰爭,躲過了“文革”,卻沒能躲過時代的變遷。漆器的衰落,給這位大師的暮年平添了一縷哀愁。
“隨著時代和人們審美觀念的變化,漆器的需求越來越小,學漆器創作的人也越來越少。”老人的身體深陷在椅子里,顯得有點落寞。她終日呆在家里,靠訂閱的兩份報紙了解外面的世界。
“之前看報紙,有個美術展覽,各個門類都有展出作品,唯獨沒有漆器。”陳思碧沒法不嘆氣。
“沒人買”和“沒人做”是包括漆器在內的傳統工藝面臨的困境。
陳思碧一直想把漆器工藝傳承下去,年輕的時候,她便開始未雨綢繆帶徒弟,但許多徒弟最后都離開了這個行業。當初,國家倡導讓大師“帶個子女學”,她便帶著兒媳朱華學習漆器創作。
如今,朱華已成為陳思碧的傳承人,也在重慶申報第七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推薦人員名單之列。
為了將這門工藝傳承下去,陳思碧還做了許多嘗試:讓朱華參加每年的藝術文化活動,“一次都不缺席,有現場展示,讓漆器露露臉”;她覺得靠嘴來講授漆器知識太慢,便特意撰寫了一本名為《重慶漆藝》的專業著作,已于2007年出版。
“但我后來發現學校都沒有漆器專業了,這書給誰看呢?都是理論知識,人們看了又去哪兒接受專業訓練呢?”為此,陳思碧和朱華又開了一間工作室。
工作室由陳思碧自己的房子改建,為把房子騰出來,她搬來和兒子兒媳一起住。工作室目前有五六個學徒,最大的六十幾歲,最小的二十幾歲。
“傳統工藝之所以傳承難,就是因為新人學得慢,老人老得快。”這也是讓陳思碧最揪心的。
老人們正在不斷離開。2015年9月,同屬“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黃楊木雕大師柯愈勄去世,陳思碧成為重慶目前唯一健在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我現在啥子都不想,做完一件作品就感到快活。”盡管前景堪憂,但陳思碧并沒放棄漆器的創作和傳承。
她通常早上6點半起床,晚上11點半才入睡,整天的時間都花在創作和閱讀上。因為腿腳不便,她常常摔倒,有一次摔倒后,她的右手骨折,康復后又繼續創作。
沒法去工作室,她便讓徒弟們來家里,一點一點講,手把手地教。
盡管已經92歲,但陳思碧的狀態仍與年輕時候一樣,工作起來便會忘記吃飯和上廁所。
“我現在正在設計一幅長約3米、寬約半米的作品,準備漆在家里客廳的橫梁上。”說著,陳思碧讓兒子把她的稿紙拿來給記者看——造型各異的竹鶴躍然于長長的宣紙上,栩栩如生,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