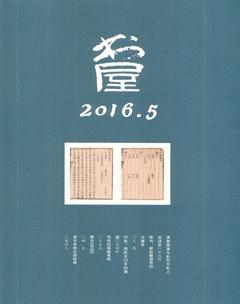“湖湘文化十杰”芻議
王強山
一
2015年湖南文化界有一件大事,就是由千年學府岳麓書院發起,著名湘籍學者唐浩明、鄭佳明、朱漢民、王魯湘領銜啟動的“湖湘文化十杰”評選活動。
湖湘之地向稱人文薈萃,自屈原、賈誼以及宋代理學之宗周敦頤、明末大儒王夫之,至近代而人才趨于極盛。如何在燦若星辰的歷代湖湘文化名人中選出十個對湖湘文化貢獻最大,也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人物,這確實是個難題。為此,組委會確立了幾條評選標準:一、上自先秦、截至1949年以前去世的有詳細資料考證真實存在的人物(神話傳說人物不在此列)。二、對湖湘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在文史哲領域豐富了湖湘文化內涵的、對湖南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經濟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三、個人影響力不止于湖南,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且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人物。四、籍貫地不限于湖南,但正史記載確在湖南生活過相當長時間。
根據這一標準,組委會列出了三十六個候選人名單,并附上其簡介(簡介略):
屈原、賈誼、蔡倫、張仲景、歐陽詢、懷素、柳宗元、溈山靈祐、周敦頤、胡安國、胡宏、張栻、歐陽玄、李東陽、王夫之、羅典、歐陽厚均、鄧顯鶴、陶澍、賀長齡、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王闿運、王先謙、譚嗣同、楊昌濟、黃興、熊希齡、楊度、陳天華、蔡鍔、宋教仁、蔡和森
確立了候選人名單后,下一步就是評選的辦法了。這次評選首開“互聯網+傳統文化”模式的先河,也就是并非由宣傳部門主導,而是由學者發起,全民參與,自下而上的評選,網友投票的權重為百分之五十,分量最重。著名湘籍學者唐浩明、鄭佳明、朱漢民、王魯湘組成的總評委只占總權重的百分之二十;知名湘籍學者、文化名流夏劍欽、周秋光、廖名春、龔旭東、歐陽哲生、孟澤、陳明、肖永明、十年砍柴、譚伯牛等擔任的推選委員會占總權重的百分之三十。
“湖湘文化十杰”評選活動正式啟動后,各地網友踴躍參與,他們通過鳳凰網湖南頻道、紅網等專題頁面或微信平臺等通道進行投票,選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湖湘文化人物。據統計,到截止日,投票的網友人數(次)超過六百七十萬,周敦頤得票高達四十九萬余。票數超過四十萬的還有屈原、張栻、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從投票網友的地域分布來看,其中湖南省內ID占比為百分之五十九點三,廣東、湖北、安徽、陜西、上海、廣西、福建、北京、江西、貴州、新疆等地網友投票人數占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港、澳、臺地區投票占比近百分之六點九。活動還吸引了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華人、華僑及留學生群體參與,海外參與投票ID接近百分之零點四九,近兩萬人(次)國外網友參與投票。
經過一個多月網友投票與專家評審,最終確定了十位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杰出人物榜單,他們是:屈原、周敦頤、張栻、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黃興、蔡鍔。
二
我以為,網友與專家學者共同評選出來的這個“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單還是較好反映了湖湘文化形成發展的清晰脈絡以及湖湘文化的內在精神,但有美中不足。
湖湘文化的形成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從戰國時期屈原入湘到北宋初期滕子京被貶岳州為第一階段,屬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注入湖湘,成為湖湘文化母體的時期。從北宋中期周敦頤開創理學,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對傳統學術與文化進行系統性批判總結為第二階段,屬于湖湘文化內在精神傳統形成與豐富的時期。清代以來至今屬第三階段,為湖湘文化這一內在精神傳統的闡釋、實踐、傳播(向省外)、創新與超越時期。所以,這次岳麓書院推出的“湖湘文化十杰”應當屬于這三個階段關鍵節點上的重要人物。在我看來,榮登這個榜單的十人中有七人非常恰當,但近代史上以事功聞名于世的左宗棠、黃興和蔡鍔入選卻差強人意,而宋代的胡宏和近代的郭嵩燾、宋教仁似可取而代之。
屈原雖不是湖南人,但他入選“湖湘文化十杰”卻是專業學者與網友兩個層面爭議較少的,這主要緣于他對湖湘文化形成的第一階段的獨特意義。
屈原入湘后,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傳播楚文化,從而使湖湘土著文化與楚文化碰撞與融合。可以說一部《楚辭》就是屈原將湖湘土著文化與楚文化結合而成的代表之作,成為后世湖湘文化的重要源頭。特別是屈原悲壯自沉后,其愛國憂世的情懷以及上下求索的人格魅力不斷被后世的湖湘士人(或外地入湘士人)歌頌,被老百姓以各種方式紀念,從而形成上下求索,心憂天下的文化內涵。
屈原之后漢代有賈誼被放逐入湘,唐代則有大量的士人或被貶謫或來湖南游歷。開元年間中書令張說被貶岳州,其后有孟浩然、李白、杜甫、王昌齡、柳宗元、劉禹錫、韓愈、白居易及元稹等先后入湘,他們或歌或詠,留下了大量的詩文,提升了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格調。這種中原文化對湘楚文化的注入和提升基本上到宋初完成,其標志則是滕子京被貶岳州,重修岳陽樓,請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提煉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化情懷。
以上為湖湘文化形成的第一階段,從文化形態言之,屬于傳播型的、詩性的、浪漫主義的文化形態。超越屈原等人對湖湘文化的貢獻,并實現從傳播型的文化形態到原創型的文化形態,從詩性的文化形態到哲學的文化形態,從浪漫主義的文化形態到現實主義的文化形態的轉變,則屬于湖湘文化的第二階段。這個過程從周敦頤發其端,中經胡宏、張栻,最終到王夫之集大成,形成以理學精神為核心的湖湘文化的學統與經世致用的學風。
這次“湖湘文化十杰”的評選活動中,作為出生于湖南本土的候選人,周敦頤是專業學者和網友兩個層面最少爭議的人物,從網友投票中周敦頤高居榜首可見一斑。周敦頤是第一個出生于湖南但真正有全國性影響的思想家,他對于湖湘文化最大的貢獻在于創立理學,把儒學上升到純哲學的高度,而宋代以后理學即成為湖湘文化的內核。也就是說,周敦頤是湖湘文化內在精神傳統即學統的開創者,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這個“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單中沒有胡安國、胡宏父子,特別是沒有胡宏卻頗令人遺憾,因為他是周敦頤開創的湘學內在精神傳統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的關鍵人物。
周敦頤開創理學,傳承至二程、胡宏、張栻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周敦頤創立理學之時并未對湖南產生太大的影響,其弟子程顥、程頤也缺乏對湖湘文化直接的貢獻。胡宏雖不是湖南本土人,但他在湖南生活、講學二十余載,并正式創立“湖湘學派”。
胡宏原籍福建崇安,是北宋末期著名經學家、理學家胡安國幼子,很小即隨父學習并接受其理學思想,后師事二程弟子楊時和侯仲良,終至發揚光大理學思想,著有《知言》、《皇王大紀》等。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是對周敦頤、二程學說的繼承,其探討的主要范疇仍不出道、理、心、性等,但他對這些范疇的發揮和運用卻表現了許多獨到之處。如二程哲學以“理”為宇宙本體,胡宏哲學本體卻是“性”。在“性”與“心”的關系問題上,胡宏以“性”為體,以“心”為用,二者的關系表現為未發為“性”,已發為“心”。后來“朱張會講”時朱熹和張栻就反復圍繞這一命題辯論。在“性”與“物”的關系問題上,胡宏認為“非性無物,非氣無形”。因此其性本體論既不同于二程洛學的理本體論,也不同于張載關學的氣本體論,是當時湖湘學派能作為一個獨立學派區別于洛學、關學與閩學的重要原因。
在人性論問題上,胡宏也反對以善惡論性,認為人性本為中道,世儒以善惡言性,不過是遠離實際的迂闊之論。其人性論闡述雖不夠周密,但有其獨到之處,對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的論斷似有啟發。
在認識論問題上,程朱理學都講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但他提出“緣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觀,其命題亦有獨到之處。特別是他認為“道可述,不可作”,即作為客觀規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可以認識它,但不可以制造和改變它,這樣就肯定了事物規律的客觀性,與周敦頤、二程明顯不同,對王夫之的認識論有一定的啟發。以上思想及其影響表明胡宏作為一代理學宗師,其地位是無可辯駁的。
胡宏之所以應登上這個“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單,不僅在于其理學思想是對周敦頤以來理學的繼承與創新,還在于他正式將理學思想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成為湖湘文化的內在精神傳統。
宋高宗建炎年間(1127—1130),胡宏隨父兄由荊門南渡湖南。其父胡安國在潭州湘潭建碧泉書院,后又在衡山山麓辦文定書院,以講學著述為業,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憲等以外,還吸引了眾多湖湘子弟前來就學。紹興八年(1138)胡安國在湖南逝世,其后胡宏繼承父業,繼續在衡山等地講學二十余年。一批批志學求道的學人紛紛前來衡山追隨胡宏研經讀史,其中就包括張栻。至此,胡宏在思想體系和人才群體上奠定了湖湘學派的基礎,正如錢穆所論:“南渡以來,湖湘之學稱盛,而胡宏仁仲歸然為之宗師,學者稱為五峰先生。”
考慮到組委會所宣稱的“湖湘文化十杰”要“能體現出湖湘文化清晰的傳承淵源和代際特點”,我以為胡宏上承周敦頤,下啟張栻,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張栻原籍漢州綿竹,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書院教事,從學者達數千人,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成為一代學宗,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主要著作有《南軒先生論語解》、《南軒先生孟子說》等。
張栻理學思想上承二程,并極力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為萬物之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這種知行觀成為湖湘文化注重“經濟之學”,重視踐履的重要精神源頭。
張栻思想對朱熹亦多有啟發。乾道三年(1167),朱熹聞張栻得衡山胡宏之學,并主講岳麓、城南兩書院,乃由弟子陪同,從福建崇安啟程來長沙,與張栻會友講學,展開學術辯論,即歷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兩人的辯論與相互影響,開創了書院自由講學之新風,對于加強各學派之間的學術交流,促進學術思想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次“朱張會講”的“潭州嘉會”歷時兩個月,兩人講學于岳麓、城南兩書院,附近學者聞風而至,聽者甚眾,盛況空前,成為中國書院史和湖湘文化史上的大事。
張栻對湖湘文化的獨特貢獻還在于將湖湘學派的重心從南岳衡山轉移至長沙,并使岳麓書院成為湖南乃至全國的理學重鎮。如果說胡宏將周敦頤開創的湖湘文化內在精神傳統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的話,那么張栻則是使這一學統在湖南蔚然成林的關鍵人物。他在長沙培養了一大批弟子,如胡大時、彭龜年、游九功及游九言等,他們成為張栻之后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
元、明兩代湖湘學派薪火相傳,人才輩出,但都無法達到宋代理學家的高度,直到明季清初王夫之橫空出世,成為湖湘文化史上與周敦頤并峙的又一座豐碑。
王夫之一生著述一百多種,其中最重要的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張子正蒙注》、《思問錄》、《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及《春秋世論》等,對宋明理學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學術、文化進行批判與總結。
在本體論與宇宙觀問題上,他繼承了張載關學“氣”一元論傳統,但并沒有停留在前輩哲人的水平上,而對“氣”的范疇作出了新的哲學規定,形成“太虛一實”的宇宙觀。同時在宋明理學中長期爭論的“理”、“氣”關系問題上作了深入闡述,駁斥了程朱理學“理本氣末”、“理主氣從”的本體論。在道器關系上,他針對程朱理學用“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的劃分來割裂道與器的統一,提出“道在器中”的道器觀。他進而提出“絪缊化生”,“要歸兩端”的矛盾觀,“動靜皆動”、“變化日新”的運動觀,“理勢相成”、“即民見天”的歷史觀,以及“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認識論,全面批判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總結了中國古代哲學長期爭論的理氣、道器、有無、體用、動靜、常變、古今、理勢、理欲、能所、心物、心理、知行以及天人等關系問題,把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思辨提高到一個全新的水平。王夫之哲學具有深刻而完備的理論形式,反映了明清之際時代精神的精華,標志著中國古代獨斷哲學的終結,成為近代啟蒙思想的重要源頭。他還從其知行觀出發,系統而全面地論證和闡釋“通經史以致用”的學風,成為近代湖湘士人的一面重要旗幟。
王夫之史學著作最重要的是《讀通鑒論》與《宋論》,這兩部巨著經過郭嵩燾的大力弘揚,在清末引起足夠的重視,其民族主義思想被大力挖掘,成為清末民族意識覺醒的重要精神來源。
如果說周敦頤是湖湘文化內在精神傳統的開創者,王夫之則是它的完善者與集大成者,往后人物則是對它的闡釋、傳播、實踐、創新與超越。所以清代以來能登上“湖湘文化十杰”這個榜單的人物,一定要在這幾個方面有獨到的貢獻。
三
清嘉、道年間,一個后世稱之為“經世派”的湖湘士子群體拔地而起,從陶澍、魏源到湯鵬、賀長齡、羅典、歐陽厚均、鄧顯鶴和唐鑒等人,他們慨然卓立,以經營天下為志。他們打破乾嘉學派重考據、鉆故紙堆的學風,對國家的漕運、河務、鹽政、科舉、官制、賦役、錢幣、兵丁、邊輿以及道德、風氣和學術等都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思想,系統性地闡釋從張栻到王夫之大力提倡的通經以濟世的思想。這個群體中,魏源無疑是杰出代表,他登上這個“湖湘文化十杰”榜單也較少爭議。
魏源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轉折大時代,潛心經世致用之學,編輯而成《皇朝經世文編》。鴉片戰爭期間,魏源任職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發憤著《圣武記》,以清初軍事成就激發愛國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后來他受林則徐委托,編成《海國圖志》,成為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巨著,對中國人了解西方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成為洋務派辦洋務的理論來源。
隨后,以曾、左、彭、胡為代表的“中興名臣”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至此,湖湘士子群體已不再是囿于湖南一地指點江山,議論風發,而是位寄封疆,手握實權,將湖湘文化的內在精神轉化為現實的力量,在中國這個大舞臺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曾國藩無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曾國藩在成就非凡事成的同時,以其言傳身教和各種著述,把湖湘文化的內在精神闡釋得淋漓盡致。太平軍起事以后迅速壯大,清廷正規的綠營兵和八旗軍不堪一擊,曾國藩毅然以一介書生墨绖出山,組建湘勇。面對勢力全盛之時的太平軍,曾國藩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咬緊牙關,苦撐危局,最終以杜鵑啼血之誠、精衛填海之力,從容補救,轉危為安。曾國藩說:“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他將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學風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行之有節,持之以恒,大智大勇,坦蕩無畏,擔荷起世道人心。以書生救國,曾國藩走到了傳統“人臣”的最高階段,時人即把他與孔子、王陽明并稱,謂之為成就了“三不朽”事業的非凡人物。
然而,同樣作為湘軍重要將領,左宗棠入選“十杰”卻爭議頗多。
左宗棠一生的主要成就是三大事功:其一為協助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其二為平定陜甘回民之亂,其三為收復新疆。收復新疆之役使左宗棠成為著名的民族英雄,在事功上或可超越平定洪楊之役。但是作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政治思想、洋務主張以及對世道人心的影響,都無法與曾國藩相提并論,其他如彭玉麟、胡林翼等中興名臣也大多數如此,其文化影響力皆可由曾國藩所代表,但郭嵩燾是個例外。
郭嵩燾是這一時期湖湘士人群體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他不但對自周敦頤至王夫之的湖湘學統熟稔于心,而且在思想上超越洋務派,下啟維新派,開近代湖湘西學之風氣,其后湖南倡時務學堂,向日本等國派遣留學生,都受到他的影響。郭嵩燾是湖湘文化史上從舊學到新學過渡的關鍵人物,所以他在湖湘文化史乃至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弘揚湖湘文化學統方面,郭嵩燾特別推崇王夫之,為之建船山祠、思賢講舍并奏請朝廷將王夫之從祀文廟。在建船山祠時,郭嵩燾親撰碑記,將王夫之與周敦頤并列為湖湘學術與文化上的兩大豐碑。
在洋務思想上,郭嵩燾認識到道光以來中國之開埠不僅僅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是世界潮流之必然。郭嘗言:“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之一大變。其氣機甚遠,得其道而順應之,亦足為中國之利。”郭嵩燾在使英期間曾與嚴復探討如何學習西法的問題。嚴復引左宗棠的話說:“泰西有,中國不必傲以無;泰西巧,中國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駿,則我不得騎驢;人既操舟,則我不得結筏。”左宗棠的觀點代表了絕大部分洋務派希望仿效西方、實現堅船利炮的主張,郭對此主張卻頗不以為然。他認為洋務實踐應以通商為本,培育經濟基礎;以政教為本,行君主立憲,培育利于工商的政治環境;以人心風俗為本,培育良好的社會風氣與人才群體。郭晚年“不以顯晦進退為異”,孜孜于教育事業,掌教城南書院,恢復湘水校經堂,創辦思賢講舍,并創立禁煙公社,正是因為他深刻認識到教育事業與人心風俗之重要。
正由于郭嵩燾的見識超出儕輩甚遠,所以他對當時最知名的洋務官員都有所批評,除左宗棠外,還包括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彭玉麟、曾紀澤及張之洞等。
郭嵩燾對于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是有清醒認識的,所以才敢于“置區區世俗之毀譽”于不顧,毅然承擔起“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的重任。這種愛國熱忱與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以及敢為天下先的自醒自覺,實與湖湘文化內在精神傳統一脈相承;其從政治、經濟及思想文化領域全面改革的主張,既是對洋務派思想的全面超越,又實為譚嗣同等維新派思想之先聲。愚以為,在“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單上,郭嵩燾之取代左宗棠是站得住腳的。
譚嗣同作為維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近代湖湘士人中的地位無可替代。早年譚嗣同亦深受湖湘經世學風影響,注重實學。甲午戰爭后,譚嗣同思想發生劇變,開始擺脫舊學羈絆,成為沖決專制羅網的激進的維新志士。
譚嗣同主要的著作為1896年寫成的《仁學》,該書大聲疾呼變法維新是救亡圖存的當務之急,“變法則民智”,“變法則民富”,“變法則民強”,“變法則民生”。《仁學》還勇敢地發出“沖決網羅”的呼聲,不但要“沖決利祿之網羅”、“俗學之網羅”,還要“沖決君主之網羅”、“倫常之網羅”,這種反君主專制的思想,閃爍著民主主義的思想光輝。
1897年10月,譚嗣同棄官回湘,在巡撫陳寶箴支持下,與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積極開展變法維新的宣傳與組織活動,提倡新學,籌劃新政,使湖南成為當時全國變法運動中最富有朝氣的省份。
1898年夏,光緒帝下詔變法。譚嗣同被召以“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旋即百日維新失敗,譚嗣同以自己的犧牲向頑固守舊勢力作最后的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以身殉道,開創了湖湘士人新的救國之路,也激勵著以黃興、宋教仁和蔡鍔“辛亥湖南三杰”為代表的革命志士。
黃興和蔡鍔在辛亥革命和之后的護國運動中以事功著稱,兩人基本上屬于同一類人物,但宋教仁的政學思想與實踐卻遠超黃興與蔡鍔。
宋教仁于1903年結識黃興,1904年與黃興等正式成立華興會,同年東渡日本,入東京政法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1905年孫中山等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宋教仁成為與孫中山、黃興并稱的主要領導人,但宋的政治理念與孫、黃都有很大差異。
1905年8月,清廷剛開始預備立憲,宋教仁立即發表文章,剖析清廷立憲的可能性。他認為“立憲國民,其義務必平等”,“立憲國民,其權利必平等”,“立憲國民,有監督財政之權”,從這三個方面看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憲。義務平等、權利平等、監督財政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與基本制度框架。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12月25日孫中山回國,第二天在寓所召開同盟會高級干部會議,討論未來新政府的組織方案時即出現重大分歧。宋教仁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制,他說:“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他之所以堅決主張責任內閣制,主要在于他試圖通過這一制度性的設計而由革命黨人掌握政府的實際權力,從而排除專制制度、專制思想以及可能存在的政治強人對新政權的不良影響。
但孫中山堅決主張總統制,且得到多數與會者的支持,會議最終決定實行總統制。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長。不久形勢發生戲劇性變化。2月12日,清帝遜位,依照以前革命黨與袁世凱達成的協定,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由袁世凱繼任。這時革命黨人一致決定未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這一制度作了憲法保障。
這年秋天宋教仁聯合五個政黨組建國民黨,他認為新建立的國民黨屬于“革命的政黨”,不同于以前屬于“革命黨”的同盟會。1913年2月1日,他在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革命黨”與“革命的政黨”的概念,“革命黨”與“革命的政黨”的區別在于:“革命黨”是秘密的組織,“革命的政黨”是公開的組織;“革命黨”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的組織,“革命的政黨”是“新的建設時期”的組織;“革命黨”對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斗”,“革命的政黨”對于“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斗”。他堅信“雖然我們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于我們。”他進一步論述:“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后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后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隨后(1913年3月)舉行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參、眾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宋教仁此時已是眾望所歸,實現其政黨政治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然而,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車站一顆罪惡的子彈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也擊碎了民初民主政治的夢想。國民黨失去精神支柱與能夠駕馭全局的領袖,很快就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之下四分五裂,孫中山、黃興也借機發動“二次革命”,中國再次陷入戰爭與動蕩之中。
綜上所述,屈原代表湖湘文化發展史上的第一階段,即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注入湖湘,成為湖湘文化的母體,形成上下求索、心憂天下的家國情懷;周敦頤、胡宏、張栻和王夫之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二階段,形成以理學精神為核心的湖湘文化內在精神傳統,包括理學的道統、學統以及經世致用的學風;魏源、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和宋教仁則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三階段,體現了對湖湘文化這一內在精神傳統的闡釋、實踐、傳播、創新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