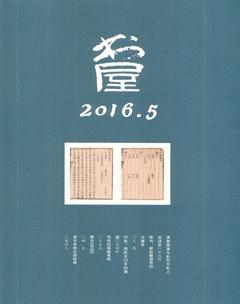環(huán)境變遷視角下的中國(guó)史
陳華文
近年來(lái)大江南北持續(xù)不斷的霧霾,使得人們普遍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健康產(chǎn)生了擔(dān)憂。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的任何變化,已經(jīng)不是理論問(wèn)題,而是實(shí)實(shí)在在和每個(gè)人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僅是民生問(wèn)題,同樣也是國(guó)家大事。而有關(guān)中國(guó)歷史興衰的解讀,其著作盡管汗牛充棟,但是不外乎從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等維度切入。若按照時(shí)間年代的順序,從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角度探究中國(guó)歷史,這顯然是冒險(xiǎn)之舉。一來(lái)環(huán)境變遷涉及氣候、地質(zhì)、農(nóng)業(yè)、水利等眾多領(lǐng)域,二來(lái)自古以來(lái)關(guān)于環(huán)境變遷的文獻(xiàn)稀少、零碎,這些客觀存在的困難,使得很多學(xué)者在環(huán)境史研究面前怯而止步。然而美國(guó)學(xué)者馬立博(Robert B.Marks)卻是一個(gè)敢闖學(xué)術(shù)險(xiǎn)灘的人,其《中國(guó)環(huán)境史:從史前到現(xiàn)代》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首部中國(guó)環(huán)境通史出自美國(guó)學(xué)者之手
馬立博教授長(zhǎng)期在加州惠爾特學(xué)院研究中國(guó)史、全球史和環(huán)境史。除了本書之外,中譯本著作還有《現(xiàn)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tài)的述說(shuō)》、《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jì)》等。《中國(guó)環(huán)境史:從史前到現(xiàn)代》共分為六大章節(jié),按照編年史的方式,由遠(yuǎn)及近地考察了中國(guó)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與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之間的交互影響。這種宏大的敘史方式,不僅考驗(yàn)著學(xué)者的綜合知識(shí)素養(yǎng),還彰顯出學(xué)者對(duì)交叉學(xué)科的高度駕馭能力。
這本著作是至今為止由西方學(xué)者撰寫的第一部中國(guó)環(huán)境通史,著作在廣泛吸收西方學(xué)術(shù)界有關(guān)中國(guó)各歷史時(shí)期、各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及其與人類社會(huì)關(guān)系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綜合會(huì)通,對(duì)中國(guó)的長(zhǎng)時(shí)段人與環(huán)境互動(dòng)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全景式的動(dòng)態(tài)考察。書中指出:在數(shù)千年改造自然環(huán)境的過(guò)程中,一種獨(dú)具中國(guó)特色的經(jīng)由市場(chǎng)聯(lián)系的中央政權(quán)和農(nóng)業(yè)家庭相結(jié)合的方式產(chǎn)生了關(guān)鍵影響。而中國(guó)發(fā)達(dá)的農(nóng)業(yè)在養(yǎng)活大量人口的同時(shí),也加劇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單一化。馬立博教授在研究中還發(fā)現(xiàn):中國(guó)文化中雖然很早就形成了節(jié)制開發(fā)資源的思想觀念,但與經(jīng)濟(jì)和政治等因素相比,這種觀念卻并沒(méi)能發(fā)揮應(yīng)有的影響。
在閱讀此書時(shí),筆者不禁聯(lián)想起英國(guó)著名學(xué)者伊懋可(Hark Elvin)的著作——《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guó)環(huán)境史》(中文版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盡管這兩本著作都是英美學(xué)者撰寫,而在研究路向上各有千秋。馬立博教授的這部著作是環(huán)境“通史”,而伊懋可教授的著作只能算是環(huán)境“專題史”,既然是專題史,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對(duì)局部的、單個(gè)的生態(tài)研究問(wèn)題進(jìn)行探究,這樣的好處使得環(huán)境史研究更具有深度,可不免給人碎片化的印象。《中國(guó)環(huán)境史:從史前到現(xiàn)代》對(duì)于環(huán)境變遷的關(guān)注是整體的、系統(tǒng)的和綜合的,其缺點(diǎn)也顯而易見:對(duì)某些問(wèn)題的分析不免蜻蜓點(diǎn)水,某些生態(tài)問(wèn)題的研究?jī)H停留在轉(zhuǎn)述他人文獻(xiàn)的認(rèn)知表層。
《中國(guó)環(huán)境史:從史前到現(xiàn)代》廣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伊懋可的著述),但依然有很多新見,如:馬立博不贊同把中國(guó)環(huán)境史僅僅描述成數(shù)千年來(lái)人與野生動(dòng)物的戰(zhàn)爭(zhēng)史,而是高度重視漢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歷史生態(tài)關(guān)系,以很大的篇幅講述漢人與其他族群在生計(jì)關(guān)系、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差異,解說(shuō)了中國(guó)遼闊大地上多樣化生產(chǎn)方式和政治體系如何走向“單一化”。再如,他注意到數(shù)千年中國(guó)環(huán)境資源破壞與農(nóng)業(yè)持續(xù)發(fā)展和土地持續(xù)利用之間的矛盾現(xiàn)象,曾多處講述了地力維持和肥料問(wèn)題,這個(gè)觀點(diǎn)雖非首創(chuàng),但持論頗為中肯。
森林在中國(guó)歷史環(huán)境中扮演的角色
環(huán)境史的研究除了可以幫助我們拓寬歷史的視野、了解環(huán)境變遷的來(lái)龍去脈之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益的視角:透過(guò)歷史的進(jìn)程、在具體的歷史背景和國(guó)情中探討環(huán)境變遷的原因、影響和保護(hù)環(huán)境的辦法,既不要將二十一世紀(jì)的環(huán)境保護(hù)觀念強(qiáng)加到古人的身上求全責(zé)備,也應(yīng)該注意從當(dāng)前的國(guó)情和世情出發(fā),看待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生態(tài)困局。
環(huán)境史雖然更多關(guān)注的是自然和生態(tài)的變遷,但是也認(rèn)為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導(dǎo)致了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多樣化的減少。馬立博教授在書中指出:“中國(guó)數(shù)千年來(lái)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提供燃料、木材而進(jìn)行的大規(guī)模森林砍伐,嚴(yán)重破壞了野生動(dòng)物的棲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種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起嚴(yán)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積,進(jìn)而導(dǎo)致了大面積的生態(tài)退化。發(fā)達(dá)的農(nóng)業(yè)在養(yǎng)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時(shí),也造成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脆弱,并且在十九世紀(jì)以后變得日益不可持續(xù)。
遠(yuǎn)古的中國(guó),曾經(jīng)是地球上生物種類、數(shù)量最為豐富的地區(qū),大象、老虎、江豚等在陸地和河流中到處可見,可是幾千年過(guò)去了,這些動(dòng)物成為稀有物種,“蝸居”在遠(yuǎn)離人類的偏遠(yuǎn)地區(qū),而長(zhǎng)江中的白鰭豚“失聯(lián)”已久,不排除滅絕的可能。書中開篇引言中寫道:“數(shù)以百計(jì)的其他物種已在幾乎不為人知的情況下走向滅絕,中國(guó)將近百分之四十的顯存哺乳動(dòng)物種類處于瀕危狀態(tài),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植物種類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脅。”在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的進(jìn)程中,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觸目驚心,今天不僅動(dòng)植物處于生死掙扎的險(xiǎn)境,人類命運(yùn)的未來(lái)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驗(yàn)。
談到森林破壞的話題,筆者又不僅想到英國(guó)學(xué)者科林·塔奇的著作《樹的秘密生活》(中文版已由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5月出版),這本書中認(rèn)為:政治經(jīng)濟(jì)政策的制定,日常生活方式的選擇,都在一定程度上圍繞樹來(lái)思考和評(píng)估。從歷史的維度看,人類的先祖曾經(jīng)生活在樹上,后來(lái)慢慢從樹上走下來(lái),逐漸學(xué)會(huì)了直立行走和勞動(dòng),接著人類文明才得以誕生。森林在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扮演這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森林不僅僅意味著一片樹林,更是一個(gè)“群落”,它擁有種類眾多的有機(jī)體,涵蓋了從土壤到微生物直到食物鏈頂端的哺乳動(dòng)物。這些物種相互依存并且彼此之間,以及在與水、土壤和太陽(yáng)能之間存在平凡的互動(dòng)。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互動(dòng)的物種越多,那么這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也就越富于生物多樣性和健康活力。
秦漢之前,森林覆蓋了大半個(gè)中國(guó),自然資源豐富,生機(jī)盎然的場(chǎng)景可以想象。然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的進(jìn)步,尤其是鐵器的使用,使得墾荒的速度大為加強(qiáng),森林、荒地、沼澤都被開發(fā)為良田。糧食產(chǎn)量增長(zhǎng)的同時(shí),人口數(shù)量也在迅速膨脹。人與自然在此之前和諧相處,可是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兩者之間的裂痕顯現(xiàn)出來(lái),人與自然之間演繹成為不可調(diào)和的一對(duì)矛盾。
如何遏制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考驗(yàn)著社會(huì)治理水平
中國(guó)歷史文化在不斷朝前發(fā)展時(shí),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的腳步可謂勢(shì)不可擋。然而,當(dāng)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入瓶頸階段,也是一個(gè)王朝走向衰微、崩潰的開始。第六章“近代中國(guó)環(huán)境的退化:公元1800—1949年”中,馬立博引用了大量西方文獻(xiàn),對(duì)此進(jìn)行了論證。在二十世紀(jì)上半期,中國(guó)北方的森林砍伐直接導(dǎo)致渭河流域及其以北和以東的黃土高原出現(xiàn)了明顯的環(huán)境退化的跡象。到1930年代,原本人跡罕至的秦嶺山脈的森林,因?yàn)楣I(yè)生產(chǎn)的加快,森林成片消失。在那個(gè)時(shí)期的山東、山西境內(nèi),很多樹木都砍伐殆盡,連綿的山脈都是光禿禿的。
同樣,這個(gè)時(shí)期的華北平原,森林也采伐完畢,1900年年代時(shí),“曠野上根本沒(méi)有任何樹木或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種著谷物”。華北平原在古代曾經(jīng)和南方一樣,有過(guò)數(shù)百萬(wàn)的湖泊和沼澤,由于植被的破壞,這片大平原的生態(tài)逐漸惡化,到1980年代,只剩下可憐的二十個(gè)湖泊。水源的減少,使得土地出現(xiàn)沙化,土地更為貧瘠,這不光是嚴(yán)重制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進(jìn)而影響人們的糧食保障。書中指出,1876—1879年、1917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華北引發(fā)的大饑荒,造成了百萬(wàn)計(jì)人口的疾病和死亡。
本書作者馬立博在研究中國(guó)環(huán)境史之后引發(fā)這樣的感嘆:中國(guó)文化思想中固然有著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然而,統(tǒng)治者在社會(huì)治理中,并沒(méi)有真正按照這種自然觀念去踐行。不僅如此,英國(guó)學(xué)者伊懋可在中國(guó)環(huán)境專題史的研究中也引發(fā)同樣的感慨。
近年來(lái),中國(guó)整個(gè)社會(huì)都急切地意識(shí)到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與治理的重要性,國(guó)家制定了相當(dāng)“苛刻”的環(huán)評(píng)法規(guī)和工作機(jī)制。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得是否到位,人民是否滿意,已經(jīng)成為量化地方官員政績(jī)的重要指標(biāo)。回首幾千年的中國(guó)社會(huì)進(jìn)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一直在持續(xù)著,從來(lái)都沒(méi)有過(guò)“回暖”的趨勢(shì)。當(dāng)前的生態(tài)的治理,是一項(xiàng)牽涉到全體公民和眾多部門通力合作的大難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修復(fù),除了需要足夠的時(shí)間,還考驗(yàn)著全社會(huì)的智慧、決心和定力。當(dāng)前的中國(guó),作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其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今后若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中留下太多的欠債,對(duì)于世界、對(duì)于未來(lái)的子孫,都無(wú)法交代。
([美]馬立博著,關(guān)永強(qiáng)、高麗潔譯:《中國(guó)環(huán)境史:從史前到現(xiàn)代》,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