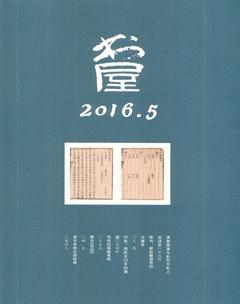也說“人彘之禍”
璩靜齋
在世人看來,西漢呂太后干的最為歹毒的事,莫過于她制造的“人彘之禍”——將高祖劉邦生前最寵愛的戚夫人砍斷手足,剜去雙眼,熏灼兩耳,強灌啞藥,殘害成沒有人形的“彘”(豬)。
制造這種駭人聽聞的“人彘之禍”,心毒如蛇蝎的呂后固然要遭天譴;若要細細追究這起禍事的起始緣由,劉邦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戚夫人年輕貌美,善歌舞,又生了一個酷似劉邦的兒子如意,因而戚夫人母子深得劉邦的寵愛。皇后呂雉生的太子劉盈為人仁弱,為劉邦所不喜,“高祖以為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劉邦有改立如意為太子之意,在戚夫人面前也毫不掩飾他的這種心跡。大凡人都是有欲望的,戚夫人也不例外。她是一個世俗的女人,并沒有多少長遠的識見,也談不上有多賢惠。作為母親的她自然不滿足兒子當一個諸侯王,而是渴望兒子有朝一日能登上帝王的寶座。劉邦對如意的偏愛無疑使戚夫人的欲望膨脹。為了滿足己欲,戚夫人也就依仗劉邦對她的寵愛,日夜對劉邦啼泣,央求劉邦讓兒子如意代替太子。劉邦竟不計后果地應允了。
如果劉邦真是一個英明睿智的帝王,他應站在大局、長遠的角度深思遠慮,不應因為個人私愛而輕易產生廢太子之心,從而激發戚夫人與呂后激烈的宮闈內爭,為日后埋下很深的隱患。
劉邦明明知道,廢嫡立庶不合情理。嫡長子王位繼承制是法定的,也是漢王朝“國之根本”的制度。劉盈是嫡長子,當這個太子理所應當,他又沒犯什么過錯,實在沒有理由廢掉他。而劉如意是庶子,立如意為太子,根本不符合王位繼承制,所以當劉邦提出廢劉盈立如意,大臣們都竭力反對、諫諍。性情堅忍耿直的御史大夫周昌態度尤為強硬,他口吃,盛怒之下說話更不利索(不時迸出“期期”二字),“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周昌旗幟鮮明地對劉邦強調兩點意見:一是廢太子不可以;二是如果陛下非要廢太子,他決不接受詔令。臣子冒死公開跟帝王唱對臺戲,說明廢太子的問題有多嚴重。
劉邦作為帝王,一言九鼎,他要一意孤行,堅持要廢太子,也沒有誰能阻攔得了的。只是此意愿真要付諸實踐,恐怕沒有那么簡單。太子雖仁弱,但皇后呂雉不是等閑之輩,她娘家的政治勢力也不可小覷,劉邦要廢太子,諸呂絕不會善罷甘休。
呂后好強爭勝,敢作敢為,而且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司馬遷在《史記》中稱其“為人剛毅”。當初劉邦定天下,韓信等功高震主的“危險大臣”被成功剪除,呂后從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這樣一個強悍而又有心計的發妻,劉邦有時也拿她沒轍。比如長公主(魯元公主)婚嫁的事,劉邦就說了不算。劉邦為了消弭匈奴邊患,采取屈辱的和親之策,準備將長公主外嫁單于。呂后只有魯元公主這么一個寶貝女兒,死活不同意讓女兒外嫁。為了讓劉邦徹底斷掉此念,呂后跟劉邦日夜哭鬧的同時,索性將女兒速嫁給趙王(張敖)。劉邦也無可奈何,只得找別人家的女子冒名頂替長公主去和親。
兒子太子位岌岌可危,呂后會是什么樣的感受?她本來就是一個嫉妒心很強的女人,劉邦寵愛戚夫人,漸漸將她冷落,已經讓她很嫉恨。如今劉邦寵愛如意,竟然要改立如意為太子!如意一旦當上太子,意味著什么?母以子貴,戚夫人遲早會取代她的皇后之位。呂后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她惶恐不安,氣恨交加,但一時又奈何劉邦不得,只能暗地里使些心計,逼著謀臣張良為她謀劃,“卑辭厚禮”請來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隱居于商山的四位老人)來“輔助”太子劉盈。此招甚為高明。當初劉邦屢次想請這四位隱士都沒有請動,如今他們肯為太子出山,昭示劉盈羽翼已豐,讓劉邦深感劉盈的太子地位難再動搖。倘若強行動搖,恐怕在他春秋后發生變亂。況且如意年幼,是一個時刻需要保護的孩子,如果非要讓這個孩子頭上頂著“太子”的帽子,一旦如意失去父皇的庇護,等待如意的將是被廢甚至被殺的悲慘下場。劉邦也就不得不斷廢太子之念。
劉邦清楚呂后的為人,他擔心自己“萬歲”后如意不能保全,特意選呂后和其他大臣們都敬畏的周昌擔任趙相,輔佐(抑或說庇護)趙王如意。至于他身后戚夫人的安全,他想顧怕是顧不上了。
呂后殫精竭慮地保住了兒子的太子位,心中的怨恨卻是一點沒減。盡管立太子的問題主要出在劉邦那兒,但在呂后的眼里,劉邦之所以要廢太子,是因為被戚氏這個賤女人灌了迷魂湯,為此她將所有的黑賬都記在戚夫人頭上,對戚夫人恨至骨髓。劉邦活著的時候,有劉邦這把保護大傘罩著戚夫人,呂雉尚不敢造次。等劉邦一死,她就開始“收拾”戚夫人,以解心頭積壓已久的怨怒。
關于呂太后處置戚夫人的整個過程,《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鑒》等史書均有所載,其中《漢書》交代得最為清晰。
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呂后最初將戚夫人囚禁于永巷,令人剃光她的秀發,頸脖束上鐵圈,穿赭色的囚衣,罰她舂米。此時的呂后也許只是虐待戚夫人以泄私憤,還沒有打算采用歹毒的手段殘害她。
假若戚夫人有審時度勢的機警,懂得“安莫安于忍辱”的道理,她應該清楚自己和兒子如意的危險處境。她已成呂后刀俎上的魚肉。兒子如意尚未成年,即便有劉邦生前指定的重臣周昌輔佐如意,也不能絕對保證如意的安全。目前呂后還沒有對如意下手,但厄運隨時可能降臨到如意的頭上。面對不可一世的皇太后呂雉,她不能有任何怨言,只能一聲不吭,老老實實地做苦役,俯首帖耳地甘做一個女囚,即便有一死,呂后或許能讓她留得全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保全她的兒子。
遺憾的是,戚夫人沒有繃緊思危的弦,沒有好好思量如何保全自己和兒子,她一邊舂著米,一邊還唱著歌表達她的哀怨:兒子你貴為趙王,母親我卻淪為屈辱的囚犯,沒日沒夜地舂米受苦受難,與死亡相隨相伴。兒啊,你我相隔三千里,我不堪的苦況能有誰去告訴你?
戚夫人不知道,她這一唱,等于給自己和兒子唱來“催命符”。呂后敏感多疑,她從戚夫人的怨歌中聽出了不甘與怨恨,聽出了對自己潛在的威脅:戚氏還指靠著有朝一日她兒子給她撐腰,為她報仇!呂后自然怒不可遏,想當初劉邦在世,戚氏撒嬌獻媚,依仗劉邦的寵愛才敢那么張狂,如今劉邦死了,她的張狂還是不減,她還在做著她的美夢——想靠著她兒子!休想!呂后殺機頓起,為絕后患,她再也不能留著這對母子。
呂后先設法毒殺了趙王如意,然后對戚夫人下了毒手。徹骨的仇恨讓她變成了一個沒有人性的虐殺狂,她將戚夫人害為“人彘”,讓戚夫人喪失作為人的尊嚴,在酷虐中凄慘地死去。呂后害人手段極度殘忍,令人發指,她竟然還召惠帝前來觀看“人彘”,或許是要有意給親生兒子一個嚴正的警醒:宮闈斗爭就是這么殘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決不能手軟!
惠帝目睹戚夫人的慘狀,精神受到巨大刺激,放聲痛哭,為此大病一場。他認為母親喪盡天良,干的不是人干的事!當初母親要殺如意,他設法加以保護,讓如意跟他一同起居飲食,母親一時沒有機會除掉如意。幾個月后,他早晨出去打獵,如意年幼,不能早起跟隨,母親趁機派人毒死如意。想必這個陰影在惠帝心中尚揮之不去,母親又以更兇殘的手段對付戚夫人,讓他這個當兒子的無法實在面對!為“對抗”母親的殘暴,生性仁弱的惠帝索性縱情酒色,不理朝政。
北宋名士司馬光曾經就此事嚴厲批評惠帝“篤于小仁而未知大誼”,指責惠帝“安可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而東漢史學家班固對惠帝深表同情,他稱惠帝為“寬仁之主”,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實在是令人悲慨!
呂后“剛毅”一生,逢怨必報;手握權柄,為所欲為。她親手制造的“人彘之禍”雖報了她對戚夫人的怨仇,卻毀掉了兒子劉盈作為帝王的信心,更是毀掉他人生的希望。身心俱病的劉盈在抑郁沉淪中當了七年掛名的帝王,死時年僅二十三歲。而呂后也讓自己留下“毒婦”的千古惡名。她真的是最后的贏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