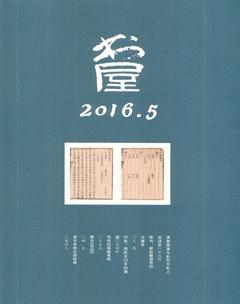中醫、西醫在日本的遭遇
周朝暉
2015年10月5日,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本年度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八十五歲高齡的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在寄生蟲疾病治療研究領域取得的杰出成就。中國生物醫學界首次獲此殊榮,國人無不歡欣鼓舞。12月7日,屠呦呦與同獲該獎的愛爾蘭科學家坎貝爾、日本木村智在德哥爾摩卡羅琳學院出席授獎儀式,三個分別代表中、日和西方醫學界的科學家同時出現在標志世界醫學領域頂峰的舞臺,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畫面,它至少表明:經過幾代人不懈的努力,曾經被誤解、輕視的傳統中醫終于華麗轉身,獲得應有的榮耀與尊嚴。
感動之余,不覺想起近世以來傳統中醫、西醫在日本遭遇的種種糾葛際遇。轉而想到:魯迅先生有知,看了這么一個振奮國人的場面,不知該做如何感想?如此不著調的突兀之念,或許來自重讀太宰治取材于魯迅在仙臺醫專留學經歷的小說《惜別》的感慨吧。
魯迅討厭中醫,個中有他少年時代目睹父親被庸醫所誤人財俱亡的慘痛記憶,乃至成了東渡日本求學奮進的最大動機——“預備畢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太宰治筆下二十二歲的周樹人也這樣想:“現在,我的志向用一句話就能概括:“成為中國的杉田玄白。只有這個,成為中國的杉田玄白,點燃中國維新的烽火。”
成為中國的杉田玄白,點燃中國維新的烽火,這樣的雄心壯志,或許出自太宰治的文學想象。不過,彼時被叫做周樹人君的魯迅對杉田玄白應該是很熟悉的。赴日前在南京讀書,他就知道了日本明治維新發端于西醫的事實;在仙臺醫專,必修課中的日本近代醫學史、解剖史,杉田是繞不過的存在。開學第一課,那個“黑瘦,八字須,戴著眼鏡”的藤野先生,登壇開講之際“挾著一摞大大小小的書”中,就有杉田玄白譯著的《解體新書》和《蘭學事始》,足見他在藤野先生同儕心中的分量。
杉田玄白(1733—1817)被稱為日本近代醫學先驅。微斯人,日本的近代醫學史、科技史乃至開國史也許是另一種故事;而傳統中醫在日本乃至在世界醫林中的境遇,也許是另一種寫法了。
習慣上,日本把源自中國的傳統醫學稱為“漢方醫學”或“東洋醫學”,基本可以看做中醫的一個支流。日本人學習、接受傳統中醫有著相當久遠的歷史。早在公元五世紀,中醫療方就經朝鮮醫師傳入大和朝廷。唐代時日本全面輸入中國文化,中醫也在其中,從中草藥到醫書、臨床、管理等環節全面接受中醫體系,經過吸收內化成日本特色的“漢方醫學”。唐朝末年日本終止遣唐使,但民間層面醫療技術的交流仍然活躍,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物品里中草藥和中醫漢籍占了很大比重。中世紀以前,日本漢方醫學主要被僧院佛門壟斷,不少的來華求法僧人在修習佛法禪理的同時也兼學醫術,有的僧侶如室町幕府時期的月湖和尚,本身就是著名醫者,他們學成歸國促進了中國醫學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到十六世紀,基本上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獨自醫療體系,在江戶中期迎來鼎盛期。但時至十八世紀中后期,一本荷蘭文醫書日譯本的問世,使得這種千年一以貫之的態勢悄悄發生變化。
大航海時代,隨著世界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西方海洋勢力不斷闖入東亞海域。十六世紀中期起,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歐海洋國家的船只源源而入日本。這些國家都取道東亞海域南面的印度洋、南洋而來,日本人按照儒家華夷天下觀,將之歸入“南蠻人”一流。“南蠻人”中傳教士占了很大比重,那些發誓要給遙遠東方帶來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在宣教同時,也帶來了與東亞傳統文明完全不同的代表當時歐洲最新科技成就的知識和學問,如天文、醫學、地理、算數、測繪、航海等近代科技。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初,以葡萄牙為先驅的西方海洋國家的天主教信徒不斷進入日本,他們在九州關西傳教建造“南蠻寺”(基督教堂),作為吸引信眾的手段,傳教士開設醫院治病救人,此為西方醫學在日本的發端。西方傳教勢力的迅速膨脹引起幕府的警覺和不安,多次加以彈壓和取締,終于釀成1637年由大量傳教士和信眾參加的島原之亂,平亂后江戶德川幕府于1639年實行鎖國政策,允許對日貿易的南蠻僅有荷蘭一國,幕府治下的佐賀藩長崎成了鎖國體制下唯一的對外窗口,此后,“南蠻”文化以一種特殊方式經由荷蘭人從這里又開始進入日本,因而被稱為“蘭學”。
荷蘭人重商不言教,并且善于和日本人打交道,尤其熟悉日本禮儀規制,比如他們每當荷蘭商館“甲比丹”(館長)上任,都要隨地方藩主到江戶覲見將軍送禮,深得幕府方面的好感和信任,無形中也成了江戶日本獲取西方情報、技術、文化的一個媒介。
十八世紀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繼位,為了克服嚴重的財政危機,政治家田沼意次推行一系列改革,獎勵實學,對外采取了比較寬松的政策,解禁部分漢譯洋書,不涉“邪教”的洋書都可以在日本流通。為了徹底了解“南蠻學問”的底細,幕府先后派醫官野呂元丈(1693—1761)、儒官青木昆陽(1698—1769)前往長崎學習醫學和荷蘭文,其后兩人分別寫出《荷蘭本草和解》、《荷蘭文字略考》。這兩個有官方背景的學者成了日本“蘭學”的拓荒人,培養出不少熟悉蘭學的“洋才”,其中青木昆陽弟子前野良澤(1723—1803)與杉田玄白合作,翻譯出德國解剖學家約翰·亞當·庫姆斯的《解體新書》荷蘭文譯本,是為蘭學之濫觴,影響所及引起日本知識結構和意識觀念的激烈變革,孕育了近代科技文明的胚胎。
杉田玄白1733年出生于江戶城外牛込町(今東京新宿)一個藩府侍醫世家。父親杉田玄甫是駐江戶城的若狹國小濱藩侍醫。江戶時代,幕府規定:各地藩主必須定期輪流到江戶居住參與協助將軍政務,是為“參勤交代”,核心家臣和武士亦隨同前往。玄白自幼修習家傳醫術,也拜幕府醫官西玄哲學醫,同時隨儒學家宮瀨龍門學漢學,從他的晚年作品來看,他的漢文功底頗深,還會作漢詩,是個有情趣的學者。杉田同時代有個醫師山脅東洋,一次偶然為死刑犯解剖時發現人體實際內臟構造與日本流傳的漢籍醫典出入很大,卻與“南蠻”洋書中人體內臟圖譜如出一轍,經過悉心研究,寫成《蔵書》(“蔵”即“臟”),并根據所見繪成《九蔵圖》對漢方醫學有關內臟理論提出質疑。由于當時漢方醫學高高在上無以撼動的權威性,山脅的學說并沒有引起重視,但卻引起杉田強烈好奇,這也成為促成他日后鼎力譯介蘭學的機緣。
據玄白的回憶錄《蘭學事始》記載:明和八年(1771年),中川淳庵帶著從荷蘭商館借來的荷蘭文醫書《解體新書》拜訪玄白。玄白不識荷文,但書中精密詳盡的解剖圖,完全迥異于見慣了的漢籍醫書粗糙模糊的人體圖畫,令他想起十幾年前讀過的山脅的論斷,十分震驚,千方百計把這本書買到手,悉心揣摩把玩,并想方設法尋求能親臨解剖現場以求驗證書中圖譜的機會。但江戶時代,孔孟朱子之學被奉為至尊,人們遵循儒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的古訓,解剖尸體與毀尸同罪。經過斡旋,機會終于來臨,江戶城郊外小冢原刑場(今東京都荒川區南千住)處決死刑犯,特許他前去察看并解剖,杉田約前野、中川一起見習,他們同時帶去了荷語版《解體新書》和漢方醫術,對照解剖現場所見后大為震撼,比如漢方醫書所載:“肺六葉兩耳,肝左三葉,右三葉”,而實際情性是:人體肺右三葉左二葉;肝右大左小,一如蘭醫所繪分毫不差。于是三人決計一同合作將這本醫書名著翻譯成日文。
在當時條件下,將荷蘭文的醫學書翻譯成日文,難度遠遠超過今天的想象。一者當時蘭學是末流之學,懂的人少,精通荷語且兼通醫術者幾乎沒有,無處求教,就連翻譯必備工具的《日荷字典》之類的輔助書也沒有;三人雖然居于時代蘭學先驅的地位,但水平參差不齊,何況草創之初,蘭學程度稍高者也是二把刀水準,遑論翻譯西方醫學專著,無異于讓剛拿到駕照的菜鳥去參加鐵人越野拉力賽。尤其是杉田玄白,強項在于家傳漢方醫術,論荷文水準則相形見絀。十年前荷蘭商館“甲比丹”到江戶覲見幕府將軍之際,杉田借機與之進行交流,萌生學習荷語之志,但被隨行長崎通辭(翻譯)西善三郎潑了冷水,說荷文難學難于上青天,澆滅他學荷語的熱情。
昭和作家菊池寬曾寫有一篇《蘭學事始》小說,系據玄白同名回憶錄敷衍而成,小說將三人翻譯《解體新書》種種艱辛寫得十分生動,一度是我外語教學中的“勵志”段子:
玄白們動筆不久,馬上就碰壁,原著《五官篇·鼻》中第一句有關鼻子的定義就難倒幾個所謂蘭學家:“鼻者,乃顏面正中vooruitsteekende之器官也”。荷語中“vooruitsteekende”一語啥意思,沒學過,不懂得!又無處可問,翻譯擱淺。后來前野良澤從長崎買回一本簡易荷蘭語會話小冊子,玄白翻來覆去閱讀研究,終于找出其中與vooruitsteekende一詞相關句子,諸如:“樹枝削砍,其創口vooruitsteekende”;還有“清掃庭院塵土樹葉集中vooruitsteekende”,反復揣摩,杉田忽然悟到:位于臉部正中間,不就是像樹枝切口愈后,塵土樹葉堆積后的形態嗎,不就是高高堆起、隆起的部位嗎,于是猜出vooruitsteekende對應日語中的“堆高”、“隆起”的意思。三人會意,不禁手舞足蹈。晚年玄白寫作《蘭學事始》追憶蘭學在日本發端之初的種種不易,感慨萬千,他形容當時翻譯《解體新書》時,戰戰兢兢,如“乘無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無可依托,但覺茫然”,但偶有突破或創意則欣喜欲狂,“心情就像無意得到世間無上的寶物一樣”。這部連圖譜在內不太厚的書,磕磕碰碰前后花了近四年才得以付梓刊行。
《解體新書》的出版,將日本人研究“南蠻學問”熱情推向一個新高度。與其說是技術上或方法論上的,不如說是觀念上的變革,人們才知道:除了傳統熟知的漢方醫學,世界上還有一種似乎更管用的學問,由此引發知識型武士學習荷蘭語,旁及其他領域學問的研究興趣。這本醫學書的翻譯出版,被認為是日本近代科學精神的曙光。在翻譯《解體新書》同時,玄白也寫一些隨筆類文字,以簡明易懂的問答方式闡釋書中精髓,后來匯書刻印成《醫學狂言》。他在推崇蘭醫學明確、科學、可重復、可驗證的優越性同時,對傳統漢方醫學的可靠性提出質疑,指出:盡管中醫經歷悠久時間的考驗,但最致命一點就是缺乏確實可操作性的理論來指導,大而化之,因此就會出現十人十見,不像蘭醫非常精確,百人同癥,療法如一,對癥而治,百人皆愈。玄白的書和言論擊中了“東洋醫學”的某一面軟肋,成了中醫在日本走下坡路的起點。
《蘭學事始》出版時印數不多,后來江戶大火災,雕版和大多數印本都付祝融,世間難見。1868年,靠蘭學起家的福澤諭吉無意中看到這本書的原版手抄本,讀后大受感動:“日本今日之進步并非偶然,百數十年前,已有文明的胚胎。”他感佩百年前翻譯《解體新書》的蘭學家杉田玄白諸人就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培育人。福澤拜訪玄白后裔協商再版,并親掏腰包促成此書復刻版印行。越十年,全日本醫師會成立之際,此書得以再版,從醫者幾乎人手一冊,影響迅速擴大開來,此后一版再版,注家并起,至今超過六種版本。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福澤諭吉“蘭學”恩師緒方洪庵后人緒方富雄校注,出版于1941年的現代語譯本,此版后來收入巖波書店文庫本廣為發行,至今是最權威版本。
西洋醫學在明治維新前后匯成一股時代潮流,與此相反,漢方醫學卻相形見絀,在日本的命運急轉直下,一度跌入千年未有之窘境。
西醫逆襲東洋醫學,在日本獲得壓倒性的優勢,從旁流躍居主流,乃是拜國內戰爭之所賜。1867年江戶無血開城,末代將軍德川慶喜把大政奉還天皇,但不愿歸順的東北諸藩爆發了對抗新政府的戊辰戰爭。戰事非常慘烈,與傳統冷兵器時代的打打殺殺不同,彼時雙方攻伐已經普遍使用殺傷力極大的槍、炮等現代熱兵器,傷亡很大,特別是由于槍創彈片導致大量出血、感染破傷風而死的人數量居多,對此,隨軍漢方醫生卻是束手無策。政府軍首腦西鄉隆盛從英國使館招聘西醫隨軍出征,派上大用場。英國醫師及助手為傷員做手術時,采用當時日本尚未掌握的傷口消毒、用全身麻醉切開縫合傷口和截肢手術,挽救了大量傷員,不但大大降低了戰事傷亡率,而輕傷者亦能很快復原,重新成為戰力。軍事活動中,西醫在外科手術與臨床診療的神奇功效,使新政府軍高層深受震動,內戰結束后,引進學習西方軍醫制度和改革傳統醫療體制成了明治政府一大急務。
1868年12月,根據天皇的旨意,明治政府將國民的健康和衛生防疫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加以督導,出臺《太政官布告》,宣布全面改革醫療制度,有曰:“醫師之義,關系人之性命,實非容易之職也。然于近世,不學無術之徒,猥弄方藥,誤人性命者不在少數,又背圣朝仁慈之旨趣,以此甚不相濟也。今般設醫學所,立規則,學之成否,術之巧拙,均以考試驗效,無有執照者,不得從事醫業。”
布告中明確國家對醫療的掌控,還規定今后在日本行醫謀生,必須通過國家醫學考核才能獲得執照。十年之后,全國通過考核獲得西醫執照的已經達到一千八百多人。明治政府雖沒有明確禁止漢方醫學,但卻施以封殺生存空間的政策導向令其自行式微:開業醫師資格考試科目全是西醫內容;漢方藥館被廢止,禁止漢方醫藥自由買賣,嚴格控制中藥“處方權”,中藥處方須得有西醫執照業者才可以開。針對當時漢方醫生占絕大多數,西醫人才稀缺的情況,明治政府采用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方式,積極培養本土西醫人才。
由于德國醫學經由江戶時代蘭學家之手傳播到日本,以及對日本成功向近代化國家轉型的啟蒙之功,成了明治政府高層心儀的楷模,于是將學習德國醫學技術和體制列入建立國家醫療衛生保障體系之中。明治元年,佐賀藩長崎蘭醫出身的相良安知被任命為“醫學校兼醫院”(東京大學前身)大學權大丞,主管政府醫療事業。在同樣是佐賀藩出身的明治權臣大偎重信、副島種臣支持下,日本全面引入德國醫學體制,聘用德國醫師傳教,同時官派大量青年才俊赴德國學醫,比如出身島根藩醫世家的明治時代著名文豪森鷗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肩負家國重托公費去德國學醫,學成歸來,官至陸軍醫院總監。明治政府的“醫制”改革不久就大見成效,到十九世紀末期本土西醫人才大量涌現,諸如連魯迅所在的日本偏遠地區的仙臺醫專,盡是西醫出身的教授、博士和教師,反過來成為日本曾經事師一千多年的中國人的學習對象了。
西醫代表先進、文明,代表主流,而一度造福東亞乃至為世界醫藥事業做出過貢獻的漢方中醫學成了落后、保守、愚昧的代名詞遭到妖魔化,這正是魯迅留學仙臺醫專的時代風氣。但仙臺醫專的留學經歷卻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當初為救死扶傷而立志學醫,但以“幻燈事件”為契機,激憤的周樹人君覺悟到學醫并非一件緊要事,更急迫的是改造國民的精神,于是棄醫從文,走上文化、思想啟蒙之路。
令人感慨的是:早于魯迅留學日本一個世紀,幾乎與杉田玄白生活年代同時期,在中國也曾出現過類似的近代醫學先驅。但很可惜,這個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名叫王清任的鄉下醫師所點燃的科學火苗,并沒有形成燎原之勢,冒了一陣煙,最終復歸于沉寂了。
王清任(1768—1831)是河北玉田人,自幼對中醫學情有獨鐘,廢寢忘食加以研究,不到而立已經將多種醫學典籍爛熟于心。他原是玉田縣武舉,家里捐錢為他得到一個類似地方武裝部主管的職位。但王清任志在岐黃之學,后辭職以行醫立世謀生。在鉆研和行醫實踐過程中,他發現《靈樞》、《素問》(《黃帝內經》)等傳統醫學有關內臟的描述存在很大問題。
有一年,河北灤州地區瘟疫流行,幼童死亡甚多,尸體在荒郊遭野狗刨出撕咬,內臟暴露,王清任行醫中得以察看兒尸臟腑血脈,由于數量龐大,記錄下的案例有三百多個。為了證實自己“成人內臟不出其外”的判斷,他設法進入刑場,觀察刑尸或參與解剖。在大量實地觀察的基礎上,他發現被后世服膺遵守了數千年的醫典存在致命的問題,比如《靈樞》雖然最早提出“解剖”一詞,但有關人體臟腑之說,與實際解剖所示存在嚴重偏差。許多醫書對臟腑功能的解釋都不正確,是造成病理不明、藥力不效的根源:“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子夜行!”積四十年實地解剖所見,他繪制成了大量的人體臟腑草圖,于1830年刊刻《醫林改錯》和《親見改正臟腑圖》,從臨床實踐糾偏傳統醫學經典的錯誤和紕漏。
王清任著作中閃耀的科學智慧之光曾引起西方相關人士的關注,十九世紀末曾有駐華英國醫生把《醫林改錯》部分章節英譯,陸續發表在不列顛權威醫學期刊《博醫匯報》上,獲得西方醫學界驚嘆。但在近代中國醫學史上,王清任的影響也就到此為止,他終于沒能像杉田玄白那樣為中國開啟一個近代醫學新時代,遑論為后世引領出變革與維新了。據研究,《醫林改錯》在當時受到冷遇甚至被當作異端,遭到不遺余力的抵制和圍攻,王清任晚景凄清,在無限抱恨中郁郁而終。
歷史上中醫的幾度興衰,每每與時代動向和社會意識密切相關。從王清任與杉田玄白截然不同的命運,不難看出作為國粹的中醫,恰如其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一樣,是遭遇西學東漸這一“千古未有之變局”過程中尷尬處境的一個寫照:先是故步自封,而后面臨強勢挑戰時捉襟見肘最終自我懷疑和否定,乃至“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潑掉”,過猶不及,一度被廢棄得比日本還徹底,境遇至今很難說有本質上的改變。
回過頭再來看當今日本醫學界,西醫依然居于主流地位,但對于一度被棄如草履的漢方醫學的認識卻發生很大改觀。1972年中日建交,也正是在這一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家東洋醫學研究所。1976年一些漢方中藥開始獲準用于醫療保健,中藥重新當作醫院處方。十年前開始,漢方醫學在日本迎來了復興。不必看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漢方藥店,從讀書出版業來看,近年來推崇中醫理療優越性的圖書每每成為暢銷書,動輒幾十萬上百萬本,“漢方藥”重新成為生活熱詞。復興的原因諸多,首先是西醫本身的局限性問題,如臨床分科過細,化療電療帶來的嚴重副作用,以檢查化驗為中心的理療無視患者的訴說,還有西醫對癌癥等重癥的無能為力,使得長久形成的西醫信仰開始動搖。2005年以來,戰后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開始進入退休,高齡化人口達到高峰值,關注健康長壽成為一大社會潮流,在此背景下,凝聚幾千年養生之道傳統智慧和實踐經驗的中醫重放光輝。中醫、西醫各有側重,并非孰優孰劣的問題,取長補短,或能造就無限可能性。就像屠呦呦所說:中醫西醫各有所長,兩者有機結合,優勢互補,具有更大開發潛力和發展前景。
偉人曾預言:“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寶庫。”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醫學,這一有著數千年悠久歷史和智慧積淀的傳統文化,曾經為人類的健康貢獻至大。古代醫籍關于青蒿水漬榨汁的記載啟發屠呦呦的靈感,經過她及其團隊數十年刻苦攻關,成功打開青蒿素研發之門,挽救上百萬人類生命,這是“傳統中醫給世界的又一禮物”。屠呦呦同時開啟的還有中醫國際化大門,她的獲獎,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出世界醫學權威體系對傳統中醫文化所寄予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