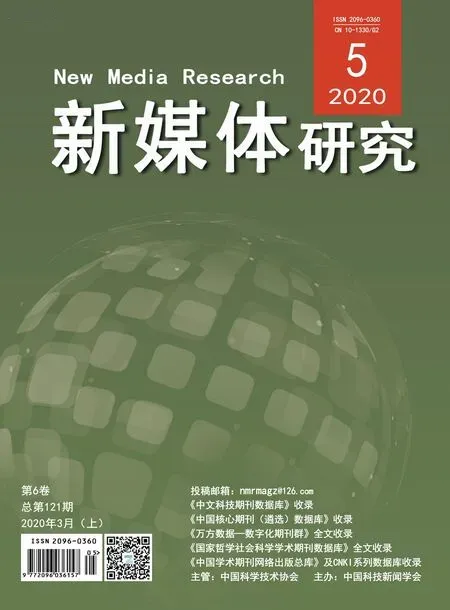丑聞爆料群體性特質研究
賈文思
摘 要 我們生活在一個丑聞爆料現象蓬勃盛行的時代,每天都會接觸到大量形形色色的丑聞信息,然而由于對丑聞爆料群體的定位缺乏客觀清晰的理性認識,使人們仍處于相當模糊、含混的狀態,無法對周遭的丑聞事件與人物做出正確的判斷。在學術界尚無對丑聞爆料現象本身完整、系統、權威界定,文章嘗試對丑聞爆料的特殊承載者及其傳播特質展開研究。
關鍵詞 丑聞;爆料;群體性;特質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6)05-0008-03
“丑聞”這一專屬名詞在我國出現的時間偏晚,后期又受到意識形態、傳統偏見等慣性思維強大勢力的影響而被劃歸到絕對貶義詞匯中,丑聞爆料,多指涉演藝界、文藝圈的明星艷聞、桃色新聞或性丑聞等。在中國人的詞典里,似乎并不習慣將其與嚴肅的、嚴謹的批評類和輿論監督類負面新聞報道相關聯。一般認為,負面報道的內容包括戰爭、疾病、災難、沖突、動亂、腐敗、犯罪、暴力、屠殺等多種題材,這些內容首先能夠滿足普通受眾趣味性的需要,同時,對腐敗、獨裁和專制的揭露,也是出于重要性、接近性的新聞價值標準的考慮。
曾幾何時,我國傳統媒體對丑聞二字諱莫如深,除了報紙的娛樂版、八卦周刊,其他的嚴肅場合中均不敢明目張膽的使用“丑聞”二字。揭瘡疤不是為了展現傷疤而是為了治療傷疤,面對負面新聞,媒體束手束腳、慎之又慎,生怕觸及社會某些方面的痛覺神經。寥寥幾篇不痛不癢的揭丑報道,也幾乎無法引起受眾的強烈呼應,與酣暢淋漓的揭破政治腐敗和社會弊病毒瘤的“掏糞運動”時代相比,我們的批評與監督有些隔靴搔癢的意味。丑聞爆料人的出現可謂打破沉寂,丑聞拼接了世界的不完美,伴隨微博反腐和民主政治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其不可阻擋之勢也將我們的目光久久聚焦在這一特殊群體身上,當今時代能否成為一個新的掏糞者時代?
1 丑聞爆料的特殊承載者及類型
將丑聞這一概念分解開來看,首先“丑”是作為限定性形容詞的定語成分出現的范疇,關于其確切含義的認知一直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也可以說,丑聞觀念伴隨傳播學領域歷史的推進也在潛移默化中不間斷的更新和修繕:在衛宣公、齊襄公、陳靈公時代,私通與亂倫,被無條件的視為“丑”,王族貴胄的荒淫無恥顯得尤為可鄙;在20世紀的西方國家,不道德的商業競爭或交易以及腐敗的政府行為被稱之為“丑”,他們或違背道德,或觸犯法律,往往與社會廣大民眾的利益構成尖銳的對立;時至今日,“丑”又被賦予了更多、更新的時代內涵。從這一丑聞觀的一般性差別來看,中國人對丑的概念描述更多停留在倫理道德批判的形而上學的虛境。
同為揭丑,從新聞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丑聞爆料人”的出現似乎順理成章,而對這一特殊群體的定位卻并不明晰,始終在線人和職業記者的身份間徘徊游移。首先,爆料人身份有別于普通受眾。在新聞傳播鏈條的各個環節中,爆料人屬于新聞源的范疇,從傳統意義上說,他們只是新聞線索的提供者,俗稱“線人”。新聞源有主動、被動之別,而丑聞爆料人大多屬于主動新聞源,出于個人動機或其他不明動機,借助微博等新媒體播報平臺,對某些事件內幕或名人秘聞(一般為負面消息)主動予以曝光。其次,爆料人身份亦有別于職業記者,他們只是新聞素材的提供者而非新聞報道的生產加工者。從其群體特征來看,作為傳播主體,丑聞爆料人具有身份的模糊性、動機的隱匿性、立場的單向度性、傳播的非正式性等特征。從具體分類來看,丑聞爆料人大致可以分為資深記者型(非職業)、意見領袖型、高知學者型、普通公眾型等類別。
2 丑聞爆料群體性特質
丑聞爆料群體作為傳播主體中的特殊類別,其具備了一般新聞所共有的傳播屬性,除此之外,還擁有其獨具的傳播特質。
1)人情味與人群性。
人的因素幾乎是丑聞賴以生存的基礎。離開了人性化的理解和帶有人情味的審讀,丑聞幾乎成了一名不文的垃圾。丑聞傳播的某些信息內容可以引起受眾的強烈的情緒反映,如憤怒、激憤、恐懼、同情、愛慕、厭惡等,或許傳播者在傳播信息時已經滲入了自己的情感,而這些情感某種程度上也會引起受眾的共鳴,這種情緒的宣泄與傳遞,構成了丑聞傳播的趣味性和人情味的來源。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情性可以看作是丑聞對于人性的展現、挖掘和捕捉,這種展現、挖掘和捕捉能夠最大限度地體現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人類獨特的情感特征。審讀行為雖然是群體化的,而審判結果卻又會因人而異、迥乎不同,這便是人情味個性化特征的充分體現。因此,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即便是最無恥、最令人生厭的丑聞主角,在人群中亦不乏其同情者。
2)傳播范圍廣,持續時間長,關注度較高。
中國有句俗話,叫作“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用來形容丑聞爆料的滲透力和推廣速度似乎再貼切不過了。無論是對大眾傳媒或是人際傳播而言,壞事與丑行,似乎總是要比好事傳播的更快、更廣,也表現得更有力量一些。
爆料者對丑聞始終保持著窮追猛打、鍥而不舍的認真態度,事件于是得以升級或持續升溫,加之連篇累牘的系列、追蹤報道,丑聞報道持續的時間往往相對較長。一件丑聞案從發生到爆光,媒體由始至終掌控著報道的節奏。何時初露鋒芒,何時欲說還休……無論事實的真相如何,先想方設法炮制成長篇連載或“連續劇”。即便毫無線索者也絕對不甘寂寞,紛紛轉載別家消息并適當添油加醋以等候時機。一旦洞悉內幕或進一步獲取獨家猛料,再跳出來風光一翻。
丑聞爆料過程中最吸引人的地方通常是人——演藝圈的明星大腕兒、知名人物、王室成員、學者政客等社會名流,平素我們只能通過媒體去了解他們,可能出于好奇、嫉妒、羨慕、崇拜、討厭或喜愛而關注他們;而通過他們,我們則體驗著另一種生活,又或者他們的行為和決定會影響以及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些丑聞的點擊率高達百萬次,乃至上千萬次,互聯網使丑聞傳播的速度更快,范圍更廣,獲知性更強了,網絡新媒體的巨大優勢使丑聞主角擁有了一夜走紅的資本與可能性。
3)異常性與“記異心理”。
“迄今已做的心理學實驗顯示,人們更傾向于更多地注意負面的東西,并且對此類東西的記憶也更長久些。”①帕梅拉·休梅克教授的這一命題在普利策評獎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壞消息一般是異常性的新聞,因此反過來通常意義認為的異常性也都是消極的,新聞報道實踐中,異常性似乎也總是與形形色色的丑聞現象相生相伴,而異常的事物又往往比常規的事物需要更多的認知過程。異常性是一種對新聞報道內容所具有的罕見性或陌生感的度量。異常性顯著的丑聞一般是關于“明顯偏離常規和日常經驗的事件”的報道。關于異常性的著名經典注解是約翰·伯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聞,因為這樣的事發生的太多了,但如果人咬狗,那就是新聞了。”
事實上,人們關注異常的人物、事件和觀念,這個傾向并不是新有的,求異,自古便是人類的好奇心理之一,是有機體遇到奇異刺激物或新鮮事時會產生的朝向和探求反射。好奇心理是一種直接的興趣,它不需引導即可產生的一種關注與感興趣的心理指向,這便被稱為“求異心理”或者叫做“記異心理”,它不是出于得益的動機,而是一種無專門目的的、感受上的愉悅與滿足。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記者的求異行動或是受眾的“記異心理”,都源于人類最古老的本能心理訴求。
從探索的角度來看,人們要想對世界有更深刻的把握和更全新的探索,就必須對奇異的事物保持長久的興趣。正如密蘇里新聞學院寫作小組所論述的那樣:“任何異常事物也都是日常生活,奇異的人和事是生活的一部分。”從信息傳播和接受的角度來看,人們容易對有陌生感的事件充滿好奇,并產生閱讀興趣。
試想,如果我們在媒介中所得到的東西比日常生活更平淡無奇,還需要媒介和新聞信息干什
么呢?
4)沖突性與沖擊力。
有價值,但很乏味。這應該是給新聞報道的一句最糟糕的評價了。新聞本應該是那種能夠使你倒吸一口涼氣,然后驚叫著坐起來,全神貫注認真傾聽的東西。這一部分要談到的是沖突性,它“是對新聞題材及文本所展現的矛盾或戲劇感的強度的度量”②。而丑聞偏偏又是所有新聞形態之中,沖突最激烈、最集中、最不易調和的一種,這一點從丑聞構成的基本要素就可得到有力的證明:丑聞角色的對立雙方相持不下,率先構成一對牢不可破的矛盾沖突雙方;而媒介報道者與丑聞主人公之間也存在一種對丑聞或揭破、或固守的尖銳對立關系;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丑聞的受眾與丑聞事件或人物本身也構成一對基本矛盾沖突。因為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丑聞的出現或存在往往與受眾預接受的基本層面形成對立,這種基本層面,或是傳統道德,或是倫理觀念,或是預存立場,或是價值判斷,有時甚至是根本利益的矛盾,這便形成了丑聞故事中的組織之間、個體之間及人與環境之間因互相矛盾或對抗而構成的某種新聞敘述上的本初張力。正是這種沖突性與對抗性的存在,才對丑聞存在形成有力的支撐。
這種沖突沖擊著人們的傳統意識與價值觀,從而形成道德、人情、法理、觀念上的接受逆差。有些沖擊力甚至還可能向受眾發出某種警告,使人們關注危險的迫近、困難的出現。另一方面,丑聞的存在形式往往是戲劇化的描繪矛盾被解決的過程,并為之提供了一種可觀賞性,促使受眾的閱讀興趣始終得以保持,并不斷升溫,最終達到沸點。于是,丑聞所帶來的無處不在的沖突性與無所不能的沖擊力,給報道本身以巨大的題材支撐,受眾因而習慣了沖突性的新聞價值觀,并就此養成了對丑聞成癮性閱讀的主要趣味之一。
3 結論
筆者嘗試以全新的學術視野聚焦于“丑聞爆料人”這一當下廣受關注的特定群體,針對形形色色的爆料行為展開系統分析,從理論視角來看,丑聞爆料相關研究對新媒體環境之下的傳播原理的更新是不可或缺的系統補丁。
丑聞爆料人作為新型傳播行為主體,是傳播鏈條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其出現對傳統議程設置理論提出挑戰。從實踐角度來看,政治方面,如以大數據時代的民間反腐之聲為研究背景,進而對于推進網絡政治民主化進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媒體從業方面,丑聞爆料人的職業化傾向對傳統的新聞內容把關與篩選等傳播實務理論產生不可預知的影響;文化生活層面,泛娛樂化時代,職業化丑聞爆料人的出現將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對名人明星丑聞的新聞消費行為。
注釋
①張詠華.新聞是異常的——帕梅拉·休梅克教授訪談錄.新聞與傳播,2004(6).
②陳衛星.網絡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第
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