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濟蒼生
賀雅文 陳達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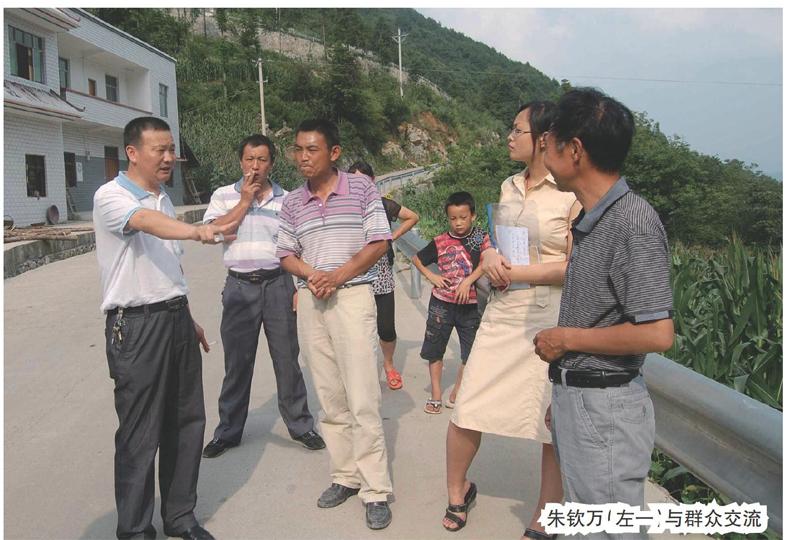

2015年12月10日,巫山縣騾坪鎮仙峰村。
這天一早,貧困戶袁洪平就來到村便民服務中心。
一大群村民已經到了。
他們笑著嚷著,把村黨支部書記助理胡祖定圍在中間。
袁洪平定睛一看,全是村里的貧困戶。
“胡助理,幫我填一下貧困戶脫貧驗收表。”有人叫喊。
“也幫我填一下!”袁洪平趕緊擠上前去。
“莫慌,一個一個來!”胡祖定大聲招呼。
良久,終于輪到袁洪平了。
胡祖定捏著驗收表,逐項詢問。有住房、有路行、有水喝、有學上、有醫療……得到答復后,他在各欄逐項打上評分。
“洪平,你91分,脫貧了喲!”胡祖定笑著祝賀。
“有朱主任相助,還能不脫貧!”袁洪平瞇眼揚頭,豎起大拇指做了一個“贊”。
一天前,這位被點贊的“朱主任”才跟袁洪平見過面。
一個“燙手山芋”,他不僅敢接,還緊緊捧在心間
12月9日,仙峰村。
一片長勢喜人的蘿卜田里,袁洪平正低頭刨大頭蘿卜。
身旁一聲吆喝忽起:“洪平,今年蘿卜長得不錯喲!”
袁洪平一抬頭,看見一個中年男人正往田里鉆。
那人約莫五十歲,花白頭發剃成了板寸,中等身材,肌肉結實,被太陽曬得黝黑的面龐飄滿“紅云”,看著就像個農民。
他就是巫山縣扶貧辦主任朱欽萬。
“朱主任,又來扶貧了?”袁洪平伸直腰桿,抹了把汗,“托朱主任的福,今年我憑2畝大頭蘿卜和5頭豬,脫貧有望了。”
“收了蘿卜,趕緊賣到楚陽紅農業公司,等著收錢。”朱主任熟練地撥拉開蘿卜葉,走到近前。
“從種田養豬到招商做買賣,朱主任,你真是全才!”袁洪平樂呵呵地夸贊。
袁洪平說的還真不是恭維話。
在巫山乃至全市扶貧戰線,朱欽萬的確堪稱“全才”。從事扶貧工作8年,他和同事們已幫助約11萬群眾脫貧。
他總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協助縣委、縣政府完成了全市首個整鄉生態扶貧搬遷項目。
他率領團隊銳意創新,為貧困山鄉催生了上百個致富項目。
名氣大了,朱欽萬也開始面對一個問題:“巫山地處秦巴山區,山高坡陡,耕地零散,貧困農村面積大,扶貧脫困門檻高。別人都怕這個‘燙手山芋,為何你卻能干得風生水起?你有什么竅門?”
“竅門沒有,就是要懂得‘三個一。”朱欽萬說,“干扶貧工作,必須要有一股牛勁,一雙慧眼,一顆善心,才能做出成績。”
一股牛勁,令他踏遍青山,開辟出條條致富大道
認識朱欽萬的干部群眾都說,朱主任身上有股子牛勁。
對朱欽萬的牛勁,原廟堂鄉搬遷戶袁孝英深有體會。
那是2008年的一天。
天剛亮,袁孝英打開家門,便看到門外站著一個男人。
此人中等身材,花白頭發剃成了板寸,黝黑的臉上堆滿“紅云”。
這不是被她和丈夫攆走的扶貧干部嗎?
深處大山腹地的廟堂鄉環境惡劣,生態脆弱,傳統扶貧戰術不能奏效。怎么辦?
這時,剛剛就任縣扶貧辦主任的朱欽萬帶人經過仔細調研,提出了“以退為進”的新戰術——通過整鄉扶貧搬遷,引導鄉親們到交通、產業和生態等基礎條件更好的新家園生活。
在縣委、縣政府支持下,整鄉搬遷很快啟動。
消息一出,當地村民立即分成了兩派。99%的村民表示“愿意搬”,而一些上了年紀的村民卻表示“故土難離”,說啥也不搬。
袁孝英和丈夫曹學弟就屬于后者。
一天前,朱欽萬和同事來到袁孝英家,動員他們參與搬遷。
面對干部的苦苦相勸,袁孝英和丈夫毫不領情。
“在山上住了大半輩子了,不走!”二老吆喝著,將來人攆出了門。
碰了釘子,朱欽萬卻不氣餒,索性就在袁孝英家門外守了一夜。
當袁孝英看到在寒風中守了一夜的朱欽萬時,心理防線瞬間松動。
老人終于讓朱欽萬進了門。
進門坐下,盡管身子還有些發抖,朱欽萬仍舊立即當起了“說客”:“您二老孩子不幸早逝,全部希望都放在了孫子身上。搬出大山,孫子就能獲得更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何樂而不為?再說了,搬出山后,你們也可以更好地安度晚年……”
“軟磨硬泡”下,老兩口終于點了頭。
兩個月里,朱欽萬等27名干部天天進村入戶探虛實、作動員,磨破嘴皮子,踏破鞋底子,最終順利完成了全市首個整鄉扶貧搬遷工程。
憑著這股牛勁,朱欽萬和同事們8年來相繼引導6萬鄉親參與生態扶貧搬遷,幫助69個貧困村整村脫貧。
一雙慧眼,讓他善抓機遇,變不可能為可能
2015夏天,巫山縣建平鄉春曉村。
殷勤招呼著如織游客,望天坪度假村農家樂業主吳寶清雙眼笑得瞇成了一條縫。
“自從朱主任把我們村打造成休閑農業度假區,日子就好起來了。去年,我們一家的收入有30多萬元!”吳寶清說。
春曉村和縣城隔江相望。因為區位閉塞,山高坡陡,飲水困難,這里曾經是一個市級貧困村。
貧困,逼著年輕人競相外出務工,剩下老人和孩子困守山村。
直到2013年,朱欽萬受縣委、縣政府之命前來調研。
“以前,扶貧就是‘授人以魚——給錢救濟,結果老百姓領到錢就花了,當地貧困局面卻毫無改變。因此,我就琢磨,要解決貧困問題,既要‘授人以魚,更要‘授人以漁。”朱欽萬說。
如何“授人以漁”?
“你得有一雙慧眼,才能從當地資源中發現潛在的致富門路。”朱欽萬說。
為尋找致富門路,朱欽萬天天往村里鉆。有一些日子,他來到貧困戶吳寶清家“借宿”。
白天,他和吳寶清一起爬山下田,琢磨當地能發展什么產業;夜里,他倆同塌而眠,暢談脫貧致富的各種可能。
閑談間,吳寶清說到了一件事。
因植被茂盛,海拔又高,望天坪的自然美景常常引來城里人觀景拍照。
有一次,一個驢友到山上拍了照片,腹中饑餓,就想尋一個農家樂吃飯。
卻不想,苦尋無果,他只好來到吳寶清家,想“搭個伙”。
樸實的吳寶清立即拿出最好的洋芋米面款待他。
那驢友吃飽喝足后,臨行前塞給吳寶清15元錢。
聽了吳寶清的講述,朱欽萬一拍腦門,大喝一聲:“有了!”
他立馬趕回扶貧辦,提出了“春曉村脫貧作戰計劃”——打造休閑農業度假區。
計劃雖誘人,卻沒人敢出來承攬。
關鍵時刻,朱欽萬又站了出來,代表村民和相關企業接洽,引來了投資,又組織村民成立農家樂行業協會,依托度假區打造農家樂配套體系。
一年下來,望天坪度假區初見雛形,游客紛至沓來,村民收獲了第一桶金。
8年來,朱欽萬憑借一雙慧眼,將產業扶貧經驗從“點”推廣到“面”,探索出“1+3+新興產業”的縣域扶貧特色產業模式。
所謂“1+3”,就是按高、中、低山區域布局,大力發展以山羊、脆李、中藥材和烤煙為主的“1+3”特色經濟,確保貧困村有2—3個特色主導產業,每個貧困戶培育1—2個增收產業。
所謂“新興產業”,就是發展以光伏發電、鄉村旅游、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規劃一個、打造一個、見效一個。
8年間,“1+3+新興產業”模式已幫助約11萬貧困群眾圓了致富夢。
一顆善心,使他情系百姓,為貧困群眾解急救難
2012年夏天,朱欽萬接到一個告急電話。
電話那頭,平河鄉陶灣村一位姓陶的農戶言語急切:“朱主任,我們村吃水問題沒解決,扶貧辦能不能出手幫一把?”
放下電話,朱欽萬眉頭皺成了一團。
“朱主任心軟了。”有同事“預言”。
果然,接下來一些日子,朱欽萬親自跑到陶灣村調研,發現當地連水源都成問題。
朱欽萬趕緊召集鄉親,連開三場村民大會,商討對策。
其間,有村民提議:相鄰的竹賢鄉石溝村水源豐沛,不如從那里引水。
然而,石溝村和陶灣村相距20余公里,從石溝村引水成本太高。
看到村民失望的表情,朱欽萬心軟了。
他不辭辛勞,積極協調相關部門籌集到約60萬元資金,又帶著技術人員登臨巖壁,勘察蓄水池和自來水管道的架設位置。
三個月后,陶灣村引水工程勝利竣工。
當清涼的自來水從水管里噴涌而出時,引來村民一片喝彩,還有不少人喜極而泣。
有熟悉朱欽萬的干部說,他這個扶貧辦主任什么都管——哪個村沒水吃了,他要管;哪個鄉沒有橋過河,他要管;哪個村小上課沒桌椅板凳了,他也要管。
“連過河、吃水、上學都成問題,還談什么脫貧致富!”對此,朱欽萬一點不含糊。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為了管好這些事,朱欽萬付出了怎樣的努力。
“在我的記憶里,只要朱主任沒出差,每天他都是最早到辦公室的。”朱欽萬的同事陶博說,“辦公室早晨的第一盞燈是朱欽萬點亮的,而這盞燈通常也是最晚才熄滅的。”
還有人算過一筆賬——8年間,朱欽萬三天兩頭往村里跑,以平均每次往返20公里計算,他至少已奔波了上萬公里。
因其在扶貧工作中的突出表現,朱欽萬被評為全市唯一一個“全國社會扶貧先進個人”;而在全市扶貧工作考核中,巫山縣扶貧辦也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