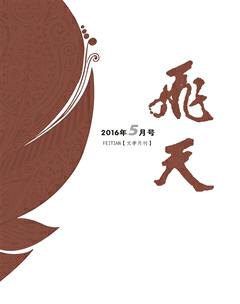“夾縫里”的存在之詩
橫豎三一寧
一
《夾縫里的陽光》是詩人王立世很有分量的一部詩集,品讀這部詩集,我們不能繞開他的代表性作品《夾縫》。全詩無一悲字,讀后卻倍感蒼涼。詩中美好的花、草、鳥、陽光都失去了往日的美好,給人沉重寂寥之痛感。“夾縫”,是他對自身生存語境的一種認知與確認;而所謂“陽光”,也只是詩人對藝術與自我確認過程中留下來的隱喻與象征之物。
二
真正的詩人都具有特立獨行的品質,一生都在苦苦尋找靈魂的家園,而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又形成了令人壓抑的“夾縫”。王立世有一首詩《這些年》,是詩人對世界與自身存在認知的有力佐證。當這個“朋友只剩下幾個”的世界一再現形,當“鬼鬼祟祟的市儈”的出沒成為常態,詩人關于“命運的安排”,其實更多的是被動和無奈。也許的確如詩人所說“時光會擦掉一切”;可是“那些最突出的部分”依然在,依然很突出。
三
瑪拉美說:貧窮,但是聽到風聲也是好的。王立世在他的《留在此岸》的“此岸”里,以自己的“風聲”,告破于自我的“碼頭”。不過,中國詩人的“聲”,更得益于“隱士一樣”的傳統文化與內心生活,但不管怎么說,詩意的生活,正是理想的生活之一,而要擁有“二畝薄田”的桃源式生活,必須拋棄很多“掉進漩渦的危險”,或者說,必須剔除那種與藝術絲毫無補的危險性可能。
四
王立世的語言,更多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部分。換句話說,王立世更多地是站在中國的大地上,更多地以中國文化為寫作背景,并一次次去完成詩的。他詩中的意象,從不復雜,也不疊加,而是以單純的一個面孔出現。單純,是好的,好在不是單薄,好在這種單純的“具象寫作”,更易為人所接受和理解。
王立世以自己的語言方式,行走在這個世界上。滄桑世故,風云變幻,都在他的詩里得到比較恰當的呈現與表述。也許,寫作方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效的表達。什么是有效?有效,就是一個詩人——在時間里,對自我與世界關系的藝術把握;而這種寫作,肯定會透露出更多批判主義的思想意識。王立世的詩里,就不時地傳達出這種意念,這也是可圈可點的良好部分。
五
實際上,王立世的很多詩都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思想與意識。他的《胡子》固然很短,卻通過對胡子的長與短,對人間某種虛偽的世態進行了藝術性的撻伐,可謂入木三分。還有他的《人獸》《傷口》《發現》等詩,尤其《發現》一詩,當“我”發現“焦慮像一群滾動的石頭”,正是人徹底撕掉偽裝的時候。這首詩極具自嘲的性質,詩中的“我”既是一個個體,同時又是一個集體的代稱;風雨中的臉,既是自我的又是很多人的;而“偽裝”,必是詩人徹底撕開世界的偽裝。這首詩無不透露著人類生存的極大的無奈性,正如詩人所說:“多年來,我只顧埋頭趕路/沒顧上看一看沿途的路標/有一天,突然發現/離我想去的地方越來越遠”。為什么“越來越遠”?皆是由于“夾縫”的存在,皆因生存的夾縫感為人類帶來致命的擠兌所致。而詩人的存活,更是“夾縫”導致的囚徒的命運。
六
詩人,都是活在一個尋找本真自我的過程。王立世也不例外,他的詩《今天》對自我進行了義無反顧的理想表達——“尋找那顆遺失多年的心”。應該說,這種“心”的存在以及詩人所追尋的理想之境,均有一個難以繞開的前提,那就是諸多紅塵里太多的、過于龐雜的“鳥事”的“草叢”。詩人,以一種晴空式的心態來面對“今天”的現實與生活;如果不這樣,也就不是詩人了。正是還有一顆純真之心的存在,所以詩人就具有了“撥開草叢”的力量與靈魂。
七
詩人在這個時代是被擠兌的人種。王立世也不能逃開這種命運,至少詩人的詩幾乎完全在裸露這種醒世的覺悟,至少詩人在這個麻木不仁的世界,敢于以正義的眼光來洞穿眾生相的糟糕部分。什么是詩人的存在,什么又是詩人的作為,至少一個詩人不能少去一雙銳眼。詩人既是一個銳利的洞察者,又是一個勇敢的思想者。即使詩人仍處于夾縫當中,仍屬于世界的弱者,依然在渴望陽光,在思考陽光。王立世的這一類詩,基本上是以口語的形式,在直抒胸臆的基礎上完全占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地。他的詩,一直處于“好懂”的狀態里,也許這正是詩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