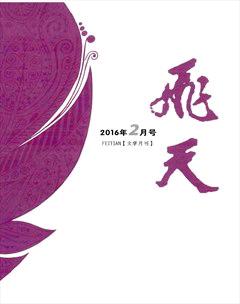零虛構

周瑄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人丁》《夏日殘夢》《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愛情》《多灣》,中篇小說集《曼琴的四月》《驪歌》。在文學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說近百萬字,多篇小說被轉載和收入各類年度選本、進入年度小說排行榜。現居西安。
一
原以為大半夜的,街上一定是人跡全無,只有我們一家出沒,哪知道還是車來車往,行人走動。城市繼續喧囂,只是壓低了聲音,燈光接替陽光,孜孜不倦地照射。女兒或許以為這是一場夢,她懷著無辜的心情,沒有聲息地坐在后面。我甚至不敢回頭看,害怕見不到人,只有一堆糖稀順著座位往下流淌。
夜里一點半,丈夫推醒我,問女兒還燒不燒。我起身摸她身上,天哪,還是燙手!兩小時前,抱著僥幸心理叫她吃了藥睡下,想著明早起來就會好的。
看來扛不到天亮了,趕快上醫院吧。丈夫下樓開車,我叫女兒起床,換衣,收拾東西,拿上醫保卡、水杯、毛巾等,下樓坐上車。去哪個醫院呢?我說,去最近的唄。
夜市上燈光明亮,男男女女在開心吃喝、大聲說話,桌上空啤酒瓶林立,腳底下一片狼藉,他們就像坐在廢墟之上。
因為修地鐵,醫院所在十字路口堵成了迷宮,竟然不知道該從哪個通道拐進。路口車輛還是一輛緊跟一輛,難道每個車上都有一個發燒病人?有什么要緊事讓他們凌晨兩點還不睡覺,開著車在大街上跑呢?
右拐后,見醫院大門關閉,門口堆放著建筑材料,根本不能接近。大門改了,改在哪里了呢?無處問人,也不能開著車亂找,于是決定到它后面那家醫院吧,雖然小些、破些,但總是三乙醫院,治個發燒還是沒有問題的。從大醫院旁邊的巷子右拐,過一個小十字路口,向前走了幾十米,一輛大型垃圾車停在路中央,環衛工人圍著在忙碌,一派火熱場面,看來一時半會兒走不了。我們的車跟得太近,垃圾車上有飄飄灑灑的東西散落。小街太窄,路兩邊又停滿了車,根本沒有調頭的位置,只好一路倒回。后面又有車跟上來,燈光嘩的照射,于是停下,打開門告訴后面,走不成了,向后轉吧。看來,半夜開車一點也不比白天省心。
倒回剛才那個小十字,向東去,走到一條大路上,再從另一條小路折回,來到那家替補醫院。
半夜看病的好處是,沒人跟你爭,也不用排隊。所有房門和窗口都靜靜地等你來,醫護人員即使打著哈欠,趴著睡覺,因你的打擾而滿臉譴責,但總算是堅守在崗位上。
其實當醫生也不難,刷刷刷單子一開,化驗血、化驗尿、拍胸片,最后得出結論: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好像她剛才用手電照到紅腫潰爛的嗓子、量體溫39度6、拿聽診器聽前心后心,還不足以判斷似的,必得把診斷權交給機器,再花了這一百多元,才能進行下一步程序。去吧,先交錢,再抽血。
丈夫去交費,我陪女兒坐在大廳的椅子上等待。從門外進來幾人,中間一男,周邊簇擁著幾個女的。男主角頭上用白紗布層層包裹,臉上和短袖上,就像是紅顏料桶扣下來一般,鮮血迸裂,圖案鮮活而生動,真實記錄著不久之前的一場毆打場面。幾個女人像對待真正的英雄一樣叫他坐下快坐下。英雄用毫不在乎的表情,不,甚至有點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風采,步履輕捷,走過來坐在我們身邊,掏出一支煙點燃,仰起臉,輕松地吐個煙圈,好像他是來醫院休閑的。那幾個女人蛾子般在幾個窗口撲來撲去,忙著掛號、問詢。我和女兒緊張地對視一下,不敢就此發表什么意見,當然也不敢表現出受驚嚇的樣子乍身逃開,盡管我們非常想這樣做。傷了英雄的自尊,可不是好玩的。幸虧丈夫交費結束,叫我們去那邊抽血,我們努力做出平淡的姿態走開。
大門外又進來三個女孩子,兩邊的小心地攙扶,中間的那位手捂著肚子,彎腰艱難地走,臉上的表情非常痛苦。
所有檢查做完,結果很快出來了,我們拿著去往急診大夫那里。
醫生說先打兩天吊針。丈夫問打柴胡行不行,也就是只肌肉注射?我們小時候發燒,打針柴胡就好了,因為孩子明天早上還要補課,不想請假。醫生說,從前那針已經不能退現在的燒了,必須吊瓶。讓她躺著打,針扎上后就可以睡覺。
躺著打針的房間里有三張床(對面是坐著打吊針的房間,兩排沙發相對),分別靠著三面墻。女兒躺在門口那張床上。護士扎上針后交代,一共兩瓶,得打三四個小時,因為有一瓶會有些疼,不能快。我們關了房間燈,為的是讓女兒睡覺。我和丈夫躺在另一張床上,他在里,我在外,隨時可以起來。其實也睡不著,蚊子嗡嗡叫,一會兒胳膊上、腿上全是疙瘩。
門被推開。“來病人了,你們起來起來,注意點影響!”護士引進來那三個女孩子。趕快起身,打開燈,那個肚子疼的女孩子躺在最里那張空床上,扎上了針,她向床的里邊靠,外面好再躺一人。那兩個女孩子互相謙讓,叫對方躺到床上去。她們彼此用極小極小的聲音說話。其中一個穿牛仔短褲的女孩子,皮膚曬得挺黑,身材細溜,雙腿修長得令人驚訝,似乎不是人的真腿,好像她因為伙伴犯了病,走得急,拉了櫥窗模特的腿就走。長腿女孩告訴另一個說,你上床睡吧,我今天夜班,早上回宿舍再睡。于是另一個被請上了床,大大的身子橫臥在床的這頭,姿態不甚文雅,但憨態可掬,睡得香甜。那長腿女孩俯在床頭的一把椅子上,姿態美好,短褲很短,長腿暴露很多,卻非性感的誘惑,而是黝黑而貞潔的懵懂,仿佛她在給畫家擺出造型。一種友愛溫馨的氣息被她們呼出,在那個床畔環繞。可能是哪家超市里的打工女孩,遠離父母家人,相互陪伴關愛,這個特殊的夜晚,兩個女伴的踴躍前來顯得尤為重要。
走廊上又有喧鬧驚慌的腳步聲、呼喊聲。又來病人了。隱約聽到醫生問,吃了什么?有人回答,海鮮。
蚊子繼續叫,屋子里非常悶熱。其實房間里有個空調,可是連著兩晚我們都沒發現,或者它的老態讓我們沒有奢望它能正常工作。我們只是做出想睡覺的樣子,但其實除了兩個病人外,都沒有睡踏實。丈夫被咬得氣惱,說他到走廊的長椅上去睡。我拿著折迭幾層的單子去給他鋪到鐵椅子上,看到另一間搶救室里燈光大亮,兩張床上,一張躺了個學齡前兒童,另一張躺了個女人,可能是母子倆,都已經掛上了吊針,旁邊還有一個青年男人,一個中年婦人,或許也是母子倆。醫生護士在旁邊站著觀察,孩子臉色蒼白,緊閉雙眼,剛才的那一陣忙碌使得小家伙止住了抽搐,這會兒累得睡著了。
那個英雄,與陪他的女人中的一個坐在另一排椅子上,他還在抽煙。他們到醫院來時,已經包扎好了傷口。是在別的醫院包的,還是在這家醫院包好后又出去辦什么事,再回來的?他們不打針,也不離開,也看不出困累,只坐在這里商談什么事情。
回到房間,摸摸女兒額頭,沁出汗來,頭發都濕了,看來是藥物起了作用。見那個長腿女孩腳也上到椅子上,雙臂環抱,把自己收成一把折疊傘。只有足夠苗條和年輕的人,才能這樣收折身體。我慈母心作祟,碰了碰她,叫她到我這邊的床上睡,她推辭一下,貓兒一樣上到床的里邊。我說,你放心睡吧,我是睡不著了,看著兩個人的吊瓶。她靦腆地一笑,黑黑的皮膚像巧克力一樣融于暗處,露出白牙,楚楚動人,像一條長長的美人魚,側身躺在床的里邊,很快發出均勻的起伏。
三點多了,走廊里安靜下來,英雄和他的女陪護們已經離去。就像是白天的午后,到了三點,一切都累了,時間步入谷底,進入一種天不管地不收的迷茫狀態,離奇的故事也該進入尾聲,諸多矛盾不再爆發,問題與病痛,撐過三點也就能等到天亮,想必不會再有人來看急診。熬夜的人也該睡去,早起的人還未醒來,這可能是夏夜里最平安寧靜的時刻。醫生護士也清楚這一點,她們的房門掩了起來,用床單蓋住身體,若不是我來叫換藥,她們會靠在椅子上睡著的。只有蚊子不知疲倦地嗡嗡叫,不停息地咬人,它們難道是夜貓子,白天睡覺晚上叮人?或者也輪班休息,二十四小時工作?我的胳膊腿上、臉上布滿了疙瘩,不停地撓,萬不得已,被子蓋到小腿上。女兒因為燒著,身體發冷,蓋上被子,露在外面的臉,汗水形成保護層,蚊子不得下口,她睡得還算踏實。
進入伏天,天天氣溫35度以上,學校堅持補課。海可枯石可爛,補課的心不能變,哪怕天塌何懼地陷,千令萬申突擊檢查學生舉報統統沒用,反正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們補課的決心。補也就罷了,簡直是喪心病狂,早上七點十分到校,中午十一點半放學,下午一點半上課,一點二十就得進到教室。每天中午,將準高三學生從短暫的午睡中叫醒,迷迷瞪瞪,撲到大太陽下,疾走二十分鐘到校。女兒每次出門,把從前的再見換成了:討厭你。開始我不明白她為何每天要帶著厚厚的校服外套。她說,教室里,男生把空調溫度開得非常低,穿著外套都冷。白天已經占滿了全部時間補課,晚上不留作業了行嗎?不行,堅決不!每晚作業寫到十一點,算是便宜你的,早上六點多,照常起床上學去。室內外溫差大,學習強度大,身體不出問題才怪。就這,她還要心心念念,打了吊針,明早繼續去上學。我常常想,我們的教育系統,莫不是被一個外星人惡魔控制住了?不把祖國花朵們的身心損壞,不把他們全部洗腦變成精致的白癡,誓不罷休。
早上六點,兩瓶針打完,女兒像個水人,全身無力,眼睛睜不開。終于決定,請半天假。天塌不下來,先回家大睡一覺再說。
二
醫生說,今晚打針最好在十點之后,不要與凌晨那次間隔太接近,于是決定,等女兒寫完作業,十一點多再去醫院。
我們帶了驅蚊劑、電蚊拍、床單。儼然是一支滅蚊小分隊,二次來到醫院。
丈夫去交費取藥的時候,我先在病房里一通噴灑,一直到走廊外面,廁所門口。
女兒要換個手扎針,躺在了直對門口那張床上,左手放在外面。今天是先打慢的那一瓶,一個多小時,才下落一半。我訂了手機鬧鈴,卻也睡不踏實,悶熱難耐,怎么躺都難受。蚊子前赴后繼而來,驅蚊劑、電蚊拍基本失效,扎上針后我們就好好睡的打算泡了湯。
兩點時分,忽聽得門外鬧鬧哄哄,有人大聲呼喊,急診,醫生!好像是很多人涌進走廊,聽到有人喊,吐血,止不住,半個小時了!有醫生在忙亂奔走,問,喝了多少?有女人答,沒多少。問,喝的白酒還是洋酒?答,葡萄酒。
看來城市并未入睡,而是以另一種方式演進。夏天的夜,找盡各種理由,變出多個花樣,遲遲不肯結束。
夜晚有著無限可能,急診科,是那種將我們從正常生活中劫持出來的機構,天大的事也先放下,解決被突然打亂的身體秩序,它的前奏常常伴隨著暴力和意外,對身體機器的野蠻操作,對自然規律的藐視冒犯,付出無知的代價,只好趕來緊急彌補與縫合。走廊上明亮的燈光,標志著急診室是永不休息的地方,醫生護士嚴陣以待,隨時收容版本迭出的身體故障,再稀奇的事對他們都是稀松平常,也難怪他們對待病人的態度,不認為你是一個又一個性格各異的人,而是各式各樣出了問題的機器,他們要尋找、要對付的相同性癥候群,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診治。
人們的來回走動、奔跑,使走廊上凝滯的空氣流動起來,彌漫著紅酒的香甜氣息,好像是挺高級的酒。聽到有人大聲嘔吐的聲音,聯想到吐出的是鮮血,恐怖感罩住了我,睡意全消。一個女人的哭聲傳來,每嘔吐一下,她就放聲哭一回,好像那位喋血者與她之間通了電,使二人有了相同的頻律。我走出去,斜對面搶救室門口,幾個人,看樣子都喝多了,飄飄浮浮站在那里,一個身體修長的女人,臉兒緋紅,是酒精的作用,失聲地哭,翻騰自己的小包包,向外掏錢。“你那里還有多少?你呢?”她問身邊的人,讓哥兒幾個把錢都拿出來,快去交費,幾個人都在翻口袋。一個男的在哄勸她,先是站她對面,攤開雙手,讓她別哭別哭。搶救室里又一陣嘔吐聲,那女子像孩子一樣大哭起來。一個小時前,她還是個風姿綽約的美人、戀人,一場酒局的女主角,沉醉在美酒與愛情里,此刻變成一個驚嚇無措的孩子。對面的男子也是手足無措的樣子,不知該怎樣更好地安慰她,除了擁抱,人類好像也沒有發明出更管用的辦法。他試試探探,終于大膽地將比他高出一截的女人抱在懷里,顛三倒四地說,何姐,何姐,聽我說,你聽我說……舌頭打絆子,或者大腦跟不上,他卻啥也說不出來。幾個人湊了一些錢,那位擁抱者抓在手里,向交費處跑去。
很多故事并沒有隨著白天的結束而中止,而是借著夜晚的神秘頑強地上演,不屈不撓地在等待、在煎熬、在交涉。深夜在這里變得叵測多姿起來。
女兒出了很多汗,頭發貼到臉上,我洗了毛巾給她擦拭。看到剛才去交費的那個青年拿著單子跑回來,收不住腳步,跑過了,像動畫片里的湯姆或者杰瑞,腳步踉蹌地退回,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四下看看,拍拍腦門,恍然大悟的樣子,進到醫生的門里。
第一瓶藥水總算滴完,我去叫護士換藥,進到值班室,空無一人,發現這里跟搶救室是相連的,人都在那里面,對付那位喋血青年。我走進去,見床上躺著一個男子,上身裸著,貼了好多管子,皮膚蠟黃,肚皮那里陷下去一個坑,周邊圍著今夜值班的所有醫生護士。我向前走去,想看到一點鮮血,滿足好奇心,可他已經被清洗干凈,見不到任何證據,只像一張皮似的躺在床上,打著吊瓶,昏睡過去。護士聽到我的腳步聲,轉過身,問,藥完了嗎?見我往床上看那青年,用身體擋住我,不知是愛護他還是愛護我,用哄孩子般的口氣說,不看不看,喝多了,走,看娃去。端了藥來到我們房間。
這一瓶快,大概一個小時就能結束。一樓走廊又恢復暫時的平靜。時間進入黎明前的黑暗與安寧。
醫院急診科,是一個預設的前提,每晚都要有幾個人光臨,醫生護士不愁沒事干。外面的夜市,路上的交通,不和的家庭,破裂的感情,花樣百出的經濟糾紛,不斷為他們輸送各式各樣的驚險。我一直在想,醫生的心里到底是希望越忙越好,還是巴不得失業?
外面漸起爭吵聲,好像是那喝醉的人,做夢一樣想起來什么,責怪醫生搶救不及時,讓他的朋友多吐了幾口血,多遭了一會兒罪,讓他們的何姐承受了驚嚇。醫生說:“你還要我們怎么樣?人一抬進來,就動手處理了,用藥得等你的交費單子,沒有單子藥開不出來。”喝醉的人語無論次:“咋說呢,你們這就叫不負責任,不為患者著想,人都大口大口吐血,哇哇的,吐了半盆子,你們一點不著急……”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說了什么,好在人已經控制住,現在靜靜睡著,他的譴責也就像是撒嬌般的絮叨,只是在證明他已經恢復了說話能力。
燈被打開,注射室進來一位中年女人和一個年輕人,好像是一對母子。母親躺下,護士給扎上了針,兒子坐在床邊守著。母親抱歉地說:“要不是堅持不住了,我不會半夜給你打電話的,打擾你們。”兒子模樣的人說:“沒事沒事。”我看她的針正常滴著,建議把房間燈關了,這樣病人可以睡得好一些。母子倆欣然同意。只有走廊上透進來的一點微光隱隱探視,病房又恢復到寧靜與安詳。母親往里面躺,拍著身邊,用很期待的語氣讓兒子躺在她外面。來回讓了幾次,兒子堅持不躺。他一定是個已婚的人,從法律到身心,屬于了另一個女人,再與母親躺在一起讓他有羞恥感,他寧可在床前身體筆挺地坐著。母親絮絮叨叨地小聲說著她的病情,可能是血壓高,引起了難受。她講述的口氣是那么平靜幸福,沒有一點疼痛或受難的感覺,好像因為病情的發作,才得以與兒子共度半個夜晚,她是多么珍惜這美好時光,很愜意地半側著身子躺在那里,面對兒子,一會兒問他熱不熱,一會兒又問喝不喝水,好像需要照顧的是兒子。
我收拾東西,叫護士來拔針,叫醒丈夫,趕快開車回家。快四點了,女兒回家還能接著睡兩個小時,再起床去上學。昨天早上已經退燒,今天打的,只是鞏固一下。拜拜了,注射室,再見了,花樣迭出的急診科。
三
中午女兒放學回家,說又燒了。一量體溫,39度4,我著了慌。按說打了兩天針,不應該再燒了呀!她說男生把空調溫度開得太低,她穿著校服外套都冷。
“我不想再請假了,可是全身難受,走路都沒勁,怎么辦呀?”她站在床前,嗚嗚哭著,是個痛苦抉擇的人。現代教育把學生訓練得如此忘我,請個假就是重大損失、嚴重事件,讓她有痛心疾首的感覺。
“那必須請假,下午好好睡半天再說。”
“可我的課本還在桌子上沒有收呢!”
“睡到下午五點多起床,或許就好了,趕六點放學的時候去學校收拾課本。來,吃了藥,好好睡一覺。”
下午四點多,摸她腦門,依然燙手。我立生恐懼,會不會不是普通的感冒發燒,而是什么急病、怪病?突然我的想像力空前的豐富,就像她放學沒有按時回家一樣,車禍、綁架、拐騙等節目在腦子里快速上演,甚至想起我編過的一本書《失獨家庭調查》。天哪,這樣燒下去,會不會化到床上成一攤水呢?將我唯一的女兒人間蒸發!再量體溫,39度6,她縮在毯子里哭了起來:“媽媽我會不會死呀?”
“死倒不會,不過這樣燒下去,有可能變成弱智、白癡,明年高考,什么中大、南大、廈大,想都不要想了,弄個藍翔技校、桃李春烹飪學校湊合上得了。我給你爸爸打電話,咱還是去打吊針吧。”
丈夫把車開到樓下。我又收拾昨晚那一套東西。來到醫院,在門口他把我們放下,調頭回去到女兒學校整理書包。
剛過六點,急診室換了個年輕的男大夫。給他看了前面所有那些材料,再量體溫,還在39度6。大夫懷疑是支原體感染,讓再抽血化驗,不過結果明天下午才能出來。他說昨天的藥里沒有退燒的,這可能是導致溫度又上去的原因,今天要加上。
醫生護士全都換班了。一個護士準備好藥之后,讓我們先去吃飯,否則藥會刺激胃。我倆在附近飯館吃了飯,回到醫院門口,見丈夫背著書包在等我們。
病房門口的床上躺了一個男人,蓋著被子打吊針,一定也是發燒。
女兒躺在最里面一張床上,扎上了針。不知怎么一抬頭,發現墻上竟然有空調,床頭柜上有遙控器,拿起來打開,竟然能制冷,只是噪音有點大,總比熱著強。
我讓丈夫出去吃飯。
又進來一對母女,女兒二十多歲,躺下打針,母親坐在床的另一頭,兩人親熱地說笑,好像姐妹一樣,談的也都是家長里短、明星逸事,看不出女兒有什么病。
門口床上男人的電話響了,他接聽,一口廣東腔,說的什么進貨、入庫之類,再后他電話不斷,不是打出就是接聽,很繁忙的樣子。他在一個電話里告訴對方,下午正在工作,感到不適,全身發冷,沒有力氣,自己來醫院看病的。一個為事業奔波的小老板,蒙在被子里,還在密切與外面那個世界保持聯系。又一個電話打來,是個女人,流水賬般說了許多,他不表態,冷靜地說,明天我打給你,現在身體不舒服。對方問,怎么你病了嗎?在哪里?他不回答,只說,明天上午我打給你。又問,小孩子怎么樣,還好吧?對方說挺好的,在玩。他掛了電話,掀開被子起身上洗手間,自己舉著吊瓶出去。是個三四十歲的男人,臉形狹窄得讓人吃驚。
一會兒他回來,電話又響,一個女子的聲音。他說,你在這個路口下車,自己問吧。
丈夫吃飯回來。我讓他照看著女兒,我出去履行每天傍晚的一小時散步。走過金店門口,看到電子屏顯示,黃金每克248元。網上有消息說,炒黃金的中國大媽賠慘了。我在大商場看到服裝大降價,一樓擺了一片衣裙攤點,好多挺漂亮的絲綢裙子三五百元,我蠢蠢欲動,可是沒帶錢。我為了找一個釘鞋的,走了幾條小街,要給涼鞋鞋絆重新換兩片粘貼。之前那個經過磨損,已經粘不牢,走路總掉。找到一個很簡陋的小店,那釘鞋老人坐在那里,與一個女人吃西瓜,每一個來釘鞋的人,要先接受他目光的嘲諷與嚴厲審查。他帶著很不屑的表情,扔了西瓜皮,用極快的方式,也不拆之前那片舊的,就將新的鉸了一塊,往上面一砸,兩分鐘完事,鞋子扔回來,問我要五塊錢。我吃了一驚,于是想起來這里是市內治安最差的地方,常有惡性事件見諸新聞,起因都是為兩三元錢的糾紛。他的女人用一種非常豪放的姿勢仰面攤在躺椅上,好像她不是女人一樣,用一種預設的挑釁目光看我。放下五塊錢,我趕快走了。
回到病房,第一眼見到直對門口床上的那對母女變成了父女,媽媽回家做飯去了。一個小時前,我出門的時候,當媽的讓女兒給爸爸打電話,問他在哪里。爸爸跟媽媽坐的姿勢一樣,整個人在床上,靠在另一頭,親昵地跟女兒說著話,用的音量是這間房里的三分之一,自覺地在他們該有的界限內,談的話題也基本屬于公共,適合別人聽到。門口廣東人的床上,籠罩著一個年輕女子,身體歪在床的上方,用手臂將病人環繞起來,大有隨時要將他攬入懷中的感覺。
我摸了摸女兒的額頭,開始冒汗,溫度有些下來了。丈夫靠在床頭看手機,我坐在床頭椅子上看書。年輕女子開口說話,聲音大得刺耳,以至于她一開腔,大家都沉默下來。她不明白這沉默是對她的譴責,反而更加得意地說著,不知道他們在這個房間的對話應該使用三分之一音量,或者小于三分之一。他二人完全是三分之三,甚至大于三分之三,那女子不但嗓門大,還夸張地裝飾她的嗓音,將每個詞每個音節都勾上花邊,學習電視主持人的發音方式,像過度包裝、華而不實的商品。不知道內心里對自己有何種期許的女子,需要這樣矯飾的聲音。我心里煩得要命,真想結結實實瞪她幾眼,可出于對她的蔑視,始終沒有看她的臉,一直不知她長什么樣,可我相信,肯定不怎么樣,好看的女子不會這么變態地在聲音上大做文章。我克制地掃視一眼她的腿和腳,皮膚很黑,不是前晚那長腿女子,為了生活在太陽下奔波曬黑,而是生來就黑的那種,不甚潔凈、皮膚糟污的那種。腳上穿一雙后跟和底子特別高的廉價涼鞋,穿這種鞋的女子,其實是在向世界宣布:我壓根不知教養為何物。他們邊玩手機邊說話。女子說:“哎呀手機又快不行了,慢死了,打不開。”廣東男子說:“換個新的。”“唉,對于我這種一年換幾個手機的人來說,也不能買什么好手機。”她用一種明顯虛假的聲音,為自己使用廉價手機開脫。
我想那男人接下來會說,我給你買一個吧。是個男人,這會兒都應該這樣說呀!屋子里安靜下來,似乎都等著廣東男人說這句話,年輕女子也在期待,我仿佛聽到她的呼吸聲和心跳聲。三個瓶子的滴答聲突然調整為一個步調,都等待一個結果。不想,廣東男人說:“叫你男朋友給你買呀!”
啊?那你們二位啥關系呢?這還摟抱著呢。屋子里的人都快要面面相覷了,我感到丈夫用后腦勺在問我,什么情況?
女子說:“哼,他才舍不得給我買呢。”她在鼓勵廣東男,似乎逼著他說,那我給你買吧。對面床上那一對父女各自眨巴著眼睛,看著墻,不說話。廣東男也不說話,三個瓶子滴答、滴答,不置可否。七個人一起捱過短暫的沉默,廣東男說起別的事,這個話題就此過去。于是我心里給這女子定位:賤人。
賤人就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不屈不撓,繼續裝飾她的聲音,嗓門大得完全不適合夜晚,更不適合病房。我知道所有這樣說話的女子過的都是與聲音不同的生活,因為寒酸,所以華麗,越寒酸越華麗,除了聲音她們什么都沒有,所以無止盡地夸張、修飾,反正沒有成本,也不需承擔什么后果,每一個音節,每一個音節的邊緣、末梢都極盡雕琢,不是她自己在說話,而是她期待成為的那個人在表演,就像在氣球上跳舞一樣輕浮無著落,極盡奢侈,也極盡讓人厭惡。
她一開口我就心煩,深深被打擾、被惹惱。那對父女也不再說話,心情都不太好了的樣子。我放下書到走廊上去。一會兒那女子出來,到護士辦公室拿溫度表,我得以從身后打量她,身材基本屬于傻大黑粗那種,偏偏穿著緊身衣裙,走路夸張地扭動。
她回到病房,用著宮廷劇里學來的姿態給廣東男將溫度計夾上,幻想自己成為受寵的人,然后又那么用胳膊環繞著他,生怕他被另外那些妃子搶走似的。病房里氣氛變得很難受,對每個人都是折磨,有一種岌岌可危的感覺,大家也都沒心情說話,分貝讓給他們,那二位賤人,立即繼承大家轉讓的資產,開心處,無所顧忌地大笑,音量擴大到三分之五、三分之六。過一會兒,女子又親手將溫度計取出來,用夸張的動作舉起來看,期待這一姿態在廣東男眼里楚楚動人,用一種驚喜的語氣說,哇,37度5,不燒了耶!好像她在參加電視節目,猜猜看,有個白癡問題是:請問他打了兩瓶吊針后,體溫降到了多少度?而她一下子猜中啦,好能干耶!她夸張地一擰身,邁著時裝模特的步伐出門,還溫度計去了。大家稍微喘了一口氣,乞求廣東男的吊針快點打完。
她又邁著很鋪張的步子回來,款款坐在床邊,腳的位置只離我坐的椅子半步遠,用一種放肆的姿態,腳尖面對我。我們五人都不再說話,好像她奪去了我們的權利,讓我們變作啞巴。那四人在看手機,我拿著一本書,卻讀不進去。我們的沉默是某種退讓,使他二人更加肆無忌憚地放大了音量。輕浮的雙關語,不打糧食的廢話,無謂的調笑。我看了看廣東男的吊針,快了,就快完了。終于的終于,廣東男抬手按頭頂上的鈴,很快護士進來,給他拔了針。謝天謝地!女的照顧男的起身,幫他提起包包,更加開心地說著廢話,挎著胳膊出門去了。屋子里的人都長舒一口氣,緊繃的神經放松了。
女兒第二瓶針剩下一半的時候,我遵醫囑去要來溫度計。想到這有可能是那對賤人拿過的用過的,我在水管下沖了又沖,直到涼透。
37度6。匯報后,醫生說,嗯,好了,退燒了。我問,明天還要打嗎?他說,如果不燒,就不用打了。
第二天傍晚,我去散步,順便取化驗單,女兒要我一拿到單子就發短信告訴她結果。“我可擔心了,要是真感染了,可怎么辦呀?”她說。
“真感染就繼續打針唄,那么我這個小說就有可能寫成中篇啦。小小注射室,多么精彩,指不定咱還遇到什么奇葩呢。”
夏夜的熱風中,我一路走向醫院。馬路上汽車疾駛,或者堵在那里,發出壓抑的吼聲。路上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覺得他們都是急診室的潛在客人,一不留神,就會去光顧那里。
醫院大門口,有一排隔離汽車的圓石墩,光溜溜的,圓潤可愛。每個上面坐著一個乘涼的人。有兩個年輕人,各拿一瓶啤酒,相對而坐,邊喝邊揮動手臂,激烈地討論著什么。坐在這里,是準備隨時喝醉了或談崩了打架,瓶子碎裂,身體開出紅花,去急診室更方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