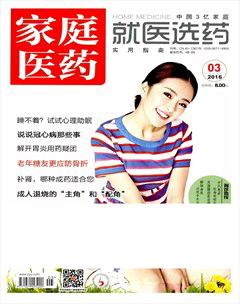如何做一名“好的”患者
徐濤
年過花甲的李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前來就診,我給他診斷為早期前列腺癌,建議入院手術。他聽到我的建議后很沮喪,因為夫妻二人退休后正在籌劃第一次出國旅游,所有手續都已準備好,近期就要出發。一旦入院,所有的計劃都要推遲甚至取消。了解到他的情況后,我認真權衡和分析了他的疾病特點,同意考慮暫時推遲手術,按計劃出游,并且跟他們解釋了前列腺腫瘤的生物學特性、他的具體病情以及推遲手術的風險等。最終,他倆經過考慮,打消了后顧之憂,決定按原計劃出國。1個多月后,旅游回國的李先生入院接受了前列腺癌根治手術,并且獲得了痊愈。
另外一名門診患者李阿姨,和張先生年齡相仿,因查體時偶然發現雙側輸尿管結石、雙腎積水來院就診。我看了她的全部資料后,強烈建議她立即住院手術取石。但她考慮到自己從來沒有任何不適,不相信我對她病情的判斷,也懷疑我為她選擇施行的是不必要的過度治療,因此拒絕了立即入院手術取石的建議,轉而尋求她一向信賴的中醫中藥治療。半年后,李阿姨開始出現少尿、浮腫,因突發急性心功能衰竭等癥狀來院搶救,最終診斷為長期梗阻導致雙腎功能不能恢復,不得不終生接受血液透析。
這是兩個真實的病例,看似很極端,但在臨床類似的情況并不少見。李先生罹患的是大家談虎色變的“絕癥”——腫瘤,恨不得爭分奪秒地去之而后心安,但他最終的結果既做到了盡可能地避免對生活質量的影響,還獲得了療效方面最大程度的收益,可謂“舉重若輕”,其原因正是基于醫生對患者的準確評估與真誠交流,患者對醫生意見的完全尊重與信賴、對疾病的坦然應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雖然李阿姨患的是目前臨床常見多發、治療技術成熟、處理手段簡單微創的結石癥,但不幸的是她對醫生心存疑慮,她的觀念中存有很多過度診治、不良醫生的偏見,加上自己對于疾病嚴重程度的錯誤估計,最終導致了令人扼腕痛惜的后果。
和人的性格一樣,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脾性”,有些疾病(例如前列腺癌)的病程比較漫長,往往在人體內“蟄伏”多年,甚至終生都不會危及生命。對這類疾病,就要根據臨床資料對患者病情進行個體化分析,如果預計疾病的發展可能導致損害,則積極治療;如果疾病的發展趨勢有可能比較溫和,那么可以選擇較為保守、風險小的方案,甚至定期監測、暫時不予治療,一旦腫瘤有進展的苗頭才開始干預。如果將這些疾病都作為“心腹之患”,給予積極治療,必定導致很多過度行為,“殺敵”與“自傷”并舉。而與之相反,生活中很多貌似“無害”的疾病,雖然沒有不適癥狀,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絕癥,卻往往潛伏很大的危害。如果不予重視,有可能“養虎遺患”,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慢性腎臟病的患者因為寄希望于偏方而演變成腎功能衰竭、前列腺肥大病人由于恐懼手術治療導致上尿路嚴重并發癥,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由于患者有各自的特點,醫患雙方對于疾病輕重存在不同判斷和評估,對治療方案的風險(失敗率、死亡率等)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對于疾病治療的遠期效果(治愈率、生存期、生活質量等)有不同的預期。因此,治療方案的選擇往往并不是單純由醫生從病情和經驗等專業角度進行判定,而是基于醫生、患者以及患者家屬相互交流、權衡之后的最終選擇,這一點在我國尤為顯著。因此,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程度、醫生對患者及家屬的態度與期望值的感受等都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選擇規范、可信賴的醫療機構,從專業醫生那里獲得專業指導和建議,對于不了解的醫學領域不妄加評判和指點,對專業人士(醫生)對病情的解釋與判斷給予足夠的尊重,對于醫學的局限性保有客觀的了解,從而獲得對于疾病診斷、治療的準確判斷和預計,這才是作為一名“好的”患者(或患者家屬)應持有的科學和理智的態度。唯有這樣,才能從醫生那里獲取真實客觀的病情評估,在給醫生以信任和信心的同時,得到最適宜的治療方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