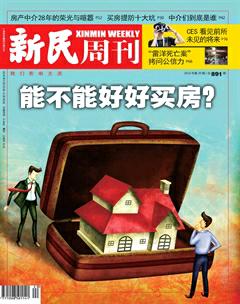在時間之外,聽優人神鼓
闕政
“時間之外”,顧名思義它不在時間之內。當我們禪坐的時候,我們把心專注在一個點上的時候,我們的心就止于這一處。只要坐一會兒你就會發現,咦,奇怪,我怎么剛剛才坐下來,一個小時就過去了。
她和林懷民、金士杰都是好朋友,曾是“云門舞集”“蘭陵劇場”的演員。
她和李安一起念過紐約大學,他的畢業作,還請她出演了女主角。
她的作品曾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幾乎只要是你叫得出名字的城市,都留下過她的足跡。
臺灣每一家誠品書店開業,都會邀請她的團隊作開幕演出。
她的作品和誠品書店一樣,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代表一種生活方式。
她就是劉若瑀,臺灣“優人神鼓”的創始人。
森林里的淬煉改變一生
28年前,劉若瑀創辦了“優人神鼓”的前身:優劇場。當時的她,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后,又赴美國攻讀紐約大學劇場藝術碩士。回國后,做過云門舞集的舞蹈演員,也曾是臺灣蘭陵劇坊(團長是金士杰)的演員,獲得過金鐘獎,前程似錦。
但就在此時,她在臺灣木柵老泉山創立了“優劇場”,十多位成員遠離繁華的臺北,駐扎在木柵老泉的原始森林中。他們每天在山上打拳、打坐、打鼓,女生束發,男生光頭,生活極其簡單。
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受波蘭戲劇大師果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內地譯為格洛托夫斯基)的影響很深。
“當時他到紐約選學生去加州訓練,200個人里選了12個,到加州以后就在一片森林里訓練,每天從下午四點半開始,至于訓練到幾點,沒有人知道,有時候是凌晨兩三點,有時候是凌晨四五點。每天都累到可以瘦兩公斤,每天回家的時刻就像是打勝了一場戰役一樣。”
果托夫斯基素來以“魔鬼訓練營”聞名,嚴格到大家只要聽說哪個藝人是出自這個訓練營,都會刮目相看。他的訓練方法,就是一直練,練到你沒了精神,也不會停,而是要等已經疲倦到極點的精神再度沖破極限,才叫停。
就這樣,劉若瑀在森林里足足“淬煉”了一年。一年后,大師讓他們創作一個作品,從自己的記憶里找出感情最深的兒歌。“我從小在眷村長大,我的父母是1949年從河北過去臺灣的,家里也沒有老人帶,和祖先文化是斷層的。”劉若瑀說,“于是我就根據陸游的《釵頭鳳》作了創作。可是導師卻說:‘看得出你是西化的中國人。這個評價,我知道絕對不是恭維。這句話,也比身體的疲累更讓我受到刺激。果托夫斯基說:‘整個東方世界聽到一個任務,都習慣于做了再說,而西方是先問才做,先理解任務。從頭腦出來的作品,是很不同的。”
經過這水深火熱的一年,劉若瑀決定要回頭重新長大,她走遍全臺灣,感受一切傳統古老的東西,感受和文化的關聯,試圖達到導師所教授的狀態:Be in concious,保持一種有意識的狀態,不再對周遭的一切事物熟視無睹。
創立“優劇場”后,她帶領著團員,在臺北近郊木柵的老泉山上,跟著叢林鳥叫、跟著山間的自然變化來生活。使團員從中體悟如何讓自己的心穩定下來,一棒一棒安靜地練習打鼓。
先學打坐,再教擊鼓
5年后,1993年,云門舞集的黃志群也加入了團隊,擔任擊鼓指導,后來,他和劉若瑀成為了夫婦,“優劇場”也由此進化成了“優人神鼓”。
所謂“優”,在中國傳統戲曲中指的是表演者;而“神鼓”,指的則是一個人在最大的放松和警覺中,通過內心的寧靜,將鼓擊打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優人神鼓”的訓練方式非常特別,必須“先學打坐,再教擊鼓”。這是黃志群帶來的新變化。黃志群曾去印度旅游,在那里遇到了一個云游僧。云游僧一見他就問:你是不是曾經打坐過?黃志群從小就跟著上海師父練功夫,十二三歲的時候,每天都要打坐2個小時。可是云游僧對他說:“你只是看見了糖盒子,糖還沒有吃到呢。”于是,原本打算旅游的黃志群,跟著云游僧去菩提樹下坐了兩周。僧問他:你有沒有注意到鳥叫?他才發現:自己坐了那么久,腦子里竟然都被無意義的念頭充斥,頭腦不是牽著過去,就是忙著未來,混亂不堪。
所以,先學靜坐,再教擊鼓。團員們每天清晨六時練太極、八時打坐,午后擊鼓、排練。
而他們那一套獨特的“當代肢體訓練法”,則來源于大師果托夫斯基。劉若瑀向記者演示了這套訓練法的起步方式:雙手平放在腿上,數到一,不動,數到二,右手向右上方伸出,數到三,右手歸位,數到四,左手向左上方伸出,再收回。但并沒有這么簡單,隨后的口令,會從一二三四,變成二三四一,三四一二,四一二三……如此循環。
“像這樣的常規訓練,要持續五天,每次連續2個小時,從一開頭的簡單,到后來會變得非常復雜,加入轉頭、說話,而且所有的循環都不是機械式的定律,需要一個人思想非常集中,同時又要保持一種放空的狀態——因為腦子越想就越容易亂,越放空才越容易做到。”
“優人神鼓”出作品非常慢,很多團員半年才學了一棒。但是黃志群說:“千變萬化,都是這一棒。”他們保持著三四年才出一部作品的節奏,不演出的時候,劉若瑀就會閉關創作,黃志群則會跑到印度去云游。可是每當一部作品誕生,都會在全世界引起轟動。當年劉若瑀在法國亞威農藝術節演出處女作《聽海之心》的時候,得到的評價是:仿佛阿爾卑斯山的山神,走到了人間。
這些年,臺灣不少名劇團都在大陸相繼打響了知名度:賴聲川的表演工作坊、云門舞集、果陀劇場……相比之下,劉若瑀“來得有點晚”,2015年才開始在上海、北京、廣州巡演,但她說:當年太早,現在不晚,一切都是剛剛好。
6年前,劉若瑀其實來過上海,當時她帶來的作品是“優人神鼓”的《聽海之心》,在東方藝術中心演出。但彼時正值世博會,全城人頭攢動,城市氣質過于燥熱,在劉若瑀看來,便是“來早了”:“境還沒有到”。
于是,她又退回山中,繼續隱居、閉關、創作。
一切不早也不晚
今年5月18日到19日,“優人神鼓”的新作《時間之外》將在上海文化廣場連演兩晚,還將赴太倉、蘇州巡演。“時間之外,顧名思義它不在時間之內。當我們禪坐的時候,我們把心專注在一個點上的時候,我們的心就止于這一處。只要坐一會兒你就會發現,咦,奇怪,我怎么剛剛才坐下來,一個小時就過去了。這一個禪定的狀態,就是一種時間之外,就是一個當下的存在。”劉若瑀如此解釋《時間之外》的得名。
舞臺上,舞者們身穿白色道袍,與鼓手們的黑色著裝相互映襯,一黑一白令人聯想到太極的意象。旋轉,則是整場演出出現最多的舞蹈動作,時而平穩如鐘、時而徐疾如風,道袍在勻速飛旋中形成一個個漩渦,像鐘表上的指針、天體的自轉,像宇宙中的黑洞,帶人漫游時間長河,穿越于作品中營造的“大驟雨”、“千江映月”、“蝕”等一幕幕亙古不變的自然現象。鼓點,有時是伴奏,有時是整齊劃一的鼓舞,令人贊嘆。“優人神鼓”的鼓是“堂鼓”,從大到小,經過師傅改造,能夠奏出不同的美妙音色。
這些年來,劉若瑀和她的劇團走遍全球,不僅帶去演出,還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在臺灣木柵老泉,如今還有了一個“禪鼓體驗營”,許多內地游客去臺灣旅游,會將這里當作必到的一站,“我們不是每年都有表演,但很多人對我們的訓練方式,對我們團隊演員的狀態非常好奇,每個月都有十幾個人會來體驗。去年我去北京演出,碰到一位觀眾,她就曾來過訓練營,她對我說:劉老師,我以前講話很急的,現在吃東西都很慢,有意識地提醒自己慢下來……”
劉若瑀希望,來看“優人神鼓”的觀眾,不要抱著看熱鬧的心態來,不只對舞臺上的聲光電感興趣,而是來體味一種禪境。這兩年,她也越來越感受到來自觀眾的共鳴:“感覺到觀眾就是我的同伴,現在,大家是真的都準備好來接受‘優人神鼓了。”
所以,一切不早也不晚,剛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