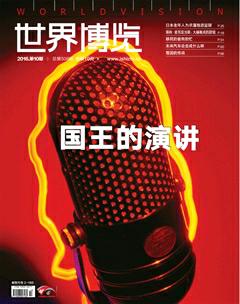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的“收藏3.0”(上)
蔣成龍
人類發展的歷史總會伴隨一系列變革,其中,科技的進步通常會創造一個時代,揭開一個嶄新的篇章。
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的進步,都對人類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眾多變化,石器的使用幫助我們登上大自然生物鏈的巔峰;銅器的發明將我們帶入了冷兵器時代;航海和航空技術拓展了我們的棲息與活動范圍。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很多是關鍵且顛覆性的。
記得90年代初,遠距離通訊絕大多數還依靠書信與電報等方法進行,家用電話在我國才剛剛開始普及。幾年后,“BP機”憑借快捷的通訊能力與相對低廉的服務價格開始在民間普及,而處于購買和使用成本問題,使用“大哥大”的人還極為稀有。這是科技發展和普及的必經之路,無可厚非。有趣的是,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恐怕很多讀者也聽說,甚至自己也秉持過這樣一個觀點:“要那東西干嘛用?有必要24小時拿著手機,隨時隨地被人呼叫嗎?”
如今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原先得出這種結論的原因很多,包括但不僅限于可用性、易用性以及投入產出比等考量。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手機網絡除了通訊外,并沒有信息交換和發布的功能,而人們對信息的價值認可與需求也尚未覺醒。
直至90年代末,Internet走出科研單位與大學院校的機房,人們也開始在生活中接觸到互聯網這一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網速越來越快,形勢越來越多,涵蓋越來越廣,以至于曾經風靡一時的“多媒體”概念在如今變得如此天經地義,充斥于手機和電腦上的各種音頻、視頻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獲取的一部分。
如果說歐洲工業革命用一百年的時間改變了世界的格局,那么互聯網從誕生發展到如今的程度,對世界的改變絕不亞于前者,且發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要知道,ARPANET(既Internet的前身)于1969年才成型,而互聯網一切的根基——“TCP/IP”協議于1972年被提出,直至1983年1月1日才開始正式應用。
講起互聯網發展史,筆者作為計算機科學專業出身的學者可以洋洋灑灑隨便寫一篇幾萬字的文章來表達各種感慨,但這和藝術品及收藏又有什么關系呢?
關系大得很……
信息爆炸 vs. 云山霧罩
根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北宋時期,東京汴梁(既如今的河南開封)城內經營古玩的店肆已成規模。如汴梁東街北潘家酒店,“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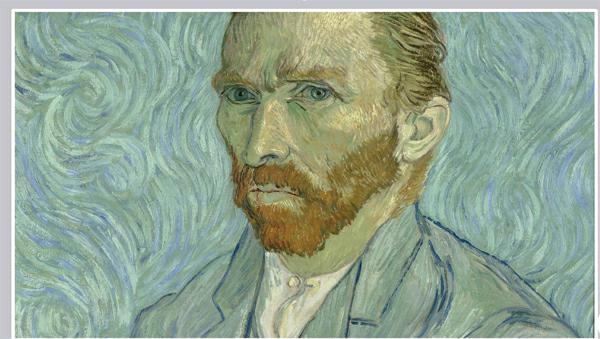
這本古籍中所記大多是宋徽宗崇寧到宣和(1102-1125 C.E.)年間北宋都城東京開封的情況,距今已有900多年。如果把那個年代的藝術品、古董、文玩交易和收藏行業描述為“收藏1.0”的話,其商業模式與行業結構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只不過當初的潘家酒店變成了如今遍布于全國各地的古玩城而已,最多也就是“收藏1.5”而已。
“古玩行業,賺的就是信息不對等的錢”,一位收藏行業的資深前輩如此總結了他多年從事古董經營的心得。確實,無論是這一行的從業人員還是收藏家個體,充分掌握器物鑒定、斷代、評估、審美、歷史等各方面專業知識,并能夠獲取及時有效的市場行情、貨源渠道等多方面信息,才能確保自己在藝術品和收藏行業的各個環節中游刃有余。
當然,除了經驗之談外,這一說法也得到了權威調查數據的支持。總部位于百慕大的Hiscox集團是一家擁有百年歷史的老牌保險公司,其起源可追溯至1901年。自1967年開展高端藝術品保險業務以來,Hiscox受到來自全球各地為數龐大的機構和個人藏家委托,對藝術品提供保險服務。也正因此,該公司在行業內發布的相關產業報告及數據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全面性。本文中所引用的數據絕大多數來自該公司于2015年發布的一項關于互聯網藝術品交易的調查報告。
根據該報告顯示,超過80%的網絡買家正是因為信息搜索的便利性而選擇了網絡平臺作為藝術品交易的手段。更具體的,其中74%通過網絡收集他人對某件藝術品的評論和評價信息,77%的買家希望獲取更多關于該商品作者或銷售商的信息,69%的買家在網上搜索該商品或同類商品的價格歷史信息,最終有64%的買家會參考權威機構的評論決定是否購買看重的商品。
由此可見,“信息不對等”在藝術品和古董交易中造成的障礙是非常明顯且普遍的,這也是互聯網對這個行業最大的幫助之一。伴隨著信息大爆炸,人們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迅速、方便地獲取各類信息。
與此同時,倡導“開放、自由”的互聯網同時也是垃圾信息滋生和傳播的溫床。由于信息來源的不確定性以及普通網民對信息識別的能力差異,導致很多人逐漸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統計數據中,67%的藝術品網絡買家試圖尋求諸如博物館、畫廊、協會組織等權威機構對商品的意見,這一定程度體現了人們對信息爆炸的恐慌。
人格營銷 vs. 權威挑戰
既然互聯網是“開放、自由”的,那么就應該允許不同的聲音出現在人們視野當中。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無論機構或個人,他們的觀點都可以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在網絡上的幾乎任意平臺迅速傳播。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出發,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人們盡情地表達著自己的心聲,在數以億記的網友中尋找共鳴,廣結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意或無意地改變著自己和相關人等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甚至彼此成就一番事業。
關于這一點,筆者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加以佐證,但相信讀者們對近年來出現的各類“網紅”(既網絡紅人的簡稱)已經了然于胸,不必再多贅述。但值得一提的是,通過“事件營銷”的手段創造話題,樹立典型人物,這涉及到商業領域一個非常有趣的慣用手段:“人格營銷”。
各大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只是人格營銷的一種表現形式,更有類似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典型案例可以更加簡單明了地體現人格在品牌及商品營銷中起到的關鍵作用。
在藝術品和收藏行業,這當然也是最為常見,甚至是最為基本的營銷手段之一。藝術家本人的形象、思想及價值觀直接影響了粉絲群體的定位與認可,而收藏家自身的知識、理念及背景也同樣影響著藏品的價值。
擁有“美國古董教父”之稱的安思遠致力于推銷“生活品味”而不單單是古董商品;以“研究并保護人類共同遺產”為己任的畢曉普把個人興趣升華到文化保護的高度;著名中國藝術品商人盧芹齋在國人心中毀譽參半,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他對古董和藝術品的審美品位及眼里堪稱一代宗師。這些人之中有些思想境界令人敬仰,有些專業能力受人推崇,而他們的藏品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自然也是精挑細選,大浪淘沙,被人們廣為認可和追捧的。
不過凡事都有利弊,在言論自由和互聯網開放精神的前提下,信息本身的權威性、真實性和有效性變得更為樸樹迷離。對缺乏專業知識和教育背景的普通網民來說,網上充斥的各類信息實在難以分辨。人們開始盲目地在各種觀點后面跟風,“羊群效應”愈發明顯。
如果僅僅對同樣一個事物產生不同觀點,并不一定是件壞事。無論是各持己見亦或挑戰權威,只要能夠獨立思考,那很可能成為技術、認知進步的引線和催化劑。遺憾的是,一旦牽扯到“利”之一字,事情就會變得愈發復雜。
近幾年來,“國寶幫”這個詞在整個收藏行業甚至廣域媒體上頻頻曝光,搞得烏煙瘴氣。對于這個詞的定義正如字面意義那樣,是一群打著“國寶”或國寶級古董的名義進行商品銷售或項目運作的團伙及個人。對于這個現象,筆者作為收藏行業的業內人士不便進行更深層的評論。排除一些商業運作上的因素不說,這一現象的普遍存在必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首先,個別終端藏家在不具備專業知識的前提下仍然過于自信,好高騖遠,這通常出現在資金實力雄厚的個人收藏家身上。在某一個領域的成功造成了他們過度的自信和膨脹的信心,固持己見且人認為親,最終被蒙在鼓里而不自知。即便事后了解到真像,通常也礙于“成功人士”的面子,難以與他人啟齒,逐而不了了之。
另一類古玩愛好者則抱有濃重的“撿漏”心態,幻想國寶級古董和藝術品會因為“賣家不識貨”就從天而降砸到自己頭上,又或者聽信各種子虛烏有的故事而被商家迷惑。要知道,撿漏心態通常也伴隨著“賭徒心態”,有道是“十賭九騙”,這古人的金玉良言著實是不可不聽。
無論哪一種受害者,他們都會經歷一個共同的階段:專家掌眼。確實,如果自己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儲備不足以應對,那么請個“明白人”幫忙看看是最簡單有效的解決方案了。然而,“人”這以因素的復雜程度不比“物”低,甚至更勝一籌。
在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時,大眾更傾向于擁有較大社會知名度的明星專家。以往,這類明星專家通常經由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出現在公眾面前,相關統計數據以60%的受訪者比例證實了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媒體本身對專家的權威性進行了篩選和“擔保”,使得信息相對可靠。不過,隨著媒體節目的娛樂性越來越強,學術性相對減弱,如此以往,日后恐怕很難再以權威話語平臺的身份得到認可了。
如今,隨著網絡資訊的爆炸式傳播,從網站新聞到手機消息,各種心靈雞湯、靈丹妙藥可謂是滿天亂飛,網絡紅人借助事件營銷等手段以超越傳統媒體的速度和效率,將人們的大腦洗了一遍又一遍。明辨是非者少之又少,掉進溝里的不計其數,這讓本已經高深莫測的藝術品和收藏行業更加雪上加霜,給不少準備參與其中的潛在愛好者造成了難以逾越的心理陰影。
互聯網上的誠信危機愈演愈烈,藝術品和收藏行業也經歷了信息爆炸的洗禮。遺憾的是,直至目前為止,仍然沒有比較權威的第三方公益組織或政府機構能為廣大初入行業的愛好者提供基于網絡的指導與服務,把真實、可靠、及時的信息傳遞到愛好者群體中。
(下期待續:伴隨著互聯網商務的發展,互聯網為各行各業的經營帶來的不僅僅是新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挑戰與商機。在這樣的浪潮之下,藝術品和收藏行業被帶入了2.0時代。)(作者為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