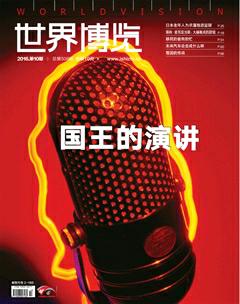長安酒家胡
周惠民
作者:導語:胡姬酒肆是唐代風情的代表,卻忘了碧眼高鼻的胡姬早就在中國大城市中當壚賣酒,閱盡人間辛酸。
歷史學家有唐型文化的說法,指出大唐盛世時期,許多異族在中國安居樂業,共享和平。還有人引李白的《少年行》詩: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想象唐代長安城中,酒肆林立,碧眼高鼻的胡姬,穿梭顧客之間,促銷各種美酒,就跟今天北京三里屯,上海新天地的風情一樣。這些詩句讓人誤以為胡姬酒肆是唐代風情的代表,卻忘了碧眼高鼻的胡姬早就在中國大城市中當壚賣酒,閱盡人間辛酸。
從商代開始,北方游牧部落便開始接觸定居的農業民族,不斷戰爭之外,文化上也相濡以沫,互相影響。漢書紀載:周幽王時,“申侯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畎戎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到秦穆公時,西戎八國臣服于秦,漸漸遷徙到山西、陜西、河北一帶,從此,血統與文化不斷融合。漢初,中國與匈奴的沖突轉為激烈,征戰不已,各有勝負。戰敗者不是被殺,便成俘虜。除了打仗之外,匈奴如果發生動亂,有人自愿進入漢朝地界,稱為“內附”。
從漢書紀載來看,漢代進入中國的匈奴人數不少。他們不以農業為生,大多數人愿意居于城市,當時工業并不發達,服務業也有限,只能開個小店,賣賣吃食營生,所幸大城中一直都需要餐飲,卓文君與司馬相如就曾經在四川開館子,當壚賣酒,而長安城中,用胡姬美女作為號召的酒館,更不在少數。
公元前200左右,詩人辛延年寫過一首《羽林郎》,專講胡姬的故事,流傳甚廣。“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因為貌美,引起不良少年的注意,“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過這位胡姬已經結親,表明“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舊,貴賤不相逾。”
漢代的胡姬并非特例,只是一般人討論的少。到了唐代,大批西域商人到中國,經商定居,許多城市還出現“蕃坊”。這些蕃坊中,少不了要有人經營餐飲業,解決胡商或當地居民的飲食問題,酒店中除了供應酒水,還有許多“胡食”,例如胡餅、胡盤肉食。店家為了招徠,頗有聘用胡姬賣酒者。
胡餅是以燒烤而成,與今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的馕類似,大家都明白。至于胡盤肉食,也以燒烤而成,特點是使用中亞傳入的香料調味。當時西域傳來的香料種類甚多,又以胡椒、蒔蘿子與蔗糖最為重要。蒔蘿子就是茴香,原產于地中海沿岸,細針狀的葉子有清香味,西方人拿來調味魚料理,也拌入生菜中;進入中國,華北各地喜歡包茴香餃子,味道特殊。蒔蘿種子味道辛辣,曬干后也是重要香料,燉煮牛、羊肉,唐代的胡盤肉食,就是用小茴香子調味燒烤而成。另有一種小茴香,也稱孜然,大約也在這時進入中國,新疆燒烤,小茴香是重要的調味料。賀朝生于八世紀,大約與李白同時,他的《贈酒店胡姬》詩提到:“玉盤初膾鯉,金鼎正烹羊”,點出酒家的特色菜。
除了胡食之外,當然也要有水果釀造的“胡酒”,例如“三勒漿”便是用三種不同的水果釀制而成。李肇生于公元九世紀,著有《唐國史補》,書中紀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中國釀酒多以谷物為之,初次接觸西方的水果酒,味道甜美,不免好奇。
胡姬酒家有美酒,有胡食,還有胡姬,自然吸引。李白具有中亞血統,特好此道,留下許多歌詠胡姬的詩。例如《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詩說:“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李白詩名滿天下,后人多半效法,于是大家都胡姬酒肆,不論真假。宋代陸游《夢行益昌道中有賦》說“酒舍胡姬歌折柳”。益昌在今天的四川廣元,未必有胡姬,可是一旦有了酒店,要是不寫胡姬,恐怕說服不了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