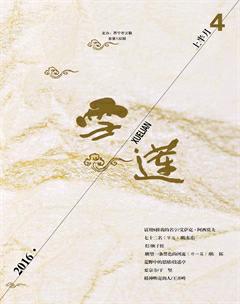書(shū)生的勝利
沈榮均
1161年的冬天,注定屬于大宋書(shū)生虞允文。這個(gè)冬天,他和他的南宋水軍兄弟,遭遇了軍事史上著名的水戰(zhàn)——宋金采石大戰(zhàn)。
1161年,紹興辛巳年,五行白蠟金屬。書(shū)生虞允文缺水克金——庚寅(1110年)生人,松柏木屬。家鄉(xiāng)蜀地隆州(南宋置)仁壽藕塘,算成都平原邊上。土坡貧瘠,雨水少,草木的長(zhǎng)勢(shì)頑強(qiáng)。茅草、松柏、麻柳、槭蒿……有名無(wú)名的草木,插滿家鄉(xiāng)的九村十八灣。遺憾的是,沒(méi)有一條江河愿意流經(jīng)其境。資源嚴(yán)重匱乏,也無(wú)便捷的水路,幾乎談不上有商品的貿(mào)易。百里之外的眉州、嘉州,因?yàn)獒航⑶嘁陆拇鞑幌ⅲh(yuǎn)比他的家鄉(xiāng)富裕。那時(shí)候,就想要有一條河多好,向南、向東、向北、向西,向家鄉(xiāng)的四個(gè)方向,流淌。那命定的水意。深埋于心,外化于情。緩慢,再緩慢,比青衣江更闊,比岷江更流長(zhǎng)。
虞允文并不迷信風(fēng)水。作為書(shū)生,前人的經(jīng)驗(yàn)提醒他,再高明的預(yù)言也離不開(kāi)人的定力。
完顏亮就沒(méi)有定力。海陵王完顏亮是虞允文的對(duì)手。這一年的秋天,他統(tǒng)領(lǐng)金國(guó)數(shù)十萬(wàn)鐵騎和步戰(zhàn)隊(duì),從新遷的南都汴京(今開(kāi)封),發(fā)兵四路南下。東路軍是主力,由他直接指揮,攻淮南。中路軍進(jìn)襄陽(yáng),西路軍逼大散關(guān)。還有一支經(jīng)海路,直取臨安(今杭州)。
金軍來(lái)者不善,臨安城內(nèi)爭(zhēng)論不休。爭(zhēng)論歸爭(zhēng)論,宋廷還是部署了防御:成閔守鄂州,吳麟守川陜,李寶守海路,劉琦守兩淮。
完顏亮的主力,依然一路所向披靡。一月之內(nèi),幾乎沒(méi)有遭遇一場(chǎng)像樣的阻擊。強(qiáng)渡淮河,輕取廬州(今合肥),很快就要“飲馬長(zhǎng)江”了。
這一次,他與叔叔完顏?zhàn)阱觯ㄘPg(shù))在三十年前發(fā)動(dòng)的南侵不同。先輩只為覬覦宋室財(cái)富,他有著更為直接的狂想。
宋金上百年的拉鋸已近白熱化。一邊是完顏亮開(kāi)始做治宋美夢(mèng),一邊是高宗王朝頻臨生死存亡。
陰歷十一月,完顏亮立馬江北。戰(zhàn)事的天平明顯偏向他的金軍。
按理說(shuō),接下來(lái)橫渡長(zhǎng)江,一路南下建康(今南京)和臨安,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他猶豫了。眼前是長(zhǎng)江天險(xiǎn)采石磯,那是長(zhǎng)江流經(jīng)廬州和建康的一處極狹之地,從軍事的角度屬于冷兵器時(shí)代兵家必爭(zhēng)天險(xiǎn),從風(fēng)水學(xué)的角度看又是景象叢生之地。完顏亮不是來(lái)江南打秋風(fēng)觀光的。他親率東軍主力20萬(wàn),加上其他三路共60萬(wàn)人馬,決定他本可以從更長(zhǎng)的戰(zhàn)線果斷渡江。但他放棄了這個(gè)打算,選擇投石問(wèn)路——先以兵力分波次取長(zhǎng)江要塞采石,邊攻邊探,試圖在戰(zhàn)役的轉(zhuǎn)換中,尋找傷亡更小的戰(zhàn)機(jī),以小股突擊的方式打開(kāi)江防缺口,站穩(wěn)根基,然后大部隊(duì)登陸,再圖南下。應(yīng)該說(shuō),以完顏亮一貫的戰(zhàn)風(fēng),不應(yīng)采取如此保守的謀略。長(zhǎng)江采石段,地勢(shì)險(xiǎn)狹,水流湍急,并不適宜投放大兵團(tuán)。按他的設(shè)想,以一比二力量進(jìn)攻,金軍少說(shuō)也可以組織五、六個(gè)波次。正常情況下,兩三個(gè)波次下來(lái),宋師了了萬(wàn)八兵士早已潰不成軍。即便宋軍頑強(qiáng)抵抗,待第四個(gè)波次上去后,再牢固的江防也會(huì)露出破綻。一旦突擊隊(duì)上去,宋金多年來(lái)的恩怨,估計(jì)就在采石畫(huà)句號(hào)了。完顏亮采取在狹窄江段強(qiáng)行登陸的策略,基于金軍強(qiáng)悍的單兵作戰(zhàn)能力,以及十倍的兵力優(yōu)勢(shì)——可以源源不斷地往對(duì)岸發(fā)兵,前赴后繼,直到把南宋水師的1萬(wàn)8千人消耗殆盡。
軍事學(xué)迷的共識(shí)是,作為進(jìn)攻的一方,面對(duì)地利劣勢(shì),完顏亮還是保守了——過(guò)分拘泥于局部的戰(zhàn)事。倘若他的數(shù)十萬(wàn)大軍沿長(zhǎng)江北岸千里防線,一字排兵,千船齊發(fā),取壓倒式的大攻勢(shì),也許就沒(méi)有后來(lái)的那么多事了。
完顏亮并不急于求勝。在他看來(lái),在渡過(guò)淮河后,勝利就已被他揣入囊中。還有什么可以讓征服者保持足夠的激情?我猜想或許是過(guò)程。他需要享受一場(chǎng)婉轉(zhuǎn)的勝利。就像下一場(chǎng)并不對(duì)稱的棋局,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的一方難有取勝的快樂(lè),就變著法子一顆接一顆吃掉對(duì)方的殘兵敗馬,直到一個(gè)人,一桿旗。對(duì)手不得不俯首稱臣。勝利者的快感由此被緩慢地拉長(zhǎng),放大。
完顏亮不只是個(gè)戰(zhàn)役家,還是宋漢通。印象中的江南,緩慢,富饒,不堪一擊。“東南形勝,三吳都會(huì),錢(qián)塘自古繁華,煙柳畫(huà)橋,風(fēng)簾翠幕,參差十萬(wàn)人家。云樹(sh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wú)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jìng)豪奢。”(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柳詞的柔軟和奢華,加重了他的猜想。此刻,正值采石的黃昏。長(zhǎng)江自西向東,滾滾而下。在大江面前,再雄壯的男人,精氣神也要打折扣——不被冷卻,也被淹沒(méi)和吹散。何況采石的風(fēng)景,美得有些異樣。柔軟的鳥(niǎo)羽和煙嵐,勾起完顏亮的惆悵,愁緒彌漫和蕩漾。這不是個(gè)好兆頭。詞家張孝祥在采石一戰(zhàn)平息后,吟詠過(guò)此番愁緒:“赤壁磯頭落照,肥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張孝祥《水調(diào)歌頭·聞采石戰(zhàn)勝》)同樣見(jiàn)景思情,完顏亮沒(méi)有張孝祥那么好的才華去抒寫(xiě)。但他可以沉靜——柔軟的南宋正在消解鋒芒。一月南進(jìn)數(shù)千里,沒(méi)有經(jīng)歷一場(chǎng)痛快淋漓的大戰(zhàn),就像一只拳頭,陷在棉垛里,難以自拔。江南的水域,對(duì)于他的軍隊(duì),也許太過(guò)陌生。家鄉(xiāng)在東北,世代游牧,逐草而生。水是他們生生不息的動(dòng)力。完顏亮對(duì)于長(zhǎng)江天險(xiǎn)的拒絕,或源于敬畏冥冥之中那一片水意。
完顏亮并不著急謀劃一鼓作氣渡江。他需要重樹(shù)精氣神——命令兵士們江邊筑壇,宰殺白馬、牛、豬各一只,祭天。眼下的天意就是長(zhǎng)江。他需要江水的寬恕和幫助,以增日益衰減的自信。
同樣敬畏這一片水意的,是南宋書(shū)生虞允文。不同于完顏亮的膽怯和惆悵,當(dāng)寬闊湍急的水域,出現(xiàn)在虞允文眼前,他隱隱覺(jué)得有什么正由外而內(nèi),一點(diǎn)點(diǎn)與軀體的每一小塊撞擊、契合——渾身的毛孔仿佛被激活,血肉在沸騰,骨頭嘎嘣作響——內(nèi)心的江河終于澎湃。
丙子、丁丑兩日。水意由內(nèi)而外。凜冽的北風(fēng)并沒(méi)有封凍江南的水意。
一場(chǎng)水意覆蓋另一場(chǎng)水意。溫暖覆蓋凜冽。
一條江河與另一條江河完成對(duì)接。長(zhǎng)江天險(xiǎn)與虞允文的宋軍血肉,連接成橫阻金國(guó)鐵騎的水上長(zhǎng)城。
很多軍事迷認(rèn)為,虞允文正在完成一場(chǎng)理論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以區(qū)區(qū)1萬(wàn)8千兵士,對(duì)抗十倍的金軍。宋軍參戰(zhàn)的人數(shù),《宋史》記載,1萬(wàn)8千,是無(wú)可爭(zhēng)議的。至于金軍,有20萬(wàn)、40萬(wàn)、60萬(wàn)三種說(shuō)法。華盛頓特區(qū)大學(xué)終身教授楊高崴研究認(rèn)為,“雙方動(dòng)員的兵力在七十萬(wàn)至八十萬(wàn)”( 楊高崴《陳康伯〈親征詔草〉與紹興辛巳宋金大戰(zhàn)》)。我個(gè)人比較采信20萬(wàn)一說(shuō),剩下的40萬(wàn)并沒(méi)有直接參加采石大戰(zhàn)。不管是20萬(wàn)、40萬(wàn)、還是60萬(wàn),但最少也是一比十。且金軍的單兵作戰(zhàn)能力,非常的強(qiáng)悍。長(zhǎng)江邊上的這場(chǎng)對(duì)決,明顯不對(duì)稱。
虞允文也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但他無(wú)興趣也無(wú)閑暇去思考,與完顏亮的對(duì)決以何種方式的失敗收?qǐng)觥2墒氖虑椋仍诿冀蕖?wù)實(shí)地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是眼下當(dāng)務(wù)之急。
四品中書(shū)舍人虞允文到采石的時(shí)候,加了頂軍階很低的臨時(shí)烏紗——督視江淮軍馬參謀軍事。上司叫葉義問(wèn),知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職務(wù)相當(dāng)于參謀聯(lián)席會(huì)兼戰(zhàn)區(qū)最高長(zhǎng)官。葉義問(wèn)從杭州到建康后,耳聞金人已陳兵采石,便不打算繼續(xù)朝前挪動(dòng)了。按理說(shuō),他應(yīng)去戰(zhàn)役一線督視。自己怕死,就讓50歲的作戰(zhàn)室老參謀虞允文替他去。他給虞允文的任務(wù)并無(wú)督視和指揮,他只是去犒師,無(wú)非噓寒問(wèn)暖,走走過(guò)場(chǎng)而已。身處防御前線,宣傳和后勤工作也難敷衍,將士們都盯著呢。四路金軍也沒(méi)閑著,正在對(duì)岸集結(jié)。他們就像一群來(lái)自北方的狼,隨時(shí)可能以水陸并進(jìn)的方式撲過(guò)來(lái)。戰(zhàn)事一觸即發(fā)。
也沒(méi)細(xì)想這么多,虞允文就奉命去了。在他看來(lái),采石的守軍一定嚴(yán)陣以待。事實(shí)上只是他一廂情愿的想象而已——原來(lái)的駐軍司令王權(quán)臨陣逃跑,朝廷新任的李顯忠還不知道在哪里。
虞允文在采石,曾經(jīng)和守軍兄弟有過(guò)些對(duì)話記錄在案。后來(lái)的戰(zhàn)局證明,虞允文的對(duì)話,可以看作是影響采石戰(zhàn)役勝負(fù)最重要的政治動(dòng)員。
見(jiàn)軍士三三兩兩散坐路旁,馬鞍和盔甲扔一地,個(gè)個(gè)耷拉腦袋,根本不像臨戰(zhàn)的樣。
就問(wèn):金人要渡江了,你們等啥?
等啥?軍士們抬了頭,見(jiàn)是一文官老頭,也沒(méi)好聲氣:將軍們都跑了,我等還打啥仗?
虞允文被問(wèn)急了,就軍士這士氣,確實(shí)還打啥仗,估計(jì)不等對(duì)岸敵人戰(zhàn)鼓擂響,早逃散沒(méi)影了。
這哪行?就跑上跑下,把渙散的將士們四下召攏,表了個(gè)態(tài)度:我是奉朝廷之命來(lái)慰問(wèn)各位的。看吧,我把金帛、誥命都拿來(lái)了。你們?yōu)閲?guó)立功,我一定會(huì)向上頭報(bào)告,論功行賞。
見(jiàn)老頭子代表朝廷發(fā)話,宋軍上下的精氣神又上來(lái)了:我等吃盡金人之苦,誰(shuí)不想抵抗?既然有你老作主,我們?cè)敢馄此酪粦?zhàn)。
看來(lái)書(shū)生虞允文的動(dòng)員做到點(diǎn)子上了。不過(guò),這番話應(yīng)該由上司葉義問(wèn)來(lái)講的,輪不到他一個(gè)參謀軍事出風(fēng)頭。一同去的同事悄悄說(shuō):朝廷叫你來(lái)勞軍,不是要你督戰(zhàn)。別人把事情搞糟了,你何必自己去替人家背包袱?
同事的話貌似在理,虞允文不愛(ài)聽(tīng),很生氣:這算啥話?大宋江山社稷臨危,我等豈能只顧自己的得失,逃避責(zé)任,一走了之?
我相信此話不是虞允文一時(shí)沖動(dòng)。國(guó)家興亡,匹夫有責(zé),不是用來(lái)掛在嘴邊裝飾門(mén)面做秀的,是須堅(jiān)持的書(shū)生本色。
從文獻(xiàn)記錄的上述對(duì)話,看得出采石戰(zhàn)事前,長(zhǎng)江邊的宋師根本無(wú)心抵抗,更談不上有效地組織防務(wù)了。事實(shí)上,擺在虞允文面前的,真是一個(gè)爛攤子。負(fù)責(zé)淮西的都統(tǒng)制王權(quán),剛把部隊(duì)開(kāi)到廬州,覺(jué)還沒(méi)睡穩(wěn)當(dāng),一聽(tīng)說(shuō)完顏亮來(lái)了,撒腿就跑,把廬州、和州直接拱手出讓了。失去了防御縱深的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锜,本來(lái)還在病中,一看自己成了孤軍,只得棄守淮陰、揚(yáng)州,退至南岸的鎮(zhèn)江。主帥當(dāng)了逃兵,剩下幾只小股部隊(duì),一時(shí)也亂了陣腳。淮南到宋都臨安,騎兵突擊也就一天一夜的節(jié)奏。高宗一聽(tīng)說(shuō)淮南淪陷,嚇壞了。趙構(gòu)是個(gè)挺沒(méi)自信的主,一會(huì)怕戰(zhàn)議和,一會(huì)想起金人欺負(fù)上頭不爽,又誓戰(zhàn),搖來(lái)擺去,像臨安城里的墻頭草。一日,他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沒(méi)過(guò)幾天,又當(dāng)眾燒了詔書(shū),發(fā)誓親征(“遂定親征之議”)。說(shuō)是發(fā)誓,其實(shí)是被陳康伯、楊存中、虞允文這些主戰(zhàn)派給逼的。發(fā)完誓,那幾個(gè)好戰(zhàn)的部下也被派去前線。這下好了,沒(méi)人再聒噪,就又跑到海上顫危危漂起來(lái)。連皇帝都搖擺不定,東躲西藏,你說(shuō)朝野上下有多亂。
虞允文沒(méi)有亂。且不講多年的俸祿,莫白拿。只說(shuō)一肚子的圣賢書(shū),總不能白讀吧。更何況不是一直在等待冥冥之中的那一場(chǎng)水意么?他覺(jué)得自己就是一條焦躁的魚(yú)——內(nèi)心的江河,正醞釀巨能,一旦尋到突破口,將匯入眼前的大江,以洶涌的姿態(tài)合二為一。當(dāng)然,魚(yú)尋找水意,只是我的想象。用今天的話說(shuō),他到采石后,說(shuō)的那些話,干的那些事,其實(shí)為找一個(gè)書(shū)生的存在感。
突破口又在哪?
有軍事迷站在進(jìn)攻一方的金軍,提出三個(gè)觀點(diǎn)——
孤軍長(zhǎng)途奔襲,后勤跟不上,不占天時(shí)。
長(zhǎng)江天險(xiǎn),采石要塞,易守難攻,不占地利。
南宋水師,裝備一流,擁有超級(jí)戰(zhàn)船。但金軍只有占領(lǐng)淮南后臨時(shí)征用的小艇,訓(xùn)練也不到位,不占人和。
事實(shí)并非如此。在天時(shí)、地利、人和三條件中,戰(zhàn)略專家更看重人和。當(dāng)人和條件具備,天時(shí)和地利也會(huì)發(fā)生轉(zhuǎn)換。采石固然險(xiǎn)峻,江防固然牢固,裝備固然精良,但軍心已渙散。所有的天時(shí)和地利,在氣勢(shì)洶洶的金軍面前,都不過(guò)是狹窄的時(shí)間和空間而已。
沒(méi)有防御的縱深,也無(wú)迂回的可能。
虞允文被逼到絕處。他找來(lái)小股部隊(duì)的統(tǒng)制,據(jù)記載有張振、王琪、時(shí)俊、戴皋、盛新這么幾個(gè)人,叫他們集結(jié)游兵,重新布防。有人覺(jué)得這是個(gè)笑話,且不說(shuō)一個(gè)中書(shū)舍人參謀軍事有沒(méi)有權(quán)調(diào)兵譴將,就那1萬(wàn)8千散兵游勇去抗擊金軍,從數(shù)量上講也是一開(kāi)始就已吃了敗仗。就像同事勸說(shuō)的那樣,你是來(lái)犒師的,不是來(lái)督戰(zhàn)的,何必自討苦吃呢?
在很多人眼里,虞允文就是在自討苦吃,接手了采石這個(gè)發(fā)燙的山芋。
虞允文知道戰(zhàn)役的勝負(fù),取決于人,不是其他。他向?qū)⑹總儠悦鞔罅x:“吾位從臣,使虜濟(jì)江則國(guó)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jìn)無(wú)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jìn)而死,死吾節(jié)也!”
這段話,核心的意思是,大敵當(dāng)前,有進(jìn)無(wú)退,后退投降是等死,進(jìn)攻殺敵是死,但死跟死不一樣,殺敵死,死的是氣節(jié)!
都說(shuō)絕處可以逢生。死就是虞允文的絕處。連死也不怕,還怕啥?
他的水師兄弟同樣別無(wú)選擇——他們只能同仇敵愾,背水一戰(zhàn)。
恐怕虞允文也沒(méi)有想到,自己的戰(zhàn)前陳詞,竟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在很多人看來(lái),當(dāng)時(shí)的背景下說(shuō)這些,高調(diào)又不接地氣,誰(shuí)聽(tīng)得進(jìn)去?或許,他本就是情不自禁在自說(shuō)自話。這些話或許壓抑太久,不發(fā)則已,一發(fā)便不可收拾——內(nèi)心的江河像決了堤,情感和力量前所未有地澎湃,與他的水師兄弟形成強(qiáng)大的共鳴。
有時(shí)候,沒(méi)有退路,或就是路。正應(yīng)了句古話,置之死地而后生。
書(shū)生虞允文內(nèi)心的江河洶涌而出!
更多的江河洶涌而出。1萬(wàn)8千洶涌的血肉江河洶涌而出!
他們不是散兵游勇,是爆發(fā)了巨大戰(zhàn)斗力的水師!
他們的戰(zhàn)斗力源于內(nèi)心的軍人榮譽(yù)——打敗敵人,然后幸福地活下去!
后來(lái)的戰(zhàn)事,可以從零散的史料中窺得概貌。完顏亮坐陣江北,舉小旗指揮。數(shù)百人的突擊部隊(duì),駕船嘗試沖鋒渡江。虞允文派主力戰(zhàn)艦,正面迎敵。還把附近當(dāng)涂縣的民兵也招募來(lái)了。民兵駕一種叫海鰍的輕型船,速度快,機(jī)動(dòng)性強(qiáng),充當(dāng)先鋒,金軍的戰(zhàn)船很快被沖散成兩塊。陣勢(shì)一散,戰(zhàn)斗力下降很快,加上水性不如宋軍,兵士們還沒(méi)弄明白是咋回事,便已陳尸江心。第二天,虞允文將主力舟師,投送到楊林河口,布陣阻擊。金軍在上游河道,部署了許多船。虞允文就又組織游記隊(duì)去偷襲,一把火把金船給點(diǎn)了。一看渡江的工具沒(méi)了,還怎么過(guò)江,金軍再無(wú)心沖鋒。宋軍大勝。在采石過(guò)不了江,完顏亮只好退而求其次,移師瓜洲,再圖下一步。當(dāng)然,這一次戰(zhàn)役轉(zhuǎn)移,讓他喪失了渡江作戰(zhàn)的最佳戰(zhàn)機(jī)。勝利的天平開(kāi)始朝宋軍傾斜。
從以上的描述,大家可能覺(jué)得這是一場(chǎng)索然無(wú)味的戰(zhàn)事,甚至連一些引人入勝的玄機(jī)和波瀾也沒(méi)有。
這就是歷史文獻(xiàn)記錄的采石大戰(zhàn)。兩天的戰(zhàn)事,虞允文指揮1萬(wàn)8千南宋水師,大敗完顏亮的20萬(wàn)金軍。僅此而已。
如果細(xì)心一點(diǎn),可能會(huì)發(fā)現(xiàn)虞允文在一些謀略細(xì)節(jié)上,也有可圈可點(diǎn)之處。如盡可能借助與水有關(guān)的地利——還是水。虞允文說(shuō),魚(yú)為水存在。他和他的南宋水師因長(zhǎng)江存在。長(zhǎng)江擁有最有力的武器——水。兵來(lái)將擋,水來(lái)土掩。長(zhǎng)江之水,就是橫在金軍面前的萬(wàn)里長(zhǎng)城。水讓完顏亮失色,卻給了虞允文無(wú)限的想象力和可能性。采石江邊的虞允文,就是一條久旱逢雨的游魚(yú)。他將車船、蒙沖、海鰍等型戰(zhàn)船,編成多兵種協(xié)同的突擊戰(zhàn)隊(duì)。車船大,防衛(wèi)性能優(yōu)異,作主力。蒙沖和海鰍(也叫“海鰭”)小,機(jī)動(dòng)性好,速度快,擔(dān)當(dāng)突擊。楊萬(wàn)里在《海鰍賦·后序》中有記載:“采石戰(zhàn)艦,曰蒙沖,大而雄;曰海鰭,小而駃。其上為城堞,屋壁皆堊之。”金軍單兵作戰(zhàn)能力強(qiáng),不能近身與之廝殺。但宋軍有火箭、霹靂炮、神臂弩、克敵弓等利器,能最大限度地延伸兵士的臂膀和部隊(duì)的作戰(zhàn)半徑。采石南岸地形奇特,就以波濤、巖石和山坳為盾,周密部署江防。用兵也有些講究,如小股部隊(duì)機(jī)動(dòng)游擊。當(dāng)然,虞允文更懂得群眾的力量才是無(wú)窮的。就發(fā)動(dòng)民間社團(tuán),充實(shí)車船和岸防,擺疑兵陣。總之,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條件,把一支數(shù)量嚴(yán)重不足,只能被動(dòng)挨打,形勢(shì)明顯不利的防衛(wèi)部隊(duì),變成了以攻為守,四面突擊,愈戰(zhàn)愈勇的鐵軍。
愈戰(zhàn)愈勇,是因?yàn)樯舷慢R心,放下包袱,不顧生死,只知陷陣。這一點(diǎn),尤為重要。
關(guān)于這場(chǎng)戰(zhàn)事,我查閱了有關(guān)史料,沒(méi)有找到更為詳盡的披露。一些軍事迷想了些辦法,試圖還原戰(zhàn)事的細(xì)節(jié)。研究古代戰(zhàn)役史的學(xué)者,也曾就戰(zhàn)役勝負(fù)原因,作過(guò)理論上的分析,但一比十的兵力對(duì)比,弱者勝,強(qiáng)者負(fù)的戰(zhàn)局,還是難以讓人信服。
“以一當(dāng)十”,聽(tīng)起來(lái)仿佛頗輕松。它忽略了許多沉甸甸的東西。比如傷亡。
一場(chǎng)戰(zhàn)局的勝負(fù),是要計(jì)算傷亡代價(jià)作為前提的。冷兵器時(shí)代,人與人近距離搏殺,直接推動(dòng)戰(zhàn)局的展開(kāi)。有戰(zhàn)事就有傷亡。勝負(fù)又直接與傷亡有關(guān)。
有一種戰(zhàn)事,是不需要計(jì)算傷亡的。那就是正義之戰(zhàn)。
采石之戰(zhàn),就是一場(chǎng)南宋軍民的正義之戰(zhàn)。
八百多年過(guò)去了,戰(zhàn)事的細(xì)節(jié)早已模糊,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書(shū)生虞允文和他指揮的南宋水師贏得了最后的勝利。完顏亮至死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撐南宋水師,如此不怕死。他更不知道,一個(gè)并無(wú)作戰(zhàn)指揮權(quán)的文弱書(shū)生,竟然是這場(chǎng)讓他蒙羞飲恨之戰(zhàn)的勝利者,幕后的精神領(lǐng)袖。
虞允文并不認(rèn)為他是宋軍的精神領(lǐng)袖。軍士們?yōu)樽约憾鴳?zhàn),為榮譽(yù)而戰(zhàn)。如果有精神領(lǐng)袖,也是他們自己。在打贏對(duì)手之前,首先戰(zhàn)勝自己。打敗金兵活下去的強(qiáng)大意念,比江岸的草根還堅(jiān)韌,比江中的波濤還恒久。
虞允文成功了,他書(shū)寫(xiě)了軍事史上以弱勝?gòu)?qiáng)的著名戰(zhàn)役史,扭轉(zhuǎn)了南宋與金的戰(zhàn)略力量對(duì)比,從此宋金進(jìn)入長(zhǎng)時(shí)間的對(duì)峙。南宋獲得了修養(yǎng)生息之機(jī)。可以說(shuō),沒(méi)有采石之勝,就沒(méi)有了后來(lái)金國(guó)朝廷政變,完顏亮被嘩變的部下所殺,也沒(méi)有南宋和元朝后來(lái)的那些紛紛擾擾了。當(dāng)然,這都是假設(shè)。
歷史不可假設(shè),但允許有改寫(xiě)歷史的奇跡存在。所以我們現(xiàn)在來(lái)看宋金采石之戰(zhàn),也并不是歷史文獻(xiàn)記載的那樣平淡無(wú)味。它所以留下諸多疑點(diǎn),為開(kāi)啟我們的豐富想象。
采石一戰(zhàn)后,虞允文因?yàn)樽吭降膽?zhàn)功連升三級(jí)。
關(guān)于采石之戰(zhàn),元人脫脫在他主持編修的《宋史》里有個(gè)說(shuō)法:“昔赤壁一勝而三國(guó)勢(shì)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shì)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zhuǎn)危為安,實(shí)系乎此。” 這個(gè)評(píng)價(jià)既沒(méi)有站在宋一邊,也沒(méi)有站在金一邊,應(yīng)是比較接近真相的,沿襲至今,算主流。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有人認(rèn)為,此說(shuō)有夸大虞允文作用嫌疑。理由是,采石一戰(zhàn),戰(zhàn)事規(guī)模和雙方傷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甚至還有人認(rèn)為那是場(chǎng)本來(lái)就應(yīng)取勝的戰(zhàn)役,因?yàn)槟纤嗡畮熡?xùn)練有素,熟悉長(zhǎng)江水戰(zhàn),作戰(zhàn)經(jīng)驗(yàn)豐富,占據(jù)長(zhǎng)江天塹,擁有先進(jìn)的武備,總之,不缺天時(shí),地利。這個(gè)觀點(diǎn),貌似邏輯上講得過(guò)去,但忽視了關(guān)鍵一點(diǎn):宋室上下的精氣神在開(kāi)戰(zhàn)前就已被金人打散了。精氣神一散,即便有利的天時(shí)地利,也可能成為阻擋勝利的障礙,再?gòu)?qiáng)大的武備說(shuō)不定轉(zhuǎn)手就成為敵人的戰(zhàn)利品。
虞允文和完顏亮主導(dǎo)的采石戰(zhàn)事,往小了說(shuō),是一個(gè)書(shū)生同一個(gè)武人的對(duì)決。武人講實(shí)力,硬碰硬。書(shū)生以柔為器。完顏亮強(qiáng)大,偏偏遭遇了一個(gè)不服輸?shù)模辛σ彩共簧稀S菰饰氖菚?shū)生,讀圣賢書(shū),煉內(nèi)功。內(nèi)功是啥?梁羽生在《唐宮恩怨》里有描寫(xiě),摘一把樹(shù)葉隨手扔,嘴里輕吹一口唾沫,也會(huì)成為殺人利劍。這是文學(xué)家對(duì)于內(nèi)功外化的想象。真正的上乘內(nèi)功是戰(zhàn)役主官?zèng)Q勝的意志,以及將士們不怕死的精神。虞允文和他的南宋水師就煉成了這樣一身上乘內(nèi)功。大敵當(dāng)前,他們爆發(fā)出超乎尋常的戰(zhàn)斗力,決定了戰(zhàn)役的最后走向。
采石之戰(zhàn),不是長(zhǎng)江的勝利,不是車船和神弓的勝利,是虞允文和他的水師精氣神的勝利,是柔弱書(shū)生的勝利,是普通士兵的勝利,是一群庶民的勝利。歸根結(jié)底,是“人”的勝利。
虞允文以活生生的戰(zhàn)例,演繹了血肉長(zhǎng)城的傳奇。他是書(shū)生——水作的骨肉。他的南宋水師,不乏水和骨肉——書(shū)生式的堅(jiān)韌。長(zhǎng)江固然險(xiǎn)峻,因?yàn)槟纤诬娒袷乃篮葱l(wèi),愈加堅(jiān)不可摧。
書(shū)生虞允文的勝利,得到后世更多書(shū)生的高度認(rèn)可。“世間允文允武,可比武侯者,非虞允文莫屬。”此話的出處,我沒(méi)有找到。都知道諸葛亮是智慧神,謀略超人。但看作者把虞允文與諸葛亮相提并論,我想多半是民間書(shū)生所為。書(shū)生嘛,容易激動(dòng)。
還有更激動(dòng)的。
采石之戰(zhàn)八百年后,有人夜讀《續(xù)通鑒記事本末》。此人文韜武略,讀史有個(gè)雅興,一激動(dòng),喜歡在書(shū)旁點(diǎn)評(píng)幾句。
這一次他讀到:“丙子中書(shū)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敗金兵于東采石……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并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行動(dòng)不穩(wěn)。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dòng)。金士卒不死于江者,金主完顏亮悉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
一個(gè)小小的文職參謀,竟然帶兵打敗了十倍于己的敵人,這還了得!書(shū)生激動(dòng)不已。
這一激動(dòng),就在書(shū)頁(yè)旁批注了八個(gè)字:“偉哉虞公,千古一人!”
注意批文的要點(diǎn)——不是諸葛亮,也不是別人,一千年來(lái),就出了這么一個(gè)書(shū)生。
這個(gè)書(shū)生叫虞允文。
寫(xiě)這話的人叫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