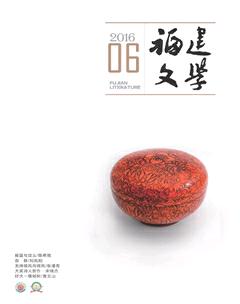黃榮才:寫活了“叛徒”
鴻琳最近的三篇中篇小說《梨城叛徒》《尋找慈恩塔》《告密者》撲騰出不小的聲響,頻頻被轉(zhuǎn)載,或者獲獎。讀完這三篇小說,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人物形象共同的標(biāo)簽:“叛徒”。
這三篇小說的主角是“叛徒”,可以說鴻琳以比較集中的筆墨塑造了這一類小說形象,讓“叛徒”直撲目光之內(nèi)。小說的共同特點是好讀。我一向認為,講故事是小說的重要一極,如果文章連讓人讀下去的吸引力都沒有,或者說達不到閱讀快感,那可能是在極小范圍內(nèi)的藝術(shù)試驗,這當(dāng)然也有存在的價值,可達不到廣為傳播的可能。鴻琳的小說顯然不是曲高和寡,他會講故事。被認為是叛徒的“我二叔”李牧,最后是日本釣魚計劃的重要棋子,而烈士陳天放卻是叛徒,指認特派員的“叛徒”王小海,最后卻是來處決叛徒的地下黨員(《梨城叛徒》);告密者本來應(yīng)該是被人深惡痛絕的,為什么豬籠寨的村民反而把朱滿倉這樣的告密者當(dāng)成全村的英雄?章文為什么面對敵人的槍口沒有挺身而出?他的自責(zé)是否是因為自己的怯弱?事實的真相是他背負更為重要的任務(wù),因為朱滿倉的指認,章文被捕,全村的人除了被殺的五人之外都幸存下來,可是鴻琳的筆不僅如此,他更深一層,因為章文被捕,他的情報之路和解救之舉戛然而止,清源山抗日部隊近百名戰(zhàn)士身亡(《告密者》)。為了保全謝家坊眾多的生命,“我父親”導(dǎo)演了一場戲,和陶梅芳等人引爆了炸藥,炸掉慈恩塔,用無奈的舉措婉拒了炸掉日軍軍火庫的命令(《尋找慈恩塔》)。這三篇小說是三個蕩氣回腸的故事,信息量極其豐富。
在這三個小說中,鴻琳讓自己走了進去。他不是在保持距離之外的審視,而是以一種尋找、解讀的姿態(tài)出現(xiàn),這種貼近的敘述方式,讓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有在場的感覺,會更吸引閱讀的目光。而且,鴻琳注重視角的轉(zhuǎn)換,現(xiàn)在和過去的穿插、融合,當(dāng)下和以往的跳躍,加上推測、爭論,可以說,鴻琳在小說中把事情復(fù)雜化了。常言道,水至清則無魚,鴻琳無疑是攪起了一潭渾水,讓事情的真相無法簡單看穿,小說里的“叛徒”不再骨感,顯得豐滿并有褶皺。在他曲里八拐的敘述中,事情的真相若隱若現(xiàn),呼之欲出,但又是在希望之中存有許多疑慮,在疑慮中又夾雜希望和渴望。這樣的膠著讓小說是個立方體,不到最后,無法輕言結(jié)局。可以說,無論哪篇小說,鴻琳都充分調(diào)動了讀者的閱讀神經(jīng)。
故事再精彩,也離不開人。寫故事是為了寫人,因為有人物,故事就不僅僅是故事。鴻琳這三篇小說,寫活了“叛徒”這特殊的人物形象,顛覆了對叛徒的簡單化標(biāo)簽。這三篇小說中的“叛徒”不再僅僅是貪生怕死、逐利貪色,他們不再是扁平的,而是更為立體復(fù)雜。或者說他們活得更為痛苦、糾結(jié),他們的選擇是用刀在割自己,割肉體也割內(nèi)心,因此他們的選擇就充滿疼痛。死對于他們來說不是問題,困難的是活下來。因此,盡管時過境遷,他們的活還是比死痛苦,活在自責(zé)、愧疚、痛悔之中。死去的人會上供臺,接受景仰的目光,而活著卻是疼痛。鴻琳的小說做了一個提醒,任何人、任何事物,我們看到的或者聽到的也許僅僅是表象或者事情的某個方面,妄下斷論是不負責(zé)任的行為,也許就是對歷史的誤讀。正因為如此,鴻琳努力想通過小說修正對歷史的誤讀,我想這是小說家責(zé)任感在小說之中的體現(xiàn)。在鴻琳筆下,英雄、狗熊無法簡單分類,人性也不是直通通的“一條道走到底”,正因為“多向”,小說因此豐富多彩。
盯著“叛徒”這個形象的多角度,或者探究真相的解讀,鴻琳無疑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方向,寫小說,找到方向不容易,找到突破點不容易,鴻琳是幸運的,他的尋找不再茫然。同時,他的方志辦工作崗位為他的尋找提供了幫助,鴻琳可以繼續(xù)尋找。
如果要提點意見,我覺得鴻琳在某些地方文字可以更凝練一些,在眾多的敘述條線之間的跳躍豐富的同時更為清晰一些,例如《梨城叛徒》。這或許有助于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更容易進入,或者更心無雜念地沉浸在鴻琳編織的小說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