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畫有關(guā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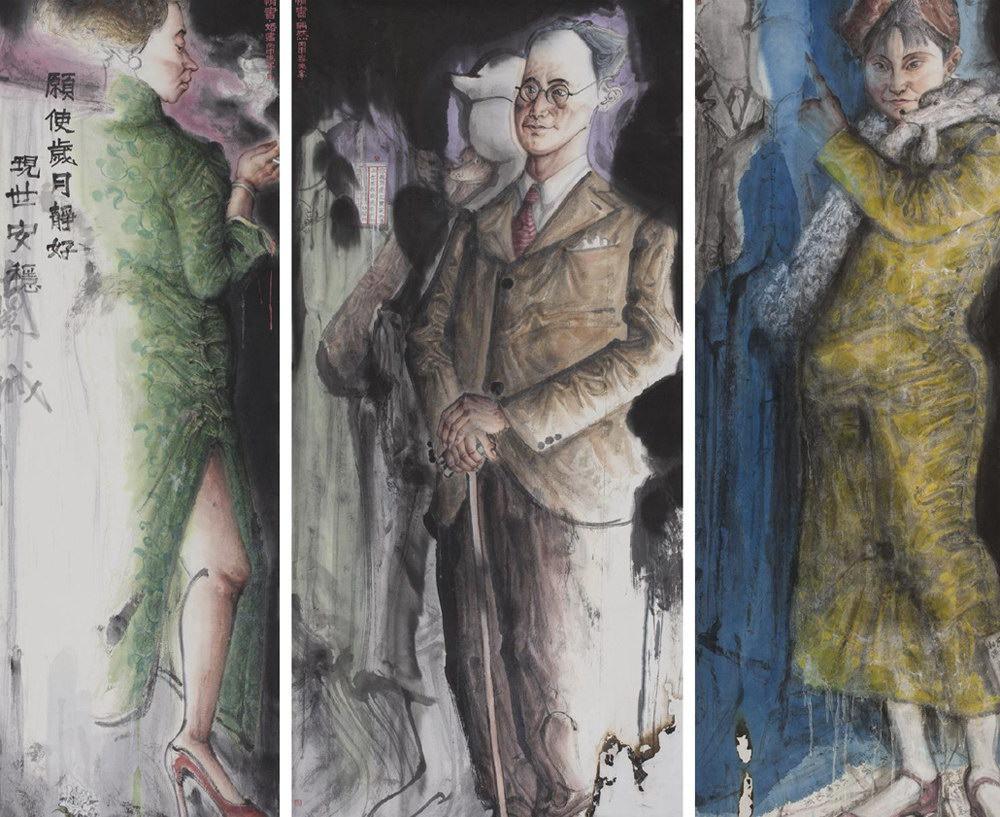
藝術(shù)簡(jiǎn)歷
盧曉峰,1977年生于山東。1999年畢業(yè)于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獲學(xué)士學(xué)位;2003年畢業(yè)于中央美院國畫系第一工作室研究生課程班;2006年畢業(yè)于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獲碩士學(xué)位;2010年畢業(yè)于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獲博士學(xué)位。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現(xiàn)任教于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
自己都經(jīng)常會(huì)覺得奇怪,零零碎碎、斷斷續(xù)續(xù)地也寫過不少東西了,關(guān)于畫的卻極少。細(xì)想來,許是生活中、書本上所得到的感受與領(lǐng)悟都已放在畫紙上,再用文字來表述倒顯得有些多余了。畫可以自如地游走于人的感覺、認(rèn)知、冥想,把一塊塊、一段段散碎的虛無整合成可見的意念,只要稍稍留心一下,耳目所見所聞的所有都可被折換成畫的概念。我們可以把一卷云,一段水從自熱狀態(tài)中剝離出來,然后修頭飾尾,將它們裹上生人的氣息,重新擺布在流水線生產(chǎn)出的毫無感知的絹素之上,意外的,它就具有了另一種生命,有了一種沾染了人間煙火的煥新意味,連帶的,本是壓滿機(jī)械空洞的白紙上也鋪陳了或渾厚沉郁或清新雋永的無邊意境。畫可以說很多,其范圍小至個(gè)人情懷,大到國計(jì)民生,在不同人的手里表現(xiàn)出不同的關(guān)照與偏愛,但當(dāng)碰到關(guān)于它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時(shí),自問自答式的解決方法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一張畫的由來,它的生成,以及兩張甚或幾張畫之間的連承關(guān)系微妙異常,其間的許多關(guān)鍵似乎只有借助文字方能一一道清。正如畫的立面是一張紙一樣,畫感受與感受畫之間仿佛也隔有一層紙,許多時(shí)候,用畫來表現(xiàn)對(duì)畫的感受總覺像穿了厚厚的棉襪,腳趾上的觸覺神經(jīng)無法盡興摩挲那些快慰感官的內(nèi)在詳實(shí)。
大部分的畫來源于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嫁接。路遇的某個(gè)場(chǎng)景,某張面孔,某個(gè)身影,突然間的一陣微風(fēng)拂面,一聲嬰孩的啼哭,一滴水落于塘泛起的空澈,都會(huì)在心弦上輕輕地扣動(dòng)一下,繼而引出遐想無限。也會(huì)有沉年積郁在心頭的某些情緒,冗冗總總,如扯不斷的絲線,密密地纏雜一處,形成蓬蓬的一團(tuán)亂。梳理它們是件相當(dāng)勞心的工作,總想在這些亂中找出一點(diǎn)可以用畫來描述的起始與落腳點(diǎn),想找出它的緣由,它的蓬勃過程,結(jié)果卻發(fā)現(xiàn)多年的糾結(jié)早已如生滿浮萍的靜湖,想溯源哪一株萍是最早的原生者是如此困難,放眼望去,滿目皆是一片盎然。坐于湖邊的我,手里的鉛筆在追隨眼光的到處記錄著,種種思緒變化尾隨筆尖的鉛芯在紙上游走,意識(shí)已經(jīng)走開,留下的是手與眼的無間揉和,等到低頭細(xì)看之時(shí),卻驀然驚覺速寫板上只有滿紙的鮮綠,滿紙的亂。恍然領(lǐng)悟,原來任何東西在經(jīng)年的混雜發(fā)酵后剩下的唯有外觀的合成,想抽絲剝繭般地厘清種種情緒的由來顯得如此艱難,留給畫的恐怕只有這一團(tuán)團(tuán)的亂。它是超越了的亂,是經(jīng)過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之后的篤定的山。這樣正好,因?yàn)楫嫿K究是要落于紙上的,再多的虛幻終要借肯定的真實(shí)來顯現(xiàn)。文字的長(zhǎng)處在于可以極盡能事地夸張,極盡細(xì)微地反復(fù)吟詠某種情愫,可以上到九天攬?jiān)拢?xì)至針鼻引線,語言帶著思維縱橫馳騁,天馬行空。同樣的情境如用畫來表現(xiàn)則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畢竟與文字相比,畫面呈現(xiàn)的事物更直觀,更肯定,從而也就更缺少想象的空間。人的理想終究不是現(xiàn)實(shí)可以滿足的,有太多時(shí)候,現(xiàn)實(shí)只是一個(gè)殘缺的環(huán),正如落在水中的明月,粼粼的波紋總會(huì)將它割成片片碎痕。唯有在現(xiàn)實(shí)之上將理想疊加上去,水中月才會(huì)升為天上月,缺才會(huì)成為圓。現(xiàn)實(shí)中不能完滿的事物,可以在畫上來補(bǔ)成。由某一個(gè)身影而引發(fā)的浮想,關(guān)乎這個(gè)身影的本來,但更多時(shí)候,我們是借助它來托付自己的某種情懷。曾路遇一個(gè)騎單車的男孩,只是在與他交錯(cuò)的剎那,自己內(nèi)心的某種浪漫情懷便如噴涌的浪潮,迅猛地傾倒在了他的身上,聲勢(shì)是如此地浩蕩,仿佛期待了多年才在這一刻撞上,朦朧中都卻能看到波濤在他身上濺起的水花。“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靜女其孌,貽我彤管”,他車筐里放置的紙袋已被理想中的鮮花取代,不問真實(shí)的他要去往何處,通往理想境的他是趕往那個(gè)與佳人相約的地方,帶著笑,帶著一絲羞怯,臉上泛著紅。此時(shí)已分不清他是我還是我是他,只有一種浪漫情緒在彌漫,濃重的彌漫,以至于把地面都折成了一塊快樂漂浮的方毯。現(xiàn)實(shí)就這樣真切的發(fā)生在理想之中,或者確切地說,理想在現(xiàn)實(shí)中發(fā)生了,更準(zhǔn)確地說,理想與現(xiàn)實(shí)在畫上交合了。
許多時(shí)候,畫是被當(dāng)作日記來看的。生活中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成敗得失,都可被寫進(jìn)里面。一時(shí)的快樂得意仿佛一劑沖劑,在杯中水由熱變涼的短暫間隔中便消失殆盡。只有那種長(zhǎng)久雋永的喜悅方能進(jìn)入畫的日記,這是一種對(duì)生命由衷的熱愛與向往,對(duì)美好的持續(xù)渴望,對(duì)未來的堅(jiān)定與信守。同歡欣不同,失落與感傷、惆悵與黯然是可以維系時(shí)間更長(zhǎng)的情緒,伴隨人生的種種境遇,隨時(shí)日變遷,它可以沉淀得更深更厚,更醇更濃,再走入畫中時(shí),也就會(huì)以更加成熟的姿態(tài)昂然邁進(jìn)。中國古人喜在山水之間寄寓情懷,描繪的多是蕭條淡遠(yuǎn)的落寞獨(dú)寂,特別是元人畫作,空亭寒林,道不盡的荒疏,枯石古木,訴不盡的悵然。即便密如王蒙者,蔥山郁嶺中也有著掩映不住的孤寒。是什么使這些畫人喪失了宋人那種崇山峻嶺,云蒸霞蔚般的磅礴之氣,失去了那種勃勃向上的生命力與進(jìn)取心?是河山喪盡的頹然,是生命無盡的失落,還是由身至心徹底的衰垮呢?他們的畫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日記,是時(shí)事、世事強(qiáng)加于他們的體驗(yàn),愿與不愿,自覺或不自覺的,他們都在記錄、書寫著一代人的整體經(jīng)驗(yàn)。大悲或大喜須脫胎于大起大落,亂世離合方能鑄就彌散于整片山林的某種悲壯通懷。恰逢盛世的我們,無法切膚地感受這些大時(shí)代才有的陣痛,就姑且流連于自身的一得一失、一悲一喜中吧。或許將這種小小的個(gè)人情緒置身于龐大紛繁的世事面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但每一朵花都有它開的緣與因,也唯此,眾花凋后方能有整個(gè)時(shí)代氣象的果。
文人悲秋,似乎是宋玉啟發(fā)了千百代人多愁善感的情結(jié),實(shí)則是春生秋殺這種自然變化所引發(fā)的深深失落感的映射。宋玉揭開了蓋上的封泥,就有了無數(shù)管感傷的筆在帛上紙上一書再書,一嘆再嘆了。這種基因并沒有因?yàn)楫?dāng)代世事、時(shí)事的巨大變化而消亡,而是變異在更加復(fù)雜,更加多樣化和更加不可預(yù)測(cè)的每個(gè)當(dāng)代人的不同境遇中。和著個(gè)人獨(dú)享的冷暖體驗(yàn),千百種混雜情緒淹沒在由時(shí)針支配的生活繁忙中。再無暇去坐享臨清流而賦詩,踞東籬以賞菊的閑適愜意,生存的壓力是如此之重,國家機(jī)器下的碌碌眾人如工蟻般奔走疲命,穿梭于不同時(shí)段的不同場(chǎng)所,勞忙著不同場(chǎng)所的不同工作。生命原本是一個(gè)鮮活的機(jī)體,在持續(xù)的高耗磨損中慢慢喪失了靈動(dòng),變得逐漸滯濁,失了它的魂和它的感覺機(jī)能。也有如我一般的人手足無措地站在這些麻木身旁,被一種離場(chǎng)的陌生感擾的焦躁不安,既想躍人他們以逃避那扼人喉管般的可怕孤獨(dú),又不甘的想保留一絲清醒,來思考一下關(guān)于人生與殘存的未來。矛盾就這樣發(fā)生了,瘦弱的軀體在表面的平和下埋藏著如火的抗?fàn)帲跉埓娴囊淮缈臻g里,對(duì)眾生的憐憫和眾生對(duì)我的憐憫交錯(cuò)產(chǎn)生,分不清哪個(gè)是對(duì),哪個(gè)是錯(cuò)。或許脫離了社會(huì)整體的思維只能淪于被流放的荒蕪之地,但同時(shí)許多燦爛的智慧也恰巧與人邂逅在這漫漫旅途中。如果能站在云端以一個(gè)巨人的眼光俯察這些圈養(yǎng)在欄里的可憐生命,那些固執(zhí)堅(jiān)守信念的離群者方有可能獲得肯定。生活是個(gè)小小的香爐,日常的所見所聞、所感所受在日子的焚燒中層層堆積在爐灰里,慢慢腐朽成厚厚的爐垢,不再有任何知覺,唯有明滅在香頭的一點(diǎn)煙火,在斷續(xù)的保留著前行的希望。畫也是如此吧,一張張記載著不同空間與時(shí)間里的人與事,不同的心情。翻過一頁又一頁,總還有未知的前方在等待著,有未曾經(jīng)歷過的體驗(yàn)在靜候著。世界由小我與大我構(gòu)成,目之所矚,身之所容的棲身之惑與對(duì)社會(huì)、對(duì)宇宙大環(huán)境的思索和神往,對(duì)人類存在、發(fā)展的反思與詰問,都是畫應(yīng)當(dāng)予以關(guān)注的。坐榻臥游的宗少文,駕風(fēng)御氣的莊周,守靜至虛的老聃,都曾于動(dòng)靜之間對(duì)人的生存境與超越境進(jìn)行過縝細(xì)至微的思考,于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坐一臥中妙語空諦。如果可以把我們的意識(shí)分割成兩半,一半清晰,是虛境,一半渾濁,是實(shí)境,虛實(shí)皆由心所生,為心所欲,取合由我,從畫的角度來理解它們,無疑會(huì)帶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