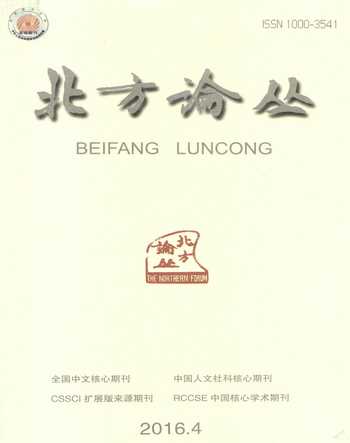國家權力重構視角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地方自治
徐振岐
[摘要]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以孫中山政治思想為指導開始了國家權力重構過程,其中地方自治作為國家權力重構的重要路徑得以迅速開展。但在進入政治實踐領域后,孫中山政治思想無法滿足南京國民政府適應所處的政治形勢的需要,南京國民政府只能從傳統政治中尋求有效手段,以至于逐漸背離了孫中山政治思想,導致與專制體制相契合的保甲制在自治的旗幟下得以大行其道。
[關鍵詞]孫中山;南京國民政府;地方自治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4-0086-05
國家權力作為政治權力的核心主體,意味著依靠國家組織體系,在政治共同體內建立普遍約束力的支配服從關系,從更寬泛的角度理解,國家權力是指國家的統治力、政府的管理力、社會的治理能力。國家權力的重構是指一定歷史時期內,原有國家權力的解體與新的國家權力的建構。
近代中國的國家權力重構還包含了封建專制政治的衰敗和現代民主政治的興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在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選擇中,以繼承孫中山遺教為名推行地方自治,但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與專制政治相契合的保甲替換了自治的內涵,體現了南京國民政府國家權力重構的方向仍然是傳統的專制統治。
一、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與方向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面臨清末以降對于國家權力重構的客觀要求,如何實現由專制傳統向民主政治的轉變,成為擺在南京國民政府面前的難題。對于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及方向,孫中山的政治思想(革命程序論)為南京國民政府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即以軍政一訓政~憲政的方式漸進實現民主政治,在此過程中,既重建了國家的統治力、政府的管理力、社會的治理能力,又可最終實現中國政治體制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整體政治面貌。
在孫中山的革命程序論中,訓政為民主政治能否實現的關鍵。1924年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明確指出,在軍政階段結束后,訓政時期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扶植民眾推行地方自治,在地方自治過程中實現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民權。在孫中山看來,地方自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治理方式的轉變即以自治代替官治,更在于地方自治的成功關系到憲政時期五權憲法的實現,關系到將來民主政治的基礎。孫中山將國家權力分為政權、治權兩個不同部分,“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孫中山認為,將來的政治必須達到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在孫中山的設想中,“五權憲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各個獨立。”同時人民享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形成對政府權力的制約,“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此即為權能分治、以權治能,充分體現了孫中山民權主義的思想。從政治實踐角度看,孫中山認為,權能分治的實現有賴于地方自治的完成。在政府扶植民眾推行地方自治的過程中,民眾掌握基本的民權;在地方自治完成后,各縣經普遍選舉產生代表組成國民大會行使政權,對政府的政治運作加以監督,以此實現以權治能。對于地方自治的基礎性作用,孫中山予以充分肯定,多次強調指出,欲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其道必自以縣為民權之單位始也。”深入分析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可以看出其精髓是將地方自治視為實現政治民主的基礎:在地方自治過程中培養民眾掌握運用基本民權,在地方自治實現后達成權能分治、以權治能。
從國家權力重構的角度考察,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包含了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及方向。其中,地方自治的實施無疑是國家權力重構的必要路徑,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傳統的社會結構根深蒂固,傳統的自然經濟及農業人口的生活方式沒有根本改變,地方自治的實施一方面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用以改變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將農村引入現代化道路上來;另一方面,在地方自治過程中,以自治代替官治,并以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訓練民眾,使得民眾從封建專制下的愚民變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為實現中國現代政治民主奠定堅實基礎。憲政時期五權憲法、權能分治、以權治能為標志的民主政治形式是孫中山為南京國民政府規劃的國家權力重構的方向,其實現的基礎就是地方自治的完成。對于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南京國民政府予以明確認可,并多次強調要以此為執政依據,政權組織行使、政府運行模式等,“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等人更是鼓吹:“總理遺教是我們今日唯一的求生存的路線。”“吾黨同志之努力,一以總理全部之遺教為準則。”但在此后具體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日益背離了孫中山政治思想,在國家權力重構的方向和路徑上均偏離了預定軌道。
二、南京國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實施與困境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在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選擇中,標榜以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為指導。國民黨中央于1928年8月召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會上正式宣布進入訓政階段,主要工作是推行地方自治。為了加快推進地方自治,國民黨中央還擬選派人員赴各省指導自治工作,“遵照擬就中央遴選工作人員交國民政府派赴各省指導地方自治工作暫行辦法,并于廿八日提呈中政會議通過。”在地方自治推行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擬定了一批自治法規,尤以1928年9月公布的《縣組織法》能體現出地方自治內涵,其中規定了縣為地方自治的基本單位,縣以下區域劃分為區、鄉(鎮)、間、鄰四級自治組織,實際上是構建了縣及縣以下的自治體系即區鄉(鎮)閭鄰制。南京國民政府在自治法規中還試圖體現孫中山要求的四大民權,《鄉鎮自治施行法》《區自治施行法》中規定:只要滿足“在本鄉鎮居住區域內居住一年,或有住所達兩年以上”、“年滿二十歲”這兩樣條件,即可出席鄉(鎮)民大會及區民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甚至對于地方自治的施行時間和具體事務,南京國民政府也予以詳細規劃,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制定了《訓政時期完成縣自治實施方案分年進行程序表》,指出地方自治以6年為期,內容包括厘定自制系統、儲備自治人才、確定自治經費、肅清盜匪、整頓警政、調查戶口、完成縣市組織、訓練人民、初期清丈土地、舉辦救濟事業等諸多方面。
從表面上看,南京國民政府在成立之初,繼承了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并有所發展,實際上并非如此,往往地方自治的相關政策法規制定后成為一紙空文,在各地均沒有得到貫徹實施。1930年11月,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的政治報告指出,除河北、河南、寧夏、綏遠、察哈爾、山西、陜西、甘肅、廣西、青海等十省未有報告外,其他各省的地方自治推行因財政困窘、地方紛亂等原因,“致自治事務,同時停頓。”1931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也認為,地方自治困難重重,難有成績。從具體事務考察,大多數省份僅完成縣以下的自治區域劃分,在涉及經費、人員等重大要素的人才訓練、機關組建等方面幾無進展。以訓練自治人才來說,稍有進展的省份也只進行了局部地區的區長訓練,區以下幾乎都沒有得到訓練,同時,正因為自治人才匱乏,導致自治機關組建困難重重,大多數地區僅組建了區公所,鄉鎮一級自治組織成立極少。也正因如此,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要求的對民眾進行民權訓練根本無法實踐,至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地方自治實施全然沒有達到預期成績。
這種局面出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諸如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權威;自治法規不盡如人意;自治經費匱乏;自治人員素質底下;民眾缺乏自治意識等等不一而足,但從根本上說,是地方自治的實施與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所處的政治形勢相矛盾。南京國民政府甫一建立,即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是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不斷掀起武裝起義,削弱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另一方面,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事威脅的加劇。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南京國民政府不斷向集權化發展,集權專制體制得以強化。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國民黨即以黨國體制掌握國家大權,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通過《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實際上是國民黨以訓政的形式將政權、治權掌握于一黨之手。在具體施政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名,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政治上排斥其他中間勢力,更以特務統治造成白色恐怖迫害異己;同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內構建個人集權體制,并企圖以法西斯主義運用于當時的政治,1931年5月5日,蔣介石在國民會議上即宣稱中國應借鑒法西斯主義,將法西斯主義融入國民黨的政治理念中。由此可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集權主義、專制主義成為主要的政治趨向。這也導致南京國民政府在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與方向上產生沖突,即孫中山提出的以自治代替官治,以地方自治作為重構國家權力的路徑與南京國民政府強化專制獨裁體制的國家權力重構方向相悖。因此,以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為指導的地方自治,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不可能取得成功,南京國民政府只能從中國傳統的政治領域尋求與集權主義、專制主義契合的國家權力重構路徑即保甲制。
三、保甲制與南京國民政府國家權力重構方向的契合
保甲制作為通過戶籍編制來控制人民的制度,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有很長的歷史,其功能在于“通過鄰里之間的連帶法律責任來維持治安。”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之初,就有意同時推進保甲制,南京國民政府于1929年7、9、10、11月相繼公布了《縣保衛團法》《清鄉條例》《鄰又連坐暫行辦法》《清查戶口暫行辦法》,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辦理保甲制,但“所有保甲制度的精神,均經分別納入。”只是由于地方自治方興未艾,保甲制并未得到真正推行。在南京國民政府“圍剿”工農紅軍過程中,保甲制才得以沉渣泛起。1931年6月,蔣介石命令先在江西修水等地編組保甲,1932年8月,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發布《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施行保甲訓令》,提出“以保甲作為地方組織之骨干也。”
1934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通知各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在廣大農村中實行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采取聯保連坐,同時“納保甲于自治組織之中,以保甲代替閭鄰,以鄉鎮代替聯保。”此后各省相繼推行保甲。1936年,國民黨中央地方自治計劃委員會通過《地方自治法規原則》,再次提出將保甲容納于自治組織之中,鄉鎮內的編制為保甲。實際上地方自治事務在1932年以后就已逐步停止,1932年,《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施行保甲訓令》頒行后,地方自治在“剿匪省份皆已停止”,此后其他各省在南京國民政府“納保甲于自治組織之中”的指令下,地方自治事實上日益被保甲取代。保甲制的推行建構了組織嚴密的縣以下的鄉村權力脈絡,是南京國民政府“利用嚴密的‘軍事部勒的方式控制廣大農村社會。”
保甲制與地方自治精神上是完全不相容的,首先,保甲制度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殘余,是一種編民制度,其目的在于用聯保切結等方式來控制民眾,而地方自治是過程中實現民眾的基本民權,二者截然不同;其次,保甲制是自上而下構建的,是由政府任免保甲長來實現保甲制的完善,保長、甲長作為政府的耳目監視民眾,自治體系規定閭長、鄰長均由選舉產生;再次,自治的基礎單位是個人,而保甲是以戶為基本單位。將保甲納人自治之中,“一方面表示保甲制度與當時環境之下的需要,他方面也可以象征著地方自治的沒落!”在當時就有人對保甲容納于自治組織之中有不同看法:“保甲的性質、運用、組織根本上與自治都不相同……保甲在性質上說,完全為政府行政機關之一部,只能在政府指揮命令之下,執行其所應為的職務。”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也承認:“保甲制度之本身,與現行自治制度,不無抵觸。”但在南京國民政府構建集權專制體制的客觀要求下,保甲制得以迅速發展。
在國家權力重構視角下考察,保甲制與現代民主政治毫無關聯,是南京國民政府從中國傳統政治資源中提取的控制廣大農村社會、構建基層權力脈絡的有效載體,伴隨著南京國民政府集權專制的確立,與集權專制相契合的保甲制得以大行其道成為專制集權的基礎。這種契合,一是表現在南京國民政府“圍剿”工農紅軍過程中保甲制的作用,即以連坐法使得“剿匪”區的居民互相監視,阻絕廣大人民群眾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系;二是保甲制有助于南京國民政府自上而下建立專制統治、構建鄉村權力脈絡,由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地方自治的實施困境,縣以下的自治機構難以建成,這也造成南京國民政府在縣以下的廣大區域內缺乏行之有效的權力體系,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管理缺乏有效保障。保甲制的推行從上自下迅速的構建了縣以下的行政體系,是在中國傳統政治資源基礎上農村政權體系的重構,滿足了南京國民政府對農村社會嚴密控制的要求。保甲制被認為是“維持社會治安的根本辦法”,同時又能適應“社會現實情況和急切需要”,也反映出南京國民政府國家權力重構的方向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與此截然相反的專制集權統治。
四、新縣制:南京國民政府國家權力重構路徑的鞏固與調整
1937年抗戰爆發后,南京國民政府以戰時需要為借口,進一步加強了一黨專政集權體制,權力結構向一元化發展,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權力運行體制,“中日戰爭的民族斗爭,不過是為其提供了一個強化一黨專政和個人集權的新借口。這一理念在戰爭狀態下繼續強化,遂成為戰時及戰后國民黨政治理念的中心價值觀之一。”在此過程中,蔣介石強化了個人獨裁的地位,一方面在法統上成為國民黨領袖,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建立領袖制度,中央黨部應在制度上明確規定全黨之領袖。”蔣介石被推舉為國民黨總裁,代行總理之職權;另一方面,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政府機構設置上,將個人集權專制制度化,1937年8月,國防最高會議取代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為最高決策機構,1939年1月,國防最高委員會取代國防最高會議,同時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掌控黨、政、軍全權,實現了其個人集權的目標。對于契合專制統治的保甲制,南京國民政府不斷予以強化,1939年新縣制的提出,正是這種強化的結果。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始終無法繞過孫中山政治思想中對地方自治的要求,針對保甲代替自治的非議,新縣制也不得不從表面上與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構建聯系,即融保甲于自治之中,表面上仍打著地方自治的旗號。因此,新縣制既是南京國民政府鞏固集權專制體制的基礎,同時也是南京國民政府國家權力重構路徑的一種調整。
1939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宣布凡與《縣各級組織綱要》相抵觸的法令一律停止,開始實行新縣制。《縣各級組織綱要》從法律層面摒棄了1929年《縣組織法》中規劃的區鄉(鎮)閭鄰制,正式將保甲融人地方自治之中。蔣介石聲稱,新縣制根本精神在于“喚起民眾,發動民力,加強地方組織,促進地方自治事業,以此奠定革命建國的基礎。”對于新縣制的實施,南京國民政府宣稱實現了地方自治與保甲的融合,“求統一于彈性之中,寓理想于現實之中。”當時社會上也有人為保甲于自治之中辯護,認為此保甲已非彼保甲,性質完全改變,“雖襲用保甲的名稱,但實質上已大大改變……而是人民自下而上的自治組織內部的機構。”“今保甲制度,已由民眾之軍事組織,進而為國家內政之設施,再進而為社會事業經濟建設運用之樞紐。”“就理論上說,保甲制度就是自治,并不是什么封建社會的殘余……說保甲不是自治,未知有何根據,徹底地說,他國所謂自治,系以個人為單位,保甲系以家庭為單位,更適合于國情。”實際上,新縣制是對此前地方自治與保甲實施的系統總結,保甲制僅是添加了若干現代元素,其主要的功能沒有改變,蔣介石在新縣制推行時強調:“辦理保甲,要想徹底收效,必須采用連坐法之精神。”
在新縣制中保甲制得到一定的強化,保長兼任保國民學校校長、保壯丁隊隊長,形成“保長之擔任國民學校校長及壯丁隊隊長之三位一體辦法。”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對于鄉鎮、保甲等基層人員進行培訓,加強控制,“鄉鎮長、干事及中心學校教員須入地方行政干部訓練團受訓或入各區訓練班受訓,保長及國民學校教員須入各區訓練班或各縣訓練班受訓,而且在受訓之后,無保留地用集體方式加入國民黨。”新縣制標榜以保甲作為地方自治的基礎,實際上“新縣制中之保甲,其性能已與往日的不同,要言之,就是它既非自衛組織,亦非地方自治團體,它是一種臨時的官治機構。”保甲長“農不暇當,紳士不愿當,而有廉恥心的人又不肯當,勢必只有地痞流氓、土豪劣紳、無業游民,無賴市儈來干”也正因為此,保甲長成為腐敗的溫床,蔣介石對保甲弊病深有體會:“我們考察現在一般鄉鎮長和保甲長普遍易犯的弊病約有下列四端:第一、就是假公濟私,營私舞弊……第二、就是倚勢招搖,壓迫民眾……第三、假藉鄉鎮長保甲長的名義報復私仇……第四、一般鄉鎮長和保甲長往往操一鄉一鎮執行政令之權,……可以憑借機會勒索窮戶!”但即使如此,保甲作為構成南京國民政府基層政權體系重要一環,并得以不斷固化,并且被賦予了更多職責,1939年12月,國民黨中央提出《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甚至將保甲制視為維持國民黨專制統治,防范、限制中國共產黨的工具,“保甲內應盡量發展本黨組織,保甲長除非常時期保甲長選用辦法選用外,并應以本黨黨員充任為原則,未入黨者,設法介紹其入黨。”
“保甲的基礎是建立在戶長的上面,亦即建立在家長的上面,這和舊式代表封建政治的保甲制度,并沒有本質的差別。”“所謂公民卻依然無行使四權的機會。”以此為基礎的新縣制背離了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真正地方自治的實現是沒有希望的。”保甲制度的固化也造成南京國民政府更多地表現出保守專制的特征,與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南轅北轍,借此達到民權、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新縣制強化了以保甲為基礎的鄉村權力網絡,利用保甲加強廣大農村的強力控制并以此為基礎,強化蔣介石個人獨裁的集權體制,才是南京國民政府真正追求的目的,也正因為此,一直到南京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終結,也沒有一個縣是達到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地方自治要求。
五、結論
近代中國的國家權力日漸衰微,內無法維持統治,外無以御敵,中國開始了國家權力重構的征程。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面臨著國家權力重構的客觀要求,但在國家權力重構的方向上背離了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也正因為此,以孫中山思想為指導的地方自治推行,被南京國民政府視為在鞏固政權合法性的一個必要手段,卻并不被認為是國家權力重構的路徑選擇,崇尚民權的自治與南京國民政府政府專制集權方向相違背而歸于失敗。保甲制作為與集權主義、專制主義相契合的有效工具,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大行其道,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始終無法在理論層面繞開孫中山政治思想,保甲制與地方自治精神上的不相容最終結果,是在自治旗幟下實行保甲制,對地方自治的外在形式進行若干移植,但在核心層面上以傳統的保甲制來推動集權專制體制的確立,體現了南京國民政府在國家權力重構方向上延續了傳統專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