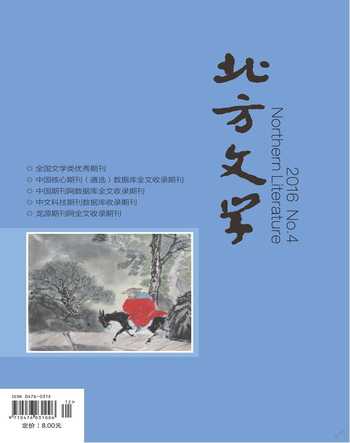黑暗中的影子
范紓宇
黑暗中一群人在沒命的狂奔。
凄冷的月光,冷酷的映襯著這個生機勃勃的大地,冷風瑟瑟地起了。黑夜中的漆黑,總有別樣的驚喜,烏鴉的哀鳴和蝙蝠的喜悅,給這群狂奔的人打上了節奏。
喘著大氣,汗水涔涔地往下涌,他們累了,決定停留下來。
“哧”的一聲,刺眼的光亮在小小的火柴上被無限的放大,搖晃著一群彎曲的影子。周圍有了亮光,疲于奔跑的人開始有了閑話。
甲抖了抖自己破爛不堪“拼圖”式的確良大衣,撇了撇嘴。“房租又漲了,隔壁的房東來我家催債比鬧鐘還準時,十三平米住七口人,操他媽的多子多福。要不是政府拆遷價格太低,我能不搬?誰想在這里寄人籬下活受罪!”他狠狠地跺腳仿佛要把自己的心臟震碎。
乙接過話茬,油光滿面地發起了牢騷。“老子的工資好幾年沒有漲了,狗日的房地產商坑害了我,多少個日夜沒陪家里人,全泡在這混賬事里了”他瞥了一眼,眨巴著淚,開始了小聲的嗚咽,“一起出來打拼的兄弟呵,哥哥我沒能力,栽在了萬惡的資本家手里”。銀白色的月光拍打在他的側臉上,亮锃锃的讓人張不開眼。
微弱的焰火搖曳了一下,丙的香煙已經緩緩地冒出顏色。他彈了下煙灰,說道:“都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家簡直就是一個藏經閣。柴米油鹽,都是嘴一張一閉的活兒。”他打趣似的自嘲,又似自言自語地呢儂,“昧著良心做人,呸,不在少數!公正、法治、民主,呵,都他媽是資本家的玩意,有錢時屁顛屁顛,沒錢時像狗一樣。”煙圈吐出來幽深得像口洞,煙草被他嚼的吧嗒吧嗒作響。
一口痰狠狠的砸在了地上,丁總給人一種威嚴的既視感。“大學時,我何曾不向往一個正義的社會,除暴安良,為民請愿。但一口池塘里生活久了,水就會變質,污水里長大的白條,肚子里也有一層黑黢黢的。哪怕你不想,但周遭的環境又怎能容得下你?”他深情的望著遠方,乞求著同情,但除了鄙夷的月光,卻似乎再也沒有人注意他。
烏鴉在枝椏上狡黠的冷笑,火柴燃滅了,連彎曲的影子都沒了。一群人又開始沒命的狂奔,似乎從來沒有剛才的談話。
月光連著黑暗被世界驅逐,留下了文明社會。
妻子給甲準備了熨燙得筆直的西裝,今天有他最重要的語文公開課,講解傳統的儒學大義,聽課的領導都是重量級的人物。出門前,妻子還拉著他的衣角提醒,“那本精裝的論語盒子里裝著一萬元,別忘了給文教局管分房的劉主任。”
看著窗外的鋼筋水泥,乙伸了伸懶腰,在旋轉椅上慢慢品著咖啡。但十分鐘前他的眉毛氣得像張大字報,一個水泥工人才因為兩個月工資沒拿到手,竟然爬到大廈頂層拉橫幅,一個踉蹌跌落致死。他氣憤地錘打著桌面,這對公司的聲譽該造成多不好的影響呀!十分鐘后,一個貼有“愛心補償金一萬元”的牛皮袋從桑塔納轎車上砸了下來,一個母親正帶著三個孩子在滿是污垢的水池邊擇菜。
丙整理好了文件袋,今天他要為一個山西巨貪出庭辯護。作為中國最高等法學學府畢業的高材生,他在讀書期間就已洞察出法律中的諸多漏洞,現在,這些都成了他揚名立萬的資本。最喜歡的不是正面迎擊法律,而是繞一圈在法律背后捅白刀子。
朝五晚九的生活使得丁越來越厭倦,他現在除了抽煙就是喝酒,且非中華不抽,非茅臺不喝。房地產商前兩天送了一包二十萬的“煙”,他笑嘻嘻的收下,文件上的紅章莊嚴地把拆遷款壓了又壓,土地都給了送禮的人。清池自凈一張嘴,濁水渾來名利得。在同僚中低調地炫耀,成了酒桌上的舊事。
影子只能在夢中,狂奔也只能沉寂。
但黑夜每天都會到來。
誰還管那凄冷的月光,不過是無知者的自作多情。那黑暗中的狂奔,是夢中的影子,可誰又會去在意呢?
甲乙丙丁,反正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