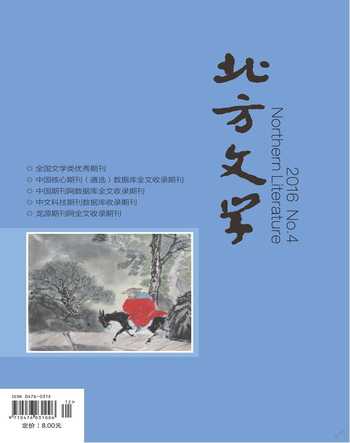解讀“雷雨”的化身——繁漪
楊亞楠
摘 要: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曹禺是一位以悲劇著稱的劇作家,在其眾多悲劇創(chuàng)作中尤以女性的刻畫最為深入人心,較為突出的有《雷雨》中敢愛敢恨的繁漪,《日出》里在清醒中墮落的的陳白露,《原野》中充滿原始蠻性的花金子以及《北京人》中具有驚人的愛心與耐力的愫方等。在這些人物的身上,滲透著作者強(qiáng)烈的情感。本文主要以《雷雨》為例,探析劇中繁漪這一悲劇女性形象。
關(guān)鍵詞:曹禺;雷雨;悲劇;繁漪
悲劇是悲痛的藝術(shù),它表現(xiàn)出一種特殊的審美情感。在我國(guó)古代的詩歌中常常強(qiáng)調(diào)以“悲”為美,草木凋零的蕭索之悲;物是人非的變遷之悲;閨中怨婦的凄婉之悲;血染沙場(chǎng)的雄壯之悲……雪萊曾說:“我們最甜美的歌就是那些傾訴哀腸的思想的。”曹禺的悲劇美學(xué)正是通過他筆下的女性形象,以她們各具特色的女性美,來訴說她們內(nèi)心的痛苦和不幸;又從陰鷙低沉的生活中綻放出生命的色彩,展示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悲劇畫面。曹禺以美的靈魂在深刻的痛苦中毀滅,從而產(chǎn)生了巨大的悲劇藝術(shù)魅力。魯迅曾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jià)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1]使人為美的撕裂而激起感情的激蕩。所以,悲劇常常與美、崇高聯(lián)系在一起。
《雷雨》是曹禺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戲劇,它也標(biāo)志著中國(guó)現(xiàn)代話劇的成熟。曹禺在《雷雨序》里,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殘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樣呼號(hào)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2]《雷雨》所體現(xiàn)的,正是“宇宙中斗爭(zhēng)的‘殘忍與‘冷酷”。“在《雷雨》里的八個(gè)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繁漪”。[3]作為劇中的靈魂人物,繁漪被稱為《雷雨》中“最為炫目的一道閃電”。[4]在曹禺的筆下,繁漪敢愛敢恨,大膽的追求自己的愛情,面對(duì)周萍的背叛,發(fā)出“我沒有孩子,我沒有丈夫,我沒有家,我什么都沒有,我只要你說——我是你的!”的吶喊。這是人被逼到走投無路時(shí),所做的最后掙扎,但是這種掙扎是毫無意義的。她把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周萍,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畸形的,況且周萍并沒有真正愛過繁漪。最后被逼上絕路的繁漪,為了愛,把自己連她周圍的一切都?xì)缌恕?梢钥闯觯变羯砩狭魈手环N難以言喻的“原始的情緒”:不是愛便是恨。在她的身上,“一切都走向了極端,中間不允許有一條折衷的路。”[5]這也是曹禺戲劇中女性形象的一個(gè)共性:充滿“蠻力”與“原始情緒”。這與作家本人的人生閱歷和情感體驗(yàn)有關(guān)。曹禺早年的生活經(jīng)歷十分不幸,他剛生下來三天,母親就去世了,父親是一個(gè)潦倒的封建官僚,脾氣暴躁,在家里經(jīng)常發(fā)火大吵大鬧,整個(gè)家庭氣氛極其壓抑沉悶。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使得曹禺自幼敏感、多疑、處處謹(jǐn)慎小心,同時(shí)又感到非常孤獨(dú)寂寞。成年以后的曹禺依然這樣,不愛講話,耽于幻想,對(duì)外界的評(píng)論特別敏感。新中國(guó)成立后,曹禺的名聲地位高了,卻更加在意別人的評(píng)論,尤其重視領(lǐng)導(dǎo)對(duì)自己的看法與態(tài)度。戲劇創(chuàng)作上的自信心衰減了,寫戲更多是為了配合形式或完成領(lǐng)導(dǎo)交代的任務(wù)。1983年,黃永玉先生與曹禺有過通信,其中一封黃永玉對(duì)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評(píng),他說:“你是我極其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duì)你要嚴(yán),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一個(gè)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里,你為勢(shì)位所誤,從一個(gè)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可見曹禺的自我保護(hù)意識(shí)很強(qiáng)。一個(gè)天性脆弱的知識(shí)分子,卻在《雷雨》、《原野》、《北京人》中一再禮贊“蠻性”的原始力量。這也許就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常見的所謂補(bǔ)償心理。曹禺之所以特別向往“蠻力”,正是出于他自身的心理缺陷。
劇中的繁漪,厭倦了周家單調(diào)庸俗的生活,難以忍受陰沉壓抑的氣氛,加之精神上的苦悶,得不到周樸園的理解和關(guān)愛,所有痛苦的潮水一齊向她涌來,她力求擺脫這一切。可是不管她怎樣掙扎都難以擺脫這“黑暗的坑”,只會(huì)越陷越深。于是就有了“掙扎”與“殘酷”的發(fā)現(xiàn)。曹禺說:“這堆在下面蠕動(dòng)著的生物,他們?cè)鯓用つ康貭?zhēng)執(zhí)著,泥鰍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著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6]他們一個(gè)抓住一個(gè),揪成一團(tuán),“正如跌在沼澤里的羸馬,愈掙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7]所以他說:“在《雷雨》里,宇宙正向一口殘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樣呼號(hào)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
關(guān)于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發(fā)現(xiàn),在魯迅在《阿Q正傳》中早有察覺。阿Q作為一個(gè)“個(gè)體生命”的存在,幾乎面臨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滿足的生的困惱、無家可歸的惶惑、面對(duì)死亡的恐懼等,為擺脫絕望的生存環(huán)境而做出的“精神勝利”的選擇,卻使人墜入更加絕望的深淵,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遠(yuǎn)不能擺脫的。這里,曹禺是對(duì)生存困境這一現(xiàn)狀的重新闡釋和另辟蹊徑。既包含了對(duì)人無論是怎樣掙扎終不免失敗的生存狀態(tài)的發(fā)現(xiàn),同時(shí)又表明了,作者對(duì)宇宙間壓抑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種不可知的力量的無名的恐懼。
《雷雨》自上映以來,繁漪一直是個(gè)頗具爭(zhēng)議人物。她美艷動(dòng)人,性格上有自私、陰鷙的一面。為了愛情,她可以不擇手段地阻撓周萍與四鳳的感情,甚至不顧顏面、悄悄地跟蹤周萍。為了愛她可以 “如一個(gè)餓了三天的狗咬著它最喜歡的骨頭”。但是當(dāng)她的愛不能實(shí)現(xiàn)時(shí),她的恨同樣也是讓人很可怕的,她可以“不聲不響的恨恨地吃了你”。終于因?yàn)樗那楦斜l(fā),周樸園想要建立的“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家庭。”[8]崩潰了。繁漪對(duì)壓迫的反抗、對(duì)自由意志的追求,是出于她身上的原始的蠻性,是完全不考慮后果的。沈從文曾說:“人被壓迫了,自然要反抗,可是若只有反抗而殊乏溫情,或者說沒有愛意的反抗,也應(yīng)該是一種缺乏。”相比之下,繁漪的愛與恨都太過殘忍。她對(duì)周萍的愛并沒有出現(xiàn)高于情欲的個(gè)性要求,從她對(duì)周萍的過分依賴與執(zhí)著,可以看出她個(gè)性的喪失。
其次,繁漪雖然在心理上排斥周公館,但她并未做出任何實(shí)際行動(dòng),如像娜拉那樣掌握自己的命運(yùn),沖出封建舊家庭、追求個(gè)性的獨(dú)立與解放。即便是繁漪像娜拉一樣走出家門,又如何?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中,告誡學(xué)生,娜拉走了以后,“實(shí)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雖然精神層面擺脫了封建藩籬的束縛,但婦女的解放首先要解決的是經(jīng)濟(jì)上的獨(dú)立。而事實(shí)上,繁漪對(duì)周公館是存在依賴的,在“張個(gè)人”方面,她遠(yuǎn)不如娜拉那樣堅(jiān)決和徹底。她只有在自己走投無路時(shí),才有摧毀一切的盲目反抗,將一切有罪的、無辜的人燃燒在她憤怒的烈火中,將他們化為灰燼。在她的身上,交織著人類“最不忍的愛和最不忍的恨”。這樣看來,繁漪的形象更接近于古希臘悲劇中報(bào)復(fù)一切的美狄亞,為了復(fù)仇不惜一切代價(jià),甚至是犧牲自己。
另外,繁漪明知道周沖喜歡四鳳,卻對(duì)兒子的選擇橫加干涉,提醒周沖說:“她始終是個(gè)沒受過教育的下等人。”[9]并決然地說:“我的兒子要娶,也不能娶她。”繁漪對(duì)四鳳的偏見,顯然不是出于對(duì)四鳳的憎恨,因?yàn)橹軟_與四鳳相愛對(duì)她是有利的。這恰恰反映了繁漪的封建等級(jí)觀念、門第思想。繁漪自己就是封建婚姻的不幸犧牲品,但她仍舊以門當(dāng)戶對(duì)的封建標(biāo)準(zhǔn)干涉周沖的婚姻。因此,在繁漪身上并未完全表現(xiàn)出“反封建個(gè)性解放的主題”。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對(duì)她的思想和行為依然有著深刻的影響,使她的意識(shí)深層,還潛伏著某些軟弱、妥協(xié)的因素,她在潛意識(shí)中仍然備受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束縛。這也是繁漪區(qū)別于西方悲劇中的女性性格,而呈現(xiàn)出民族悲劇美學(xué)內(nèi)涵的獨(dú)特之處。
曹禺在塑造戲劇中的女性時(shí),著重發(fā)掘她們精神的痛苦。她們對(duì)自身的痛苦是清醒地感覺和意識(shí)到的,她們的心靈在痛苦中掙扎,都想擺脫這痛苦和不幸,卻絕望地發(fā)現(xiàn)自己無路可走。他們清醒的靈魂最終只能掉進(jìn)痛苦的巨大深淵。所以有人說:“曹禺的悲劇是用心靈的淚水匯成的一片痛苦的海洋。”
參考文獻(xiàn):
[1]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雨絲》周刊第15期,第26頁。
[2]曹禺:《雷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4:120.
[3]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4.
[4]錢理群:《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名篇十五講》,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210.
[5]錢谷融:《雷雨人物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117.
[6]《〈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88:213.
[7]《〈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88:213.
[8]朱棟霖:《論曹禺的戲劇創(chuàng)作》,北京: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6:12.
[9]錢理群.《大小舞臺(tái)之間—— 曹禺戲劇新論》[M].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