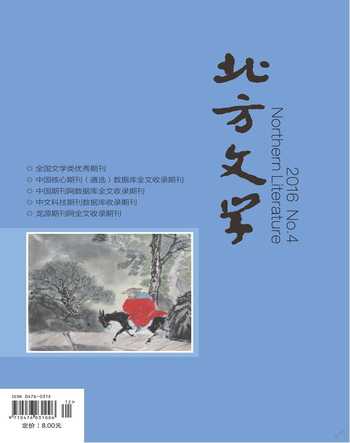在現(xiàn)實(shí)與烏托邦的交匯處
彭云濤
摘 要:勒克萊齊奧的《烏拉尼亞》中存在著眾多鮮有人關(guān)注的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本文借助結(jié)構(gòu)主義文論的觀點(diǎn),從坎波斯和朗波里奧兩個(gè)地域之間的對(duì)立談起,再?gòu)奈谋局型诰虍愘|(zhì)文明激蕩、人與自然沖突的深層含義,最后,圍繞“我”串聯(lián)起極具象征意義的三個(gè)人物形象,從而深化對(duì)文本整體性象征意義的理解,啟迪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方向。
關(guān)鍵詞:結(jié)構(gòu)主義;《烏拉尼亞》;二元對(duì)立;深層意義;象征隱喻
法國(guó)作家勒克萊齊奧于2006年出版的小說(shuō)《烏拉尼亞》一經(jīng)問(wèn)世旋即受到極大的關(guān)注,中國(guó)官方也美譽(yù)它為“二十一世紀(jì)年度最佳外國(guó)小說(shuō)”。它講述了這樣的故事:一位法國(guó)地理學(xué)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時(shí),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烏托邦式的理想王國(guó)——“坎波斯”,這里的居民都是來(lái)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他們生活簡(jiǎn)單自由、心地善良淳樸,但隨著殖民者對(duì)經(jīng)濟(jì)利益的狂熱追逐,這個(gè)遺世獨(dú)立的理想王國(guó)在人類社會(huì)的圍攻中不斷遭擠壓,最終被迫遷徙,雖“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時(shí)”能重建家園,每個(gè)人卻都心存“天堂”的信仰。
有論者質(zhì)疑這種烏托邦社會(huì)存在的可能性,批判其語(yǔ)言平淡、情節(jié)零散、題材小氣,也有論者盛贊其為心靈空虛落寞的現(xiàn)代人提供了一個(gè)精神的庇護(hù)所,稱其結(jié)構(gòu)新穎、人物充實(shí)、詩(shī)意盎然……本文筆者則力圖從結(jié)構(gòu)主義角度重新梳理小說(shuō)中繁多的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極其蘊(yùn)含著的豐富隱喻,從而深化對(duì)文本深層內(nèi)涵的理解,啟迪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方向。
一、坎波斯與朗波里奧:表層結(jié)構(gòu)中的兩地對(duì)話敘事
在結(jié)構(gòu)主義看來(lái),敘事是對(duì)現(xiàn)象的描述或者與現(xiàn)象產(chǎn)生某種聯(lián)系,它是對(duì)意義的編織和構(gòu)建,作者選擇的敘事方式與其所要傳達(dá)的思想必然具有某種聯(lián)系。從整體上看,勒克萊齊奧有意學(xué)習(xí)墨西哥歷史學(xué)家路易斯·貢扎拉孜的前一章的末尾作為下一章的題目及開頭寫作方法,這種敘事形式突出了全書的連貫性、激發(fā)讀者向后閱讀的興趣,同時(shí),該形式與故事內(nèi)容也相一致,因?yàn)楣适卤旧淼慕Y(jié)尾就是開放的。從敘事視角來(lái)看,作者以“我”(達(dá)尼埃爾)的視角展開敘事,其間穿插與拉法埃爾、馬爾丹的書信,由此展開朗波里奧和坎波斯兩地之間富有張力的對(duì)話敘事。
“烏拉尼亞”一詞來(lái)自于古希臘神話,原意是“天文女神”,這里將其引申為“天上的國(guó)度”,“坎波斯”即是這樣一個(gè)地上的天國(guó),關(guān)于坎波斯的敘述,主要來(lái)自“我”在旅行途中結(jié)識(shí)的“最奇怪的年輕人”——拉法埃爾,他出身在魁北克的狼河,隨父親來(lái)到坎波斯,而坎波斯有個(gè)習(xí)俗,即男女長(zhǎng)大就得離開村子,拉法埃爾想看海,便離開坎波斯去尋找海了,后來(lái),錢花完了又重返坎波斯。拉法埃爾這一敘事視角的介入,空間上,不僅可以深入坎波斯的內(nèi)部,切身了解并描述這個(gè)地上天國(guó)簡(jiǎn)單美好的日常生活,而且拉法埃爾作為一個(gè)外來(lái)者又可以站到坎波斯的外圍,用一個(gè)旁觀者的眼光去觀察和打探坎波斯與自己曾經(jīng)生活過(guò)的狼河之間的差異;時(shí)間上,拉法埃爾從長(zhǎng)者那里得知坎波斯的由來(lái),在書信、筆記中為“我”講述其親歷的祥和生活,看海歸來(lái)后他又目睹坎波斯被占領(lǐng)、居民被迫遷徙的慘景,因而,拉法埃爾是坎波斯由盛而衰的見證者,采取這一視角使得敘事更加客觀真實(shí)、細(xì)致全面。實(shí)際上,拉法埃爾自己就是一個(gè)鮮活的“坎波斯”,他熱愛(ài)生活、熱愛(ài)自由,對(duì)萬(wàn)事萬(wàn)物充滿好奇和興致。他的這種特質(zhì)又為“我”提供了最為直接生動(dòng)的感受,它們與“我”童年的記憶融合,更深刻地引發(fā)了“我”強(qiáng)烈的共鳴和對(duì)現(xiàn)狀的反思。朗波里奧的敘述則主要以“我”為主體,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我”作為一個(gè)還保有良知和天真的外來(lái)研究員,不僅觀察著科學(xué)家、銀行家等人虛偽、墮落、腐化的生活,體會(huì)著朗波里奧的孕育、變化和擴(kuò)張,同時(shí)也介入其間,控訴當(dāng)局對(duì)像莉莉這樣的社會(huì)邊緣人的擠壓,在土壤學(xué)的演講中呼吁人們應(yīng)像愛(ài)護(hù)自己的皮膚一樣愛(ài)護(hù)土壤……第一人稱敘事與第三人稱直接敘事交替使用,展開兩地差異性對(duì)話敘事的同時(shí)也傳達(dá)出作者的態(tài)度,啟迪讀者做出反思和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敘事視角下,勒克萊齊奧選用了不同的敘事時(shí)間觀。持續(xù)進(jìn)步、無(wú)限發(fā)展,注重未來(lái)的線性時(shí)間觀為現(xiàn)代社會(huì)所取信和偏愛(ài),這也是理解現(xiàn)代性的基礎(chǔ)和核心,它在朗波里奧的發(fā)展、擴(kuò)大以及吞并中有很好的體現(xiàn):一開始革命者將這里的人全部殺害,把尸體埋到一片田里,之后零零星星的科學(xué)家入住到此,他們對(duì)朗波里奧進(jìn)行了一番甚囂塵上的改天換地,以至于最后阿朗薩斯將貧瘠不堪的坎波斯也納入囊中,可謂是步步為營(yíng)。而古老的文明常倡導(dǎo)一種退化時(shí)間觀,它認(rèn)為最好的時(shí)代永遠(yuǎn)都在過(guò)去的時(shí)光里,這個(gè)世界是退化的而不是向前發(fā)展的,坎波斯即是一例。最初世外桃源般簡(jiǎn)樸單純的生活模式吸引了來(lái)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后來(lái),外來(lái)殖民勢(shì)力慢慢滲入,與世無(wú)爭(zhēng)的價(jià)值選擇已經(jīng)難以維系,最后被迫四散天涯,悲涼之音響徹耳際。這種退化時(shí)間觀反應(yīng)在個(gè)人身上就體現(xiàn)為一種返回童年的渴望,這即是賈迪所說(shuō)的“要學(xué)會(huì)做人,我們首先都得學(xué)習(xí)怎樣做孩子。”
二、現(xiàn)代文明與古老傳統(tǒng):深層結(jié)構(gòu)下的異質(zhì)文明激蕩
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認(rèn)為任何一部文藝作品都存在外結(jié)構(gòu)和內(nèi)結(jié)構(gòu)兩個(gè)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主義不僅僅要看到事物的表面現(xiàn)象,更要把握和分析表層結(jié)構(gòu)之下的深層內(nèi)涵,由此才能更清晰深刻地理解文藝作品所傳達(dá)的思想與情感。以坎波斯和朗波里奧為代表呈現(xiàn)出的地域差異,除了影射現(xiàn)代人與傳統(tǒng)人觀念的差異,更凸顯出異質(zhì)文明的沖突,是現(xiàn)代文明與古老傳統(tǒng)的對(duì)峙,也是人與自然的深刻矛盾。
關(guān)于教育。可以說(shuō),坎波斯到處都是學(xué)校,無(wú)論何時(shí)何地,人與人互相學(xué)習(xí)、請(qǐng)教,是彼此的老師。上課就是聊天、聽故事、做夢(mèng)、看云。在坎波斯人看來(lái),重要的不是記憶連篇累牘的知識(shí)來(lái)裝點(diǎn)自己,正如賈迪所言:“你需要的不是知識(shí),恰恰相反,是遺忘”,因?yàn)橐磺械挠洃浂疾粦?yīng)以記憶為目的,而應(yīng)融化知識(shí)、指引人們?cè)娨獾厣睢,F(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是建基在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突飛猛進(jìn)之上的,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又集中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教育體制之中。居于山岡上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知識(shí)分子們,他們接受的都是課堂上的教育,以將象牙塔里的學(xué)問(wèn)換得專業(yè)雜志上的幾篇文章或者參考文獻(xiàn)中的一條索引為傲。來(lái)到朗波里奧的他們更是將知識(shí)視為一種權(quán)力和獲得財(cái)富的手段,他們不顧當(dāng)?shù)鼐用竦陌参#O(shè)立研究所,大肆投資房產(chǎn)、興建工廠,弄得民不聊生。事實(shí)上,錯(cuò)誤不在現(xiàn)代教育內(nèi)容本身,而是這種教育方式切斷了人與自然的親密聯(lián)系,為人類中心主義的膨脹提供了通途,現(xiàn)代教育體制所孕育的文明已然失卻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guān)系,而看似落后的古老傳統(tǒng)卻蘊(yùn)含著強(qiáng)大的平衡力,它不僅維系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guān)系,更保護(hù)著每一個(gè)人內(nèi)心的和諧。
在對(duì)待女性的態(tài)度上,兩種文明也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以坎波斯為代表的古老傳統(tǒng)保留著母系社會(huì)對(duì)女性地位的尊崇,年輕、美麗的奧蒂成為引領(lǐng)這個(gè)彩虹民族前進(jìn)的美好象征,她給拉法埃爾的性啟蒙更顯現(xiàn)了母性之愛(ài)的無(wú)私與博大。隨著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男性在社會(huì)中日益居于主導(dǎo)地位,他們憑借自己的力量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財(cái)富,睥睨萬(wàn)物,這使他們將女性視為私有財(cái)產(chǎn)抑或是發(fā)泄性欲的工具。以加爾西為代表的人類學(xué)家們,打著研究紅燈區(qū)的名義,傷害單純質(zhì)樸的姑娘們,小說(shuō)諷刺到:“那不過(guò)是一個(gè)把包括純科學(xué)在內(nèi)的一切都當(dāng)作權(quán)力追求方式的團(tuán)隊(duì)成員所制造的不值一提的搞笑事件中的一個(gè)小變奏而已。”最后,他們?yōu)榱司S護(hù)虛偽的體面終于將這些無(wú)辜的姑娘趕盡殺絕!
在勒克萊齊奧筆下,土是居于自然元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這部小說(shuō)中也不例外。作為地理學(xué)家的“我”,在一次演講中通過(guò)追溯土地的誕生,反觀現(xiàn)代文明對(duì)土壤的大肆破壞,朗波里奧一座座新興工廠的繁榮是以人與自然的失衡為代價(jià)的,“他們的錢是從黑土地里,從孩子被草莓酸腐蝕到流血,腐蝕到指甲脫落的幼小的手指的疼痛中榨取的”,一棟棟光鮮亮麗建筑的背后隱藏著散發(fā)陣陣惡臭的垃圾山……已然談不上什么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更不用提對(duì)自然的敬畏之心了。坎波斯卻不同,盡管土地貧瘠、資源匱乏,這里的居民仍互相扶持、辛勤耕耘。晴朗的夜晚大家最愛(ài)的便是一起躺在溫潤(rùn)如母親懷抱的土地上欣賞閃爍的星群以及水一樣的夜色,人、土地、天空渾然一體。拉法埃爾寫道“對(duì)于所有在大地上生活的——不僅是在大地上生活,對(duì)于所有生命來(lái)說(shuō)——天空是一種補(bǔ)償”,可見,在這個(gè)古老文明中自然與人不僅和諧共生,甚至作為對(duì)人的回報(bào),自然還啟迪著人的精神向更高遠(yuǎn)的地方進(jìn)發(fā)。有趣的是,坎波斯人盡管熱愛(ài)著故土,在他們成年后卻被要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體驗(yàn)不同的生活,他們的世界早已超越了腳下的方寸之地,而現(xiàn)代人卻恰恰相反,他們各自為政,看似日益占據(jù)更廣闊的土地,實(shí)則生存空間愈發(fā)狹窄,就如“我”與拉法埃爾第一次相遇時(shí)見到的旅店老板,他整日囿于旅店巴掌大的空間,舉著擠滿密密麻麻字符的報(bào)紙,這不正是現(xiàn)代人日常生活的一個(gè)縮影嗎?
三、象征性人物群像:整體視野下的主題升華
每部小說(shuō)都在告訴讀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復(fù)雜。”①事實(shí)上,將朗波里奧和坎波斯僅僅視為純粹的兩個(gè)地域和異質(zhì)文明的對(duì)峙還不夠。結(jié)構(gòu)主義重視整體性,即相對(duì)于部分而言整體具有邏輯優(yōu)先性。霍克斯說(shuō):“在任何情境里、一種因素的本質(zhì)就其本身而言是沒(méi)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事實(shí)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所決定。” 人物的功能不僅是由他與這個(gè)體系的其他功能部分的關(guān)系所決定,也與不同人物之間錯(cuò)綜的關(guān)系密切相連。為了更好地保持結(jié)構(gòu)的整體性,傳達(dá)復(fù)雜內(nèi)容,作者有意以“我”為基點(diǎn),聯(lián)系起其他人物(包括達(dá)莉婭、莉莉、奧蒂等),在串聯(lián)之中每個(gè)人又都各自具有象征意義,他們構(gòu)成一個(gè)意義的整體。正如有論者所言,《烏拉尼亞》的價(jià)值在于一次富有啟示意義的獨(dú)特歷程,在于其中所體現(xiàn)的人道主義、世界主義和大量豐富的隱喻。②作者將自己對(duì)世間真、善、美等普世價(jià)值的堅(jiān)定信仰寄寓到人物之中,從而使小說(shuō)擺脫現(xiàn)實(shí)主義一地雞毛的瑣碎敘事,達(dá)到凈化和升華主旨的作用。
對(duì)于一個(gè)內(nèi)心具有愛(ài)的能力的人來(lái)說(shuō),愛(ài)的不斷受挫是無(wú)法擊垮她堅(jiān)持愛(ài)下去的勇氣的,達(dá)莉婭即是這樣一個(gè)人,雖飽受欺騙、遍歷苦難,仍敢愛(ài)敢恨、無(wú)怨無(wú)悔,年輕時(shí),勇敢地投身革命,堅(jiān)定地為受害者和正義事業(yè)發(fā)聲,年邁時(shí),熱情洋溢、愛(ài)憎分明的性格特征愈發(fā)明顯,收養(yǎng)喪母的女孩,為女性維權(quán)排憂而樂(lè)此不疲……她的生命光芒四射。正是這束不變的光讓“我”對(duì)她的“愛(ài)”歷久彌新。達(dá)莉婭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真”這一普世價(jià)值,一路走來(lái)沒(méi)有悔恨、沒(méi)有憤懣,唯有沉實(shí)的心愿和堅(jiān)定地步伐。
在朗波里奧和坎波斯之間存在著一個(gè)不容忽視的特殊地域,即阿特拉斯花園,這是眾妓女的居住之處,姑娘們?yōu)槟切┧^的體面人提供服務(wù)以獲取微薄的收益,最后卻被他們以“凈化河谷風(fēng)氣,關(guān)閉‘可恥的花園”為由驅(qū)趕、迫害。莉莉也在受害者之列。第一次從研究員口中聽到對(duì)莉莉的褻瀆時(shí),她便成了“我”一生的牽掛,雖然“罪惡像臟水一樣從她身上流過(guò)”,卻沒(méi)有在她溫和、清香的身體上留下絲毫痕跡,“她的微笑,她那女人的身體和孩子的面龐,依然保留著她來(lái)自土地的芬芳。”她始終保持著善并相信著世間的善,當(dāng)“我”去探訪她時(shí),她不僅熱心以待,還在路人懷疑的眼光中保護(hù)著“我”以免受他人誤解。清澈、純凈的瀉湖容易被污染,唯有一顆善良的心永遠(yuǎn)明凈。莉莉的“善”是她在污濁世界里備受欺凌的原因,卻也神奇般地保護(hù)著她。
坎波斯的奧蒂是另一個(gè)重要的女性,她實(shí)實(shí)在在是“美”的象征。當(dāng)奧蒂覺(jué)察到拉法埃爾對(duì)自己的愛(ài)慕時(shí),她無(wú)私地給拉法埃爾以性啟蒙教育,在日后的生活中又落落大方,不給他任何心理壓力。因?yàn)椤皩?duì)她來(lái)說(shuō),愛(ài)不是獨(dú)占,不是悲劇。她說(shuō)愛(ài)是人每天都要經(jīng)歷的,它會(huì)改變,會(huì)轉(zhuǎn)移,會(huì)回歸。她說(shuō)一個(gè)人可以同時(shí)愛(ài)著幾個(gè)人,愛(ài)著一個(gè)男人,一個(gè)女人,甚至一只動(dòng)物或一株植物。她說(shuō)愛(ài)很簡(jiǎn)單,有時(shí)候沒(méi)有結(jié)果,愛(ài)是現(xiàn)實(shí)的,也是虛幻的,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當(dāng)坎波斯人被迫流亡時(shí),她擔(dān)起引領(lǐng)全族重尋家園的重任,途中還為賈迪舉辦喪禮,幫阿達(dá)拉接生……奧蒂美麗的容顏之下有著一顆更唯美的心,是這個(gè)彩虹民族名副其實(shí)的象征。
可以說(shuō),通過(guò)對(duì)這部小說(shuō)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的梳理以及對(duì)人物群像特殊象征意義的整體性思考,除了能明顯感受到作者對(duì)現(xiàn)代文明肆意擴(kuò)張的控訴、批判以及對(duì)淳樸善良的烏托邦文明的向往,更蘊(yùn)含著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方向的啟迪和祝愿。坎波斯的參事賈迪曾說(shuō):“沒(méi)有任何東西會(huì)永恒不變。只有星星永遠(yuǎn)還是那些星星。我們應(yīng)該做好出發(fā)的準(zhǔn)備。坎波斯不屬于我們,它不屬于任何人。”人類一直苦苦尋找的天堂不在一個(gè)遙不可及的遠(yuǎn)方,也不屬于任何人,人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gè)遙遠(yuǎn)的光點(diǎn),在奔向這個(gè)光點(diǎn)的時(shí)候,人們秉心斂性,反思自己,從而不斷完善自己。小說(shuō)以引用約翰·歐文的《烏拉農(nóng)·烏拉尼亞》為開篇,頗具啟發(fā)性:“萬(wàn)事震驚,心余平靜:/風(fēng)暴交錯(cuò)似無(wú)情,/雨后盼得彩云歸,一晌通明。”也許,對(duì)于這個(gè)彩虹民族來(lái)說(shuō),風(fēng)暴和波折看似無(wú)情,實(shí)則是對(duì)人堅(jiān)定信仰的考驗(yàn),坎波斯不僅僅是一片地域,更是心靈中一方永恒的凈土,風(fēng)雨過(guò)后必將重見彩虹。
注釋:
①[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shuō)的藝術(shù)》,董強(qiáng)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頁(yè)。
②高方、許鈞主編:《反叛、歷險(xiǎn)與超越——勒克萊齊奧在中國(guó)的理解與闡釋》,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法]勒克萊齊奧.烏拉尼亞[M].紫嫣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
[2][英]特倫斯·霍克斯.結(jié)構(gòu)主義和符號(hào)學(xué)[M].瞿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3] 高方、許鈞主編.反叛、歷險(xiǎn)與超越——勒克萊齊奧在中國(guó)的理解與闡釋[M].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
[4][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shuō)的藝術(shù)[M].董強(qiáng)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5] 趙小琪.結(jié)構(gòu)主義視野下白先勇〈臺(tái)北人〉新讀[J].貴州社會(huì)科學(xué),2009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