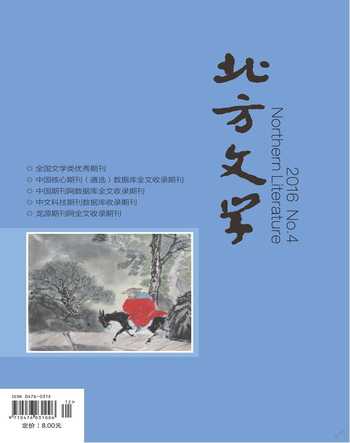淺析柳永夢詞
羅明秋
摘 要:柳永是北宋詞壇大家,在其160首詞中,出現“夢”字的詞有29首,占18.1%,比例相對較高,值得我們思考。論文解析了柳詞中“夢”意象本身所獨有的理想性、生活性、情感性、共情性、共通性等特質;認為柳永夢詞擴充了詞的表現內容與方式,增強了詞的情感表達的力度,擴大了其詞傳播群體,在中國夢文學史上應具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柳永;夢詞;意象
夢是人類自然的生理現象,在中國文學中,對于夢的表現,源遠流長。自《詩經》始便有《小雅·斯干》以夢占卜歲年吉兇,繼“莊生曉夢”借助夢境的虛幻力量擴大夢境對人生哲學的思考,“華胥夢”、“黃粱夢”等文學創作展現了更多的可能性,“夢”成為文人抒發自我意識表達的方式。[1]宋代是詞體文學的高峰,宋代記夢詞比比皆是,但作為詞壇大家的柳永,其夢詞尚少有關注,值得探討。
柳永的詞作流傳已久,并且其詞中展現的文學價值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其160首詞中,出現“夢”字的詞有29首,占18.1%,比例相對較高,值得我們思考。本文將結合“夢”自身所具備的特質對柳永夢詞的思想情感、詞體特色等方面進行探討分析。
一
在外敵侵擾較少的情況下,宋代的經濟得到了較大地發展,農民的生產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呈現出一片安定的局面。繁華的都市生活,市民對于娛樂的需求都促進了宋代各類藝術形式的發展,詞作為一種易于抒發詞人情感并且容易被大眾接受傳唱的文學樣式得到了較大地發展。
從現實的生活來看,柳永放蕩不羈的天性與傳統儒家的家庭環境相矛盾導致其悲劇,一生大多落拓不得志。因此,在詞作創作中柳永不免將其內心情緒、所想所思寓于詞作創作中,而“夢”則是他將內心感情寓于其中并且成為情感抒發的突破口,詞作中描摹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夢的理想性
柳永生于仕官家族,自幼便受家族的影響、父輩殷切的期望,儒家思想中經邦濟民的教養讓他曾一度有強烈的報效國家的愿望。在此期間,我們不乏看到柳永創作出投贈詞以表達自己的功名用世之志。如:
一寸金[2]
夢應三刀,橋名萬里,中和政多暇。仗漢節、攬轡澄清,高掩武侯勛業,文翁風化。臺鼎須賢久,方鎮靜、又思命駕。空遺愛,兩蜀三川,異日成嘉話。
此詞以成都特色風物作為開篇,并以短句鋪排的氣勢,向讀者呈現出一片詳實繁華的成都景象。下篇以《晉書·王濬傳》傳中的“夢應三刀”的典故,暗贊益州太守的懿行政績,借此來博得其好感以求功名。
柳永的投贈詞并不算太多,但詞中多次出現“荊王魂夢”等具“夢”詞來暗示其所頌的官員,既委婉含蓄的表達了自己對于官員的贊賞之情,又能體現其渴望被舉薦的希望,表達了積極立志從政的愿望。
此外,“夢斷披衣重起”(《夢還京》)等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柳永“夢”中所包含的理想色彩,僅僅數語便描繪出自己的不得志,用“斷”字修飾“夢”更看出柳永心中理想抱負不能實現時的憂愁哀嘆。
(二)夢的生活性
柳永的羈旅行役詞被世人所贊賞,這得益于長期漂泊在外的人生經歷給了他極大地感觸。多次應試科舉不第,任官又多次輾轉不定,這些經歷都導致了他內心的積郁與孤苦。生活中的種種思緒情感,都被柳永以細膩的筆法融入詞作中,如:
輪臺子
一枕清宵好夢,可惜被、鄰雞喚覺。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前驅風觸鳴珂,過霜林、漸覺驚棲鳥。冒征程遠況,自古凄涼長安道。行行又歷孤村,楚天闊、望中未曉。
以“好夢”被“鄰雞喚覺”開篇,用悠遠的雞鳴聲從聽覺效果上自然地將作者的時空觀由夢境轉入對現實生活的描摹。將內心凄涼的感情通過“淡煙衰草”、“霜林”、“孤村”等意象進行渲染呈現,達到使讀者感同身受的目的。柳永此番受挫后,身心俱疲。在下闋中接連暗借“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江淹《別賦》)描繪出自己的悲慘現狀,以及內心無限的留念與失意悲傷。無不暗含柳永的無奈,以及想要“返瑤京”、“千金笑”的想法。將“夢”與現實生活進行緊密貼切的聯系,并為此詞的分界線,“好夢”成為一個側面反襯現實生活不如意,雖然對“夢中”的情景沒有詳細的描述,但以“夢前”“夢后”的巨大差異性仍可以有力地突出強調柳永羈旅生活的痛苦。
(三)夢的情感性
繁華的市井生活,歌妓的淺吟低唱,一心追求自由的柳永不免流連于煙花柳巷之地。這些經歷都成為其情感吐露的來源,促成了柳永大量閨怨詞的創作。
佳人醉
暮景瀟瀟雨霽。云淡天高風細。正月華如水。金波銀漢,瀲滟無際。冷浸書帷夢斷,卻披衣重起。臨軒砌。 素光遙指。因念翠蛾,杳隔音塵何處,相望同千里。盡凝睇。厭厭無寐。漸曉雕闌獨倚。
暮雨初霽之恬靜,云淡天高之闊達。“此時相望不想聞,愿逐月華流照君。”(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此處的月華風景比張若虛所見有過之而無不及。然一“冷”字砭人肌骨致“夢斷”,之前美景再美好也都全部化為空。而下闋則繼寫“夢斷”后對千里之外的她的相思掛念。曠達如蘇軾的“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但柳永做不到,只是“盡凝睇。厭厭無寐。漸曉雕闌獨倚。”因念而思,將內心的愛與思念的深切情感寓于夢中,別離時間之久,音信久不相知,“夢斷”一詞將柳永對遠方情人憂思的情感溢于筆端、心頭,更襯心中之悲傷。
二
夢產生于人的情感生活,以夢境的形式呈現出來,不同的夢境具有不同的意愿,而意愿的不同則影響著詞本身所具備的價值。我們從柳永的夢詞中可窺見夢讓其詞更具可讀性與價值。
(一)夢的共情性
“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記載于《避暑錄話》。娛樂的需求、歌妓們的傳唱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柳永詞的傳播范圍,但不能忽略的是,其詞中“夢”的適時運用對詞的傳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夢作為一種虛幻的產物,是人類生命生活中的一種自然而然的身心體驗,存在普遍性與必然性。柳永詞傳播之廣和“夢”意象本身所具有的共情性有著極大關系。“夢”不僅讓柳永的生活情感有了寄托的載體,而且還拓寬了柳永詞的表現內容,如:政治理想不能實現的失意,羈旅漂泊在外的孤苦,思念戀人的想念……凡此種種,正因為詞作中抒發了柳永自身的真實情感,同時涵蓋情感內容之多,不管是身為朝廷官員還是身處街井市民,在接觸了柳永的詞作之后都能聯想到自身的境遇遭際,從而對其詞作產生心理上的認同,即共情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柳永詞作的可閱讀性范圍變寬,詞的接受群體也變得更廣。
(二)夢的共通性
“夢的景象,夢的意識,夢的境界,夢的氣氛,彌漫與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切領域,從這個特殊的角度說,整個古代文學就是一個由無數作家之夢共同構成的大夢。于是,我認為,夢正是那個千差萬的文學創作的一個共同的交匯點。”[3]這便解釋了夢對于作家作品間產生了重要的聯系作用,從這些聯系中我們對作家作品的理解也有了更好的參照作用。
“夢”在詞中所具有的共通性很多,以詞人用“夢”表達情人相思詞為例進行比較分析。“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云。”(晏幾道《蝶戀花》)此詞以思婦的口吻記敘了自己日常生活,通過夢醒后對獨身一人寂寞的感慨,轉寫現實生活中眼前“紅燭自憐”、“垂淚”,表達出對男子深切地思念之情。
柳永詞中也不乏以“夢”表達思人之情,如:“殘夢斷、酒醒孤館,夜長無味。”但因其詞多寫勾欄瓦舍之中社會地位比較低的歌妓酒女,所以被很多人譏誚其只作淫詞濫調,即王灼曾評柳永詞:“唯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4]李清照亦曾言:“雖協音律,而詞語低下。”[5]柳永在《傾杯》中寫道:“當無緒、人靜酒初醒……夢枕頻驚,愁衾半擁,萬里歸心悄悄。”柳永將男女相思之情進行細致描繪,不僅將自已羈旅行役所見所感融入詞作之中,并且用男子在夢中思念女子的獨到的視角,展現了超出一般閨怨思念詞的高遠境界。故《樂府余論》中曰:“柳永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恒流。”[6]這即是柳永詞之一大特色。
綜上所述,柳詞中“夢”意象本身所獨有的理想性、生活性、情感性、共情性、共通性等特質,讓詞的表現內容與方式更多樣化,詞的情感表達更具詞人自身特色與魅力,在此過程中也增大了其詞的傳播范圍,讓更多的讀者易于接受。鑒于此,柳永夢詞在中國夢文學史上應有一席之地;對于柳永夢詞的探討也可成為窺見柳永創作內心的新方式,成為柳永詞研究的一個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89.
[2]唐圭璋.全宋詞[M].北京:中華書局,1965:32.(本文所引柳永詞均據此書)
[3]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22.
[4]王灼著.碧雞漫志校正[M].岳珍點校.四川:巴蜀書社,2000:36.
[5]王延梯.李清照評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101.
[6]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中華大典.文學典[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461.
(指導老師:劉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