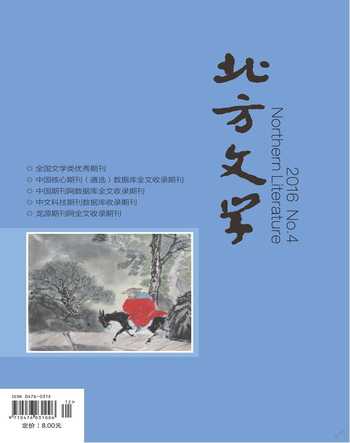淺談史詩與英雄
謝天昊 陳矚遠 李文鑫
摘 要:史詩是人類文明沉淀的產物,各洲史詩各有千秋,其中英雄更是形象各異。智慧、勇武與豐富的情感均為英雄必備的特質,但不同大洲的史詩著重描述的方面也不盡相同。“英雄”,是由集體無意識驅動的,為了拯救,為了大多數乃至全部人類而挺身而出的人。擁有著人的血統,便會受到影響,不論是人類還是半神。由人類創造的名為英雄的工具,終將在人類的長矛下走向終點。所謂的英雄,只是由人所編織的,一幕宏大的悲劇罷了。
關鍵詞:史詩;英雄;人類;文學性
“神話”與“史詩”兩詞均源自希臘文。神話描述了眾神祇的天庭生活的矛盾,史詩是半神或人類英雄豐功偉績的紀念碑。因神是統轄人類的,就會與人產生聯系,那些具有燦爛幸運被神選中的人類,或奉詔奔走于人間的半神便是英雄。因此,許多時候,神話與史詩二者是重合的,交織顯現的。
在此并不對“神話”和“史詩”進行具體的定義,畢竟二者重合度要很低才能給出合適的劃分標準。史詩可分為神話史詩和英雄史詩,這二者重合度也非常高,至此只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因為大部分史詩的創作年代比神話晚,但還處于宗教至上的年代,遂與神話一樣,神秘主義色彩十足。但因成書晚,史詩在敘事的宏大規模和人物形象的豐滿度上遠勝過神話。神話故事的依靠大量單獨的故事得加才能獲得對一位神形象的總結,而史詩則以巨大的長篇敘事展現一個巨大的沖突,使在一個單獨完整故事中獲得對英雄形象的完整概括。再談談文學性,形式主義學派對其的定義是:鮮明生動、感人心魄是文學性;對傳統符號規范、文學作品模式、人物模式和因果原則有批判是文學性;它還體現文本所用材料在完整結構中的地位與前景,總而言之,創新即文學性。
一、具體分析
(一)文明的沉淀——何為英雄
史詩是人類文明沉淀的產物,主要分布于亞洲、歐洲與非洲,而曾被土著統治,后又被殖民者占領的美洲則鮮有史詩的蹤跡,更不用談南極洲了。
各洲史詩各有千秋,其中英雄更是形象各異。智慧、勇武與豐富的情感均為英雄必備的特質,但不同大洲的史詩著重描述的方面也不盡相同。
亞洲史詩中對于英雄的智慧與勇武都很看重,不論是吉爾伽美什與恩奇都合理擊敗天之公牛,還是塔里埃爾擊殺獅虎等事跡,均對英雄的智、勇進行了詳盡的描寫。同樣,亞洲史詩中,友情與宿敵往往是英雄情感世界的重要元素。阿夫坦季爾有名為努拉丁的忠誠的友人,迦爾納與阿周那是同父異母的生死宿敵,即便高傲暴虐如君臨于古巴比倫的半神吉爾伽美什,也有恩奇都這一摯友兼宿敵。
歐洲英雄與亞洲英雄較為相似,但史詩中對于忠誠的友情的描寫僅有寥寥數筆,其中著重描寫的是愛情與騎士品質(騎士這一身份也經歷了很大的轉變),而凱爾特的史詩神話更是其中典范。《奪牛長征記》中的庫丘林,因為殺死鐵匠庫蘭的獵犬一事道歉,而將自己的姓名改為“庫丘林”,即“庫蘭的猛犬”,發誓代替獵犬守護庫蘭,后加入赤枝騎士團。這一階段的騎士,并不像后世提到的那般高潔,反而帶著一股匪氣與濃濃的年輕熱血。而后來的《芬尼亞傳說》中的迪盧木多·奧迪那,費奧納騎士團的成員,則是以一位高潔的騎士的身份現身。迪盧木多高尚的騎士精神及其愛情悲劇,都成為后世多個傳說的藍本。
也許是由于生存環境的影響,非洲史詩中對于英雄的勇武的描寫可謂是登峰造極,極盡夸張之詞。非洲英雄往往如原野上的兇獸一般,天生神力且蠻勇無比,因此常常會令人產生其大腦也滿是肌肉的錯覺,加上書中鮮有對其智慧的描寫,因而使讀者忽略他們的智慧。非洲英雄中不僅有胎兒時期便可從母體爬進爬出,尚未出生便可手舉巨樹之人,也不乏直至七歲仍在地面爬行,但一出手便有萬夫不敵之勇之輩。非洲史詩,堪稱史詩中一大奇葩。
(二)無意識的拯救——英雄的誕生
在史詩之中,主角總是擁有人的血統。即使是吉爾伽美什之流,也只是“半神”,是神與人的混血。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史詩的主人公漸漸脫去了“神性”,變為凡人。而他們的敵人,也往往只是普通人。人類與神明的沖突,也漸漸變為人類與人類的沖突。那么,英雄的“拯救”由從何而來呢?
或許可以用這個,來解釋英雄的誕生。
榮格提出的集體無意識,即人在嬰兒以前的一切時間,包括祖先的生命的殘留在內,可以在一切人的意識中找到的普遍性的無意識,它只是一種可能,以某種并不明確的形式存在于人的意識中。
那么,用集體無意識的概念來解釋的話,便也說的通了。引用榮格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島代表一些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部分,由于潮汐運動才露出來的水面下的部分代表個體的個人無意識,所有的島最終作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體無意識”。那么,我們可以認為,“英雄”,是由集體無意識驅動的,為了拯救,為了大多數乃至全部人類而挺身而出的人。擁有著人的血統,便會受到影響,不論是人類還是半神。
同樣,他們的敵人,也包括人類自身。
(三)消滅異端的異端——英雄的輝煌與陌路
英雄因“拯救”而出現而“拯救”這一概念,并不僅僅是那種經典的勇士斗魔王的套路,還有阻止動亂的意思。總之,便是“消滅異端”。
消滅神明這一異端,因為它們會玩弄人類;消滅魔物這一異端,因為它們會殘殺人類……消滅暴君這一異端,因為他們會危害大多數人;消滅奸人這一異端,因為他們會威脅多數人……這,就是英雄的職責。
人類具有強烈的排外性,即排斥所謂的“異端”。所有的異端都是社會的敵人,都是可能威脅人類社會的存在,也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是,人的個性本就存在,又何談通常與異常?都只是因為恐懼罷了。因為神明之流的力量令人恐懼,所以消滅他們,就是拯救人類。
但英雄們也有許多與所謂“常人”有異的地方,與被他們消滅的存在同為異端的英雄們,也會因為他們本身存在的可能的威脅而被消滅。齊格弗里德斬殺惡龍,在狩獵時被別國騎士刺死;迦爾納在戰車上被射殺;庫丘林被自己的槍刺死……神子與屠龍之人,都離“人”太過遙遠,這種異端只能走向消亡。而后世的塔里埃爾之流,雖勇猛無比,但卻遠未脫離“人”的范疇,所以并沒有半神之流那么具有威脅性,因而有極少數得以幸存。
由人類創造的名為英雄的工具,終將在人類的長矛下走向終點。
(四)褻瀆的圣言——人類的存在與終結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英雄是人類的象征。而神明象征自然,抑或是星球、宇宙、世界。
那么,英雄戰勝神明,便是人類對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祈愿。但如此強大的英雄們,又有幾人逃離了死亡與歲月的追捕?即使吉爾伽美什取得了那長生不老之藥,但也因神藥被蛇吞食而不得不走向死亡的終局。那么,將這些故事翻譯一下,“即便人類在某種程度上戰勝了自然,也終將被自然毀滅”。
但是,不論是神話還是史詩,向來都是神明主動攻擊人類,企圖對人類不利,而非人類主動挑戰神明。那么,問題來了,神明為什么要攻擊人類?神話與史詩之中給神明的行為冠以各種天馬行空的動機,但在這一切的動機背后,我們會發現,神明對于人類具有一種仿佛是與生俱來的敵意,但神明卻能與除人以外的其他所有生物和諧共處。不僅僅是神明,就連那些所謂的神獸魔怪也對人類抱有敵意。甚至可以說,世上所有一切都是人類的敵人,包括人類自身。或者說,人類是世界的敵人。
人類抱著對于“人類”這一身份的優越感以及“人類在與世界的對抗中頑強生存下來”的自我滿足,站在全世界的敵人的位置上,就如史詩中的英雄一樣,在對抗神明(自然)中走向滅亡。
所謂的英雄,只是由人所編織的,一幕宏大的悲劇罷了。
二、矛盾特色與價值觀
史詩以矛盾的構造勝出。眾多矛盾的交織并行使史詩的戲劇性更強。為了更好的闡述這一問題,在此對參考文獻進行分類:(1)反擊外來侵略類有《伊戈爾遠征記》、《薩遜的大衛》、《羅蘭之歌》、《馬丁·菲耶羅》;(2)宮廷斗爭類有《尼伯龍人之歌》;(3)貴族奇遇類有《熙德之歌》、《貝奧武甫》、《吉爾伽美什》、《虎皮武士》、《勇士魯斯塔姆》、《埃涅阿斯紀》、《羅摩衍那》、《奧德賽》;(4)古代重大戰爭類有《埃達》、《薩迦》、《伊利亞特》、《摩訶婆羅多》。
上述分類不一定合理,也因上述膾炙人口的史詩巨著有許多內容上的重合點。每種史詩都有其獨特之處。
(一)矛盾的多重性和復雜性
作為維系史詩的重要因素——矛盾,總是表現出多重方面交織的狀態:《吉爾伽美什》中,吉爾伽美什“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是神”。恩奇都是神創的可與吉爾伽美什匹敵的英雄,一開始的故事源于他們兩人的矛盾,后來兩人成了生死之交,于是就引入人神矛盾,寫到女神見棄于吉爾伽美什,二人與天牛的戰爭。因恩奇都之死,引入生死矛盾、吉爾伽美什肉體與心靈的矛盾。《伊戈爾出征記》中伊戈爾大公執意要率軍征波洛夫人,表現民族矛盾;而伊戈爾兵敗被俘,向俄羅斯大地上的諸王公呼吁來救的時候,各王公表現了不同態度,回憶往昔相互攻訐的歲月,哀嘆“博司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又展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矛盾的多重性直言矛盾數量之多,但若彼此并行,依舊無奇,矛盾的復雜性則表征它們互相交織,互相顯現。眾多矛盾的交織并行使史詩的可讀性更強。
(二)關于矛盾激化
而史詩中難有的技法是借一個小小的導火索將矛盾不斷地有層次地激化開去。《尼伯龍人之歌》全篇圍繞尼伯龍根寶藏的歸屬問題是英雄們之間的矛盾加深,由宮廷斗爭演變為民族大戰,以激烈的戰爭為伴奏,記述克琳希爾德由溫情走向冷酷,對英雄們展開攻勢,只為財富。本書以眾英雄共同奔赴天堂為結局。出場勢力錯綜復雜的。
三、文學性
史詩是歷史文化的結晶,是其文化背景的高度濃縮,其本身就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史詩并不依靠華麗的辭藻,僅僅是以極為簡樸的語言,便將人物的形象勾勒出來。每個人物的特質,都包含在其言行之中。正如“普遍升華說”認為,文學語言與話語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話語便是文學語言的源泉。史詩本身,并不像是如今常見的書面作品,倒不如說是作者站在讀者面前,用話語來講述其中的故事。這同樣是一種極有效率的表達方式,每一句話都極為簡練,可以直接牽引讀者的形象思維。
史詩中所選用的形象,如龍、神等,本就是某一概念的具象。代表惡欲的龍,居高臨下的神。將當代的某種困境提取出來,具象為史詩中英雄的敵人,這便是文學幻想。而人與人外之間曖昧的分界,往往有助于對于史詩的感情色彩的理解。
史詩中的暗喻屢見不鮮。如著名的樹中劍Gram,象征著光輝與太陽,而奧丁用Gungnir毀去Gram,便是摧毀了諸神的輝煌,只能絕望地迎來諸神的黃昏。而對于史詩的理解,也應從每個意象的背景,從整個故事的歷史背景來看。
四、現實價值
這些古典作品對今日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熙德之歌》被法國劇作家高乃依改寫為戲劇,《貝奧武甫》《伊戈爾遠征記》都被搬上熒屏。古老的神話與史詩為《哈利·波特》《魔戒》等現代小說作品提供了創作靈感。
這里談談讀這類作品的方法論。這一類作品大多是時代鮮明的反映,得先了解時代背景和作者經歷,才能讀好它們。
當今之世,人們無神學世界觀,大多數人沒“逞英雄”的勇氣,沒有好奇心與求知欲,遂棄置了對英雄的開辟精神。工業文明沖擊著田園詩式的人性的自由。工商業文明要求短周期高利潤,而史詩中的英雄的誕生則是長期精神積淀;工商業時代的榜樣用過即棄置,而神話中的神性也非人朝夕可達的境界。
我們需要神的慧眼,英雄的精神,人的欲求。我們不僅需要法律,我們還需要道德。我們依法的精髓為內核,以道德的元神為緩沖,也要將詩的靈魂外化于生活。
參考文獻:
[1]張遇.世界英雄史詩譯叢[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6.
[2]普羅普,李連榮.英雄史詩的一般定義[J].民族文學研究,20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