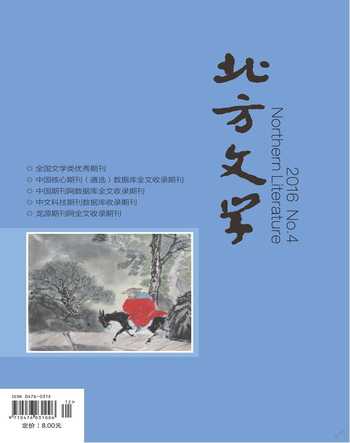詩話愛情里的李商隱
何汝星
摘 要:李商隱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學界對其政治生涯與詩歌技巧分析較多,但在愛情方面較少有人涉及。本篇論文通過對李商隱愛情經歷的考察,從大婚之前、甜蜜婚姻、喪偶獨處三個階段剖析詩人的愛情觀發展趨向,指出詩人從“為賦新詞強作愁”般的愛情夢幻到最終境界指向人生意義的愛情寫實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李商隱;愛情觀;人生意義;心路歷程
李商隱生于公元八一二年,即唐憲宗元和七年,卒于八五八年,即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縱觀義山一生,說他是個悲劇人物一點都不過分,他病逝于故里,即今天的河南鄭州,算是魂歸故里了。但他是死而無官籍。這一點,對于一個要求積極入世的儒家學者來世,是個莫大的遺憾。
一、懵懂的愛情夢幻期
年少的商隱非常自命不凡,常有“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孫”的優越感,但是他的家境并不好,楊柳說義山是“沒落的小貴族”。但是義山家境雖然沒落,但是自小就才華橫溢,連他自己后來在不忌諱地說“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可以想象,一個富有才華的少年,除了追求科舉功名之外,難道不會想點其他的事嗎?春風得意的少年在愛情上蠢蠢欲動是必然的:
“小苑華池爛漫通,后門前檻思無窮。”(《蜂》)
“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秋月》)
這兩句詩表達的是年少的詩人對于愛情的憧憬與向往的情感。看著佳人池上、小苑、橋邊的身影,詩人那顆懵懂的心亂了。躲在一旁偷窺,詩人被美人深深地吸引住了。一“難忘”,一“可憐”,在佳人走遠之后,詩人陷入了深深地回味之中。可是,義山迷戀的僅僅只是佳人嗎!恐怕不是,詩人留戀的是那種意境,而佳人恰恰是這種純美意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光是這樣?不,義山的詩絕不只是停留在這個層面上,義山的情也不僅僅止于此:
“鴛鴦可羨頭俱白,飛來飛去煙雨秋。”(《代贈》)
這是什么,不就是對于美好愛情的渴望嗎!言為心聲,詩言志。義山在這里不就是表達了自己對于一種甜蜜愛情的向往嗎?這當然只是義山心之所想,一個少年的甜蜜的春夢。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清楚,義山與每一個普通的青年一樣,對于愛情充滿甜蜜的幻想,對于那個“佳人”是那么地蠢蠢欲動。
當真正經歷過情事,我們的詩人在長大。但被滿足了自身的物質渴求后,我們的詩人開始向自己的精神世界進行探索。“憑欄明月意,池闊雨瀟瀟”,這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的思考姿態。思考著什么?義山在問自己,在愛情里,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這種東西沒有現成的答案。思之不得則求索,以下便是義山的求索:
斂笑凝眸意欲歌,高云不為碧嵯峨。(《聞歌》)
楚腰知便寵,宮眉正斗強。(《效徐陵體贈更衣》)
掃黛開宮匣,裁裙約楚腰;乖期方積思,臨酒欲拼嬌。(《又效江南曲》)
根據楊柳先生的意思,這是李商隱對于戀人的一系列的神情姿態的刻畫。我把義山對于女人的描寫說成義山對于愛情的求索,是因為我覺得這是義山在自我審視。當愛情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中的時候,它的內容就是與情人的相處。李商隱是個天才的愛情詩人,他的求索讓自己陷得更深,不能自拔,同時也對愛情認識得更加深刻:
“若將石城無艇子,莫愁還是有愁時。”(《莫愁》)
“芭蕉不卷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代贈二首》之一)
“總把春山掃眉黛,不知供得幾多愁。”(《代贈二首》之二)
一言以蔽之,此上皆可謂愛情之愁。但是,正是一些“剪不斷,理還亂”的煩惱給了義山越來越深刻的愛情認識。
二、誰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有人講,李商隱是因為想要巴結權貴王茂元,所以才和王茂元的小女兒結婚的。這種觀點從表面看,確實很有邏輯,很站得住腳。但是,我們今天去翻看李商隱的生平經歷時就會輕易發現,李商隱不但沒有從這段婚姻中得到任何的政治利益,反而受這段婚姻所累,在朝廷中被人排擠。吳調公先生更是有言“王茂元彌留之際,李商隱都不在跟前。”有詩為證:“屬獷之夕,不得聞啟手之言。”因此,我們就可以說,李商隱與王氏女的結合就是不為名利的如“結愛曾傷晚”。
李商隱選官時落選(其實是受人排擠),非常抑郁,當時就寫下了這么首詩:
“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
“錦長書”說的不是別的,正是妻子王氏給自己寫的家書。“鄭重”二字表明了王氏對于自己丈夫的事情的關切。末尾“中心最不平”一句是寫妻子為自己鳴不平。義山必然是被王氏對自己的深情感動了,才寫下的這首詩。這時候的李商隱,是真的把自己的妻子視為“平生之知己”了。李商隱與王氏女的婚姻長達十四年,直至王氏女病逝在河南家中。十四年的風風雨雨,一幕一幕仿佛就在商隱的眼前。
最妙的還該是那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楊柳先生用了四個字評價這首詩“語淺情濃”。當今社會日漸開放,夫妻好像僅僅就是一種關系。結婚,離婚,可以那么得輕易,那么得隨便。中國是有自己的美好的婚姻愛情傳統的。中國人傳統的夫妻之間的相濡以沫是不僅僅值得當今國人去學習,更是值得全世界去學習的。更有近人整出了個“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對比詩人的愛情,不禁讓人唏噓不已。
戀愛需要的是“恬不知恥”的狂轟猛炸,婚姻需要的是相濡以沫的體恤理解。王氏女先商隱而逝世。商隱悲慟不已:“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于人。”這樣的悲痛不是一兩首詩就可以派遣得了的,義山的暮年,悼亡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三、愛情的挽歌
本來政治上的失意,至少可以在妻子對自己的甜蜜愛情里得到一點慰藉。但是,妻的離開,意味著義山不得不黃燈孤影了此生。暮年的義山,心是孤寂的。可是也恰恰是這個時候的李商隱,寫成了《錦瑟》這樣的愛情千古絕唱,站在了詩的巔峰,也到達了對于愛情理解的通境。
就《錦瑟》而言,有人說李商隱在這首詩里講的更多的是政治經歷的總結,還有人說這里說的就是愛情經歷總結。本文認為,這首《錦瑟》是詩人以愛情經歷入詩,在中間糅合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失意與體驗,最終達到一種對自己人生總結的效果。也就是說,在暮年的義山眼中,愛情已經不單單只是某一種情感,而是融入了他的生命中,并與他的政治情懷相交融,形成了一種通境。而這種通境的形成,與他對于妻子的悼亡是密不可分的,且看:
“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暮秋獨游曲江》)
這是一首情意極其濃烈的悼亡詩。尤其是最后一句,成了詩人對于妻子的冥思。那“江水聲”,意味著太多太多的東西了。而“悵望”二字,則寫出了詩人對于無情命運的無奈。
邊行邊思,愈思愈傷,傷生頓悟。在李商隱的筆下,這首《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幾乎是達到了自己對于亡妻悼念的高潮:
“潘岳無妻客為愁,新人來坐舊妝樓;
春風猶自疑聯句,雪絮想和飛不休。”
“長亭歲盡雪如波,此去秦關路幾多;
惟有夢中相近分,臥來無睡欲如何!”
悼念慢慢地上升為自己對于人生的冥思,開始不局限于愛情。這個時候,義山緬懷的是絲絲溫情,是親情般的愛情。這種愛情,沒有轟轟烈烈的熱戀,沒有地久天長的海誓山盟,有的只是物是人非之后“夢中相近分”、“臥來無睡”的牽掛。
人生到了至親離世、抱負難酬的苦澀境地,義山的心里一定是五味雜成的。但是詩人的境界與思考卻是在這種孤寂的苦痛中又深了一層。“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讀來言簡意賅,可是文字背后的情感卻是說不盡。“夕陽”是什么,“黃昏”又是什么?義山的含蓄給了我們無限遐想的空間。這里面必然有情:愛情親情;必然有志:入世功名。可是,似乎又不僅僅只是這些。
李商隱正是帶著這樣的一種超然于悲喜的愛情情懷離開了人世。他的一生本是悲劇的一生,有如“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但是,宗教給了義山更大的智慧,更高的人生境界去承載著這種悲劇。
參考文獻:
[1]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董乃斌.李商隱傳[M].上海古籍出版,2012.
[3](清)何焯.義門讀書記[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7.
[4]李中華.試論李商隱無題詩[M].唐代文學論叢,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