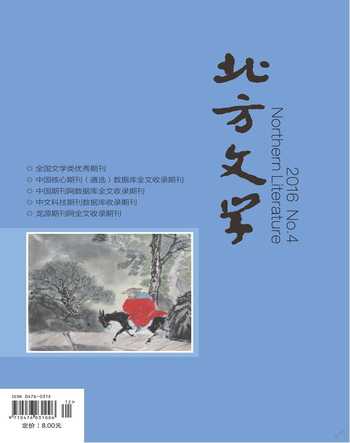王之春《談瀛錄》及其日本觀
何靜
摘 要:王之春是晚清的駐日使臣,曾撰寫《談瀛錄》。王之春本人在日本的種種見聞及其對于日本的認識,涉及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教育、軍事方面,對日本的這些看法與認識,反映了王之春的經世與保守。其記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近代化過程中的日本,也展現了一個晚清士人對日本的認識和看法,對于近代中國人認識、了解日本有一定的意義,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關鍵詞:王之春;《談瀛錄》;日本觀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號椒生,湖南清泉縣獅子坪人,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后裔。王夫之被稱為“船山公”,因此后人稱王之春為的“七世祖船山公”。
王之春出生于清王朝封建統治窮途末路時期,外族不斷的入侵;他自幼飽讀詩書,對于“圣賢六經之奧,國家治乎之原,民生根本之計,皆有‘所窺”[1],因此在王之春的身上帶有挽救民族危亡的憂慮感和責任感。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直接威脅中國的東南沿海,但中國的統治階層對于日本的了解不深,于是兩江總督沈葆楨委派王之春赴日考察長崎、橫濱等地,王之春熟悉了沿海一帶的地理狀況,“以日本之狡焉思啟,檄委馳赴該部察其情形……借以新耳目而擴胸襟。就所經游,編為日記。至其國之風土人情,姑就所知一二瑣記,統名之曰《談瀛錄》。”[2]
《談瀛錄》共三卷,光緒六年(1880)上海文藝齋刻本,卷一、卷二為《東游日記》,卷三為《東洋瑣記》,還有四卷本,則是將《東洋瑣記》分為上下兩卷,其中第三卷對日本的地理、戶口、租稅、兵制、官制、國債、物產、教育、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扼要的介紹。在書中綜述清代的外交歷史,繪制出列國地理的輪廓,其目的是使辦洋務的人能懂洋務,不要讓那些利已之徒用洋務作為作利已的借口。因此可知王之春此行是要去考查日本的地理、民俗等狀況,同時密查日本的軍情。《談瀛錄》是中國第一部介紹日本國情的著作。在此之前,雖然1854年有羅森的《日本日記》,1878年有何如璋的《使東述略》,但這兩本書并沒有公開流傳開。王之春將《談瀛錄》及時刊刻,知名學者王先謙說,“《談瀛錄》三卷,文瞻而事核……異日從事東方者,宜于是書有取焉。”[3]回國后,向清帝“上萬言書,陳夷務,自請率銳師規復中山”[4]以期天朝進行改革自強。
一、政治制度——日本文明皆源自中華
王之春到日本以后雖然對于日本的社會現狀十分的驚奇,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日本的認識存在著局限性。晚清社會以前日本這個鄰邦,一直都以“蕞爾小國”,甚至“倭人”這樣的形象出現在晚清社會人們的文章典籍和人們的視野中,多年的閉關鎖國,使得民眾對于外界的了解甚少,王之春作為一個生活在當時的文人,他對于日本的認識,很難不停留在士大夫們都能接觸到的,諸如《山海經》、《史記》、等這樣的一些文化典籍的記載之中,因而王之春對于日本近代以來的變化不但知之甚少,還竭力的想要從中國的儒家經典之中,找到日本的社會現狀與清王朝在歷史上是否有相通之處,換句話說就是仍然覺得日本的物質文明源于中土,是模仿中華民族而來。即如他所說,“《三國志》、《后漢書》既載其求仙東來事,今該國尚有徐福祠,熊趾山復有徐福墓,則日本之主,其系出我中土無疑。而作《日本通鑒》者,則以為周吳泰伯后,乃源光國尚駁之,曰:‘謂日為泰伯后,是視日為中華附庸國也。”[6]
他認為中華歷史上有日本制度的源流,即西學中源的理論,甚至認為“彼西人所詡為絕學者,皆不能出吾書”[7],王之春在參觀日本的博物院時看到博物院中陳列之物,感嘆道“其傳國之寶,及各國衣冠制度在焉,尚有漢唐時頒賜該國衣物。”[6],極力尋找中國留給日本的影子,看到“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6]士大夫的保守思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看到日本的變化與進步。在王之春后不久出使日本的黃慶澄對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的認識就超過了他,黃慶澄認為“日本官制,自維新后,屢加更改,甚至有一歲中旋設旋廢者,茲就其現存者約略言之……”[8]
王之春對于日本的官制、徭役、兵額、戶口、田賦等也進行了細致的記載,反映出日本明治維新過后社會雖然改觀很大,但是仍然存在“民無私田,租稅定額”,賦稅則“取諸民者已十之七,而民亦不堪命矣”[6] 的現象。
二、經濟制度——物質文明先進
在商業方面,日本的商業文明的發展程度相對于當時的歐洲國家是落后的,但是相對于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而言已經有了相當的進步,王之春“旋游長崎市”時,“聞中華之貿易于此者約千三百人。”[6]如此可見中日民眾之間的貿易往來在那時還是相當頻繁地。日本的市場上,凡是有奇技異能創制器的人,被準許在這里設肆貨賣,因此物之良者、難致者,大多聚集在這里。“近年有西商延中人制紅茶,味薄,遠不及中土所產,制日多,價驟賤。……近海多產鯊魚,漁者折翅干之,販賣中土……其余海物,如鰒魚、魷魚、干鱈、海帶,運來中土極多……”[6]王之春看到的是一個街市喧鬧、商業繁盛的日本,并對此表達了驚羨之情。
交通運輸業方面,王之春對于日本的交通運輸業說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鐵路交通,這也與后來他在出使俄國之際,對于歐洲國家的鐵路運輸網如此發達感到驚嘆,并在回國后主張發展鐵路運輸有著微妙的關系。他在到達日本以后,“偕梁煒煌同坐火車返神戶。”,“十一日晴。乘火車往游東京,計程七十里。鑿山填海,以通鐵路。”[6]可見日本當時火車已經為普通百姓可用之交通工具,并且火車的車速也是相當的快,為此王之春還專門寫了一首名為《火車》的詞來贊嘆日本的火車:“車聲轆轆逐斜暉,四面蒼茫入翠微。良驥追風偏就范,游龍無翼亦能飛。路如砥矢長繩亙,山比煙云轉眼非。或挽或推都是拙,本來達者在之機。”[6]
王之春對于日本的經濟,科學和技術的先進性,并沒有像一些保守派官僚那樣,鄙夷的稱之為“奇技淫巧”,而是保持了贊美和崇拜的態度,這是他思想開明的表現。
三、文化教育——學校教育注重軍事、字體皆模仿中華
日本的學校,“東京太學生徒凡百馀人,分法、理、文三部。”“所設官學校甚多……不專重漢學。雖參讀孔孟書,既不敬惜字紙,又不聞圣人之教,擇邦之賢者為師而崇祀之……”學校亦多,“考唐時,日本遣使中國,每有留學生,由官給以職祿,于中國諸事亦步亦趨。”日本之教育西化由此可見一斑,教學內容上強調軍事教育,“海陸軍有士官學校,專以教帥兵者。凡地之險要、器之精良、陣之分合、兵之進退、營壘之堅整、手足之純熟,一一皆成書,繪圖貼說。”[6]這種教育方式與當時清政府實行的八股文、科舉取仕的教育制度有著天壤之別,再加上1889 年至 1894 年,王之春出使西歐四個國家 ,通過考察 ,深切的感受到西方各個國之所以強大,除了制作精良的武器和發達的實業之外,國民教育也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這些方面對后來王之春提倡西方教育方式的產生了影響。
書法字體方面,皆仿佛我六朝人手筆。王之春在那里看到日本學者們書寫的書法作品,認為“初學書者,皆懸腕執筆,作二三寸大字,點畫波撇頗留古法。行草亦佳。碑之古者,有《大和尚法隆寺金堂佛背銘》、《釋迦佛像銘》、《那須國造碑》、《多賀城碑》,皆仿佛六朝人手筆。”[6]從中可以看出王之春并沒有走出日本制度源于中國的傳統看法,預示著在學習日本的進步方面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軍事方面——警惕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威脅
明治維新后,日本很快就踏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的自身國情,使得向周邊的鄰國擴大原料市場和產品市場成為其迫切的需要。日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卻沒有讓清政府和整個中國社會的高度警覺起來。他們對日本并不理會,仍以“蠻夷”來看待它,持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我國與日本隔海相望,鄰封密邇,種族文字,源流相承。”[9]“二千年來,迭有交往,國人恒以普通外夷視之,未始注意。其后日本經明治維新,國勢驟強,然猶未知其可畏。”[9]清王朝的主流意識仍然認為日本全面向西方學習是“雕蟲小技”,無礙大局。
王之春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來刺探日本軍情,《談瀛錄》中附有日本各地地形圖,以便于回國后對于日本進行分析,并對所去各地的軍事優劣勢情況進行分析,其中透露著分析日本的軍事地形優劣勢的信息,以便于預防日本之侵略。王之春一直以來以一個愛國者自居,他甚至異想天開得想帶一隊人去偷襲日本,以解心頭之恨。
五、結語
綜上所述,王之春對日本的各個方面的認識,雖然帶著士大夫保守的有色眼鏡,但他看到了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的種種變化,無疑在視野方面,高出了那些固守家中的保守的地主階級,這些在他后來積極贊成開展洋務運動中有所體現,他的關于日本軍事方面的關注,也給清政府傳遞了防范日寇的信息。由于使節的身份和時間的限制,王之春走馬觀花似的參觀訪問,對于日本社會物質層面的認識并不全面,也不深刻。然而,走出國門目睹外國先進的物質文明,要遠比在國內從書本上看到的外面世界更真實生動,更具有說服力。王之春經過在日本一個多月的考察,在《談瀛錄》中,特別是《東洋瑣記》中記載的日本的地理、戶口等方面的情況,比何如璋的《使東述略》更加深入具體。《談瀛錄》的出版帶動了一系列游記的出現,并且在國內引起了一股出游西方的熱潮。
參考文獻:
[1][清]王之春.椒生筆記.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岳麓出版社,2010.
[2][清]王之春.椒生詩草卷三.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岳麓書社出版社,2010.
[3][清]王之春.談瀛錄·自序.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岳麓書社出版社,2010.
[4]李元度.椒生詩草序.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岳麓書社出版,2010.
[5][清]王之春.談瀛錄卷一.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岳麓書社出版,2010.
[6][清]王之春.東洋瑣記.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岳麓書社出版,2010.
[7][清]王之春.使俄草.卷二.趙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點.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岳麓書社出版,2010.
[8]黃慶澄.東游日記.陳慶念.蒼南文獻叢書:東游日記.湖上答問.東瀛觀學記.方國珍寇溫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韓小林.論近代中國從輕日到師日的轉變[J].安徽史學,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