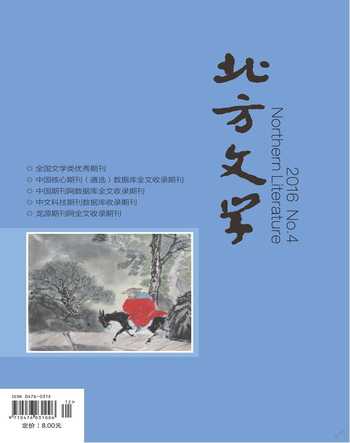從“禪農并舉”到“禪商并舉”
李鐵薇
摘 要:如今少林寺推行的“禪商并舉”并非是一個全新的寺院發展模式,所謂的“禪商并舉”事實上就是“禪農并舉”在新的社會時代中的一種適應和表現。本文主要通過對“禪農并舉”的探討,以期理解當今少林寺的商業現狀。
關鍵詞:少林寺;禪農并舉;禪商并舉;禪宗
德國《南德意志報》在2009年8月12日關于少林寺的報道中曾使用這樣的標題:“中國佛教寺院:廢墟上的經濟帝國,少林寺不僅是功夫中心,也是中原的‘資本主義。”[1]現在的少林寺一改人們對于寺院青燈黃卷、靜坐苦修的傳統印象,創立少林公司、注冊少林商標、擁有自己的電視制作公司和電子商務平臺;武僧團把“功夫秀”帶往世界各地,少林俗家弟子遍布全球。現在的少林寺完全是一個架構完備的集團化企業,旗下擁有專門的外聯處、寺務處等機構,在2002年美國探索頻道為釋永信拍攝的電視記錄片中,將“方丈”一詞翻譯為CEO。如此高度商業化的寺院經濟發展模式引起大量爭議,佛門圣地被卷入市場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中也導致社會輿論界質疑聲不斷。但如今少林寺所實施的“禪商并舉”并非是一個全新的寺院發展模式,它自禪宗傳統的“禪農并舉”發展而來,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
一、“禪農并舉”的農禪制度
所謂“禪農并舉”,就是把農業勞動和參禪結合起來的禪法,也稱農禪制度,它在中國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制度的形成來看,它孕育于禪宗四、五祖道信、弘忍時期,實踐于馬祖道一時期,完成于馬祖的弟子百丈淮海禪師,之后興盛起來。道信、弘忍提倡的“坐作并重”是農禪的雛形,發展到馬祖道一法師時期,他提出的“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的禪理成為實踐農禪的佛理基礎。“即心即佛”,就是眾生自心含藏萬法,世間萬物皆是佛性的表現,由此眾生包括行住坐臥在內的一切施為、現象皆是佛性的妙用,所以成佛不假外求,只要回歸自心便可成佛。而“平常心”就指的就是本然的自然之心,也就是無污染、不造作、去執著的眾生自心。這些禪法理念使禪走入日常生活之中,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吃飯穿衣,即是佛性,在勞動作務中滲透禪機。
另一方面,傳統的禪定修行將出世和入世置于二分對立的地位,講求摒棄一切外務,專心坐禪、調身、調息、觀于一境而守心的禪法。而農禪將出世和入世視為一體,所謂“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其中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2]實踐“于世間出世”之理,即永嘉禪師所言:“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禪宗打破了佛教傳統的出世退隱后凝然靜坐的修行方式,將禪修與日常生活、生產勞動融為一體,農禪由此得以順理成章地發展起來,也為僧伽從事世俗事務提供了理論根據。
從社會背景來看,在原始佛教戒律中,無論是儲備日常用品還是儲蓄金銀財產都是不被允許的,要求僧人修“頭陀行”,以乞食為主要生存來源。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重視生產、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占據主要地位,歷代帝王都把重農抑商作為其重要國策,這種重農傾向使得中國產生自給自足的文化品格,乞食的生存方式令漢人所不齒。再加上受社會宗法制社會的影響和制約,封建王權也難以容忍一個團體可以與塵世脫離,不事生產,不受王權監管,因而佛教很難保持其游離于政治之外的獨立性。而“禪農并舉”的確立讓僧眾可以通過從事農耕以實現自養,從而使僧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對外部的依賴,強化了禪宗的生存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禪農并舉”是禪宗發展過程中一個勢所必然的事情。
二、“禪農并舉”與寺院經濟的關系
“禪農并舉”是佛教在其傳播中適應中國國情的產物,但是這并不是說,“禪農并舉”產生之前的中國佛教就完全遵守原始的佛教戒律,只能說是它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為了在中國生存和發展而做出的進一步妥協。在唐代農禪制度才被正式確立,而從東晉時期的寺院就已經涉足興販營利,有的寺院還從事質押和放貸經濟,南北朝時期寺院的“質庫”則被認為是中國典當業的源頭。資財富裕的寺院從事借貸活動,既可慈善救濟,解困生民,又可生息積財,供養三寶。發展到隋唐時期,寺院放貸已經很普遍了,主要有質押借貸和生息借貸兩種。唐代敦煌寺院還實行實物借貸,貸出的物品主要有谷物和織品兩大類,提供給借貸人生產或生活所用,一般利率為50%,即春季借二秋季還三。[3]對于當時的富貴人家來說,向寺院施舍本錢創立質庫已經是十分普通的投資事業。單由放貸業我們就可以窺見寺院經濟至唐代已是相當發達,但寺院經濟的發展難免與政權賴以生存的地主經濟產生矛盾:一方面它與國家爭奪勞動力和土地,另一方面,寺院經濟集聚了大量錢財,僧尼生活富足,吸引了大量好逸惡勞的逃避賦役者致使僧人魚龍混雜,這不僅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也對國家政權和社會安定構成威脅。漢唐之際的“三武一宗”滅佛,就是國家與寺院經濟嚴重沖突的結果。為了應對來自世俗政權限制佛教的措施,佛教界一方面展開弘法護教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在調整寺院經濟的經營模式,農禪制度便于唐代逐漸發展完善,將僧人從不事勞作的食利群體中拉出來。
雖然從表面上來看,比其農禪,唐代發達的寺院經濟似乎看起來世俗化程度更深。但農禪制度之前的寺院經濟中,僧人多為間接接觸世俗事物。例如由于佛教認為掘地傷生,政府在賜予寺院土地的同時,“往往還將附近農戶若干封賜于寺廟”,[4]僧人本身并不事生產,依賴性很強。而當《百丈清規》中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制度確立下來,僧人們已經在直接地從事世俗勞動。因而“禪農并舉”從一定程度上使得禪宗向著更加世俗化的方向邁了一步,并為后世僧人接觸世俗事物提供了更為充分的理論依據。
三、“禪商并舉”
當今的佛教正在面臨著時代環境的巨大變化,科技突飛猛進、各種文化思潮的興起給傳統佛教帶來了種種沖擊。要想在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信仰多元化的社會中繼續生存和發展佛教就必須進行現代化的思考和轉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這導致了中國20世紀“人間佛教”思潮興起,以期應對在當代社會所面臨的種種挑戰。自太虛大師以降,其思想繼承者們如印順、趙樸初等人皆致力倡導“人間佛教”之理念,之后凈慧法師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以禪宗為核心的“生活禪”修行理念,這種理念與上文提到的馬祖道一法師“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一脈相承,為今日少林寺之“禪商并舉”提供了更為充足的思想基礎。
現任少林方丈釋永信在談及少林寺商業現狀時如是說:“我們的商業運作,和一般的商業運作有本質的不同。市場經濟下的商業是以盈利為目的,而我們是以自養為目的。事實上,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農禪并重的傳統,僧人講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但是今天,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耕種的層面,我們有機會也有能力參與其他類型的自養活動,我們為此進行了一系列嘗試。”[5]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一般觀念認為佛教講求出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于任何宗派來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都是很難得到發展和壯大的,如果真正做到避世,佛教很難存活到現在。佛教過去以農業活動自養,現在的轉向商業,因而所謂的“禪商并舉”事實上也可以說是“禪農并舉”在新的社會時代中的一種適應和表現。但是被當代影視文化賦予極大符號意義的少林寺,被貼上了崇高的標簽,當其留給世人的出世的印象與入世的事實相矛盾時,它就不可避免地站在了爭議的中心。
總的來說,少林寺發展商業是一種在所難免的選擇,如同農禪的產生一樣,它也是佛教在其傳播過程中為了順應時代和社會做出的妥協發展。這樣看來,將世界各地的功夫秀和少林實業公司看作對佛教的弘揚也無不可,畢竟自1999年釋永信正式接任少林寺方丈以來,確實使少林寺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但如果要繼續發展“禪商并舉”,“自養”和“盈利”、佛法弘揚與世俗娛樂化之間的度該如何把握,也是少林寺在接下來的發展中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李騰.德媒體關注少林寺釋永信在廢墟上建經濟帝國[J].武魂,2009(12):16.
[2]釋心田.圖解維摩詰經[M].紫禁城出版社,2009.
[3]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4]何蓉.佛教寺院經濟及其影響初探[J].社會學研究,2007(4):75-92.
[5]釋永信.我心我佛[M].華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