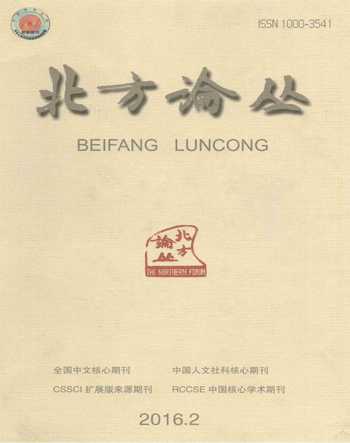陸世儀的詩學思想與詩歌創作
李倩倩
[摘要]陸世儀在詩學觀念上主要繼承的是儒家的詩教說,同時面對易代的社會環境,他又提倡孟子的知人論世說,強調借詩歌以“論人論世”,即注重詩歌抒發個人性情之真與記載社會時事的功能。這一詩歌閱讀理論影響到陸世儀的詩歌創作,其詩前期主要表現了作為理學家的性情與學問,從而呈現出清新恬淡的詩歌風貌;晚年生活困頓,情感激烈,其詩歌則緊緊圍繞自我人生之遭際與下層人民生活之痛苦而展開,呈現出沉痛隱微的風貌。易代之際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諧世與濟世相交織的人生態度,也是形成其詩歌復雜面貌的原因。
[關鍵詞]陸世儀;以人取詩,以詩取事; 清新恬淡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2-0036-05
Abstract: Lu Shiyis poetic conception mainly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poem teaching sai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ace of the replacement of the genera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e advocated Menciuss ZhiRenLunShi said, stressed that the poetry should express personal temperament and record the social events. This poetry theory affects Lu Shiyi's poetry creation, whose early poems main show his temperament and learning, therefore present a new pure and fresh poetic style. In his later years,with difficult life and intense emotion, his poetry is closely around the pain of life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lower people's living, present a deeply hidden and subtle feature. The serious and humorous of the attitude toward life which caus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generat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reason of the complex features of Lu Shiyis poetry.
Key words:Lu Shiy;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from the personal,understand the thing from the poem; pure and fresh
陸世儀(號桴亭)是理學史上的重要人物,錢穆先生尤為推崇其理學成就,認為桴亭的學說“致廣大而盡精微,會性理經濟而一之,實與向來一輩道學家不同,洵不失為朱子學之正統嫡系也”[1](p. 27)。作為明代遺民,陸世儀既不仕清,又不隱逸,而是以道自任,關心民生疾苦,體現了一種諧世與濟世相結合的人生態度。陸世儀也創作了大量詩歌,粗略計算《桴亭先生詩集》中的10卷詩歌,約有一千首。從題目上看,多為感懷、寄懷、贈答、田園與山水詩,語言也較為平淡清新,展示了一個深情而又溫和的儒者形象。陸世儀在追求理學的過程中使得性情與學問成為他主要的人生態度,而這種涵養和心態又影響到他的詩文創作,使其詩歌呈現出一種蕭散淡泊的意味。因此,錢穆先生稱陸世儀為理學詩人的代表,認為其詩與邵庸、朱熹、陳白沙等理學家的詩都展現了“心情之灑落恬淡”[2](p. 5)。“灑落恬淡”也可以用來形容陸世儀的詩歌風格,此風格既是其推崇理學家的性理之詩歌美學的展現,又是他在易代之際的社會環境中所保持的平和心態的一種體現。
目前,學界對陸世儀詩歌理論及其詩歌創作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還很少,僅有一篇論文《陸世儀的山水詩簡論》[3],該文介紹了陸世儀山水詩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但是此文并沒有結合詩人的心態,進一步探討這些山水詩所蘊涵的作為理學家的陸世儀對生命的自得與真實的體悟這一深層內涵。另外,陸世儀的詩歌內涵是多方面的,面對明清易代這樣一個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他自身的遭際,他的詩歌中也流露出沉痛幽微的一面。本文在詳細解讀其詩歌文本的基礎上,結合詩學傳統、社會政治環境及其理學思想等三個因素,詳細解析陸世儀的詩學思想,分析其理學、詩學是如何在思維、情感和審美領域融合在一起的,以此展現詩歌對于一個遺民抒發情感、安頓生命的意義。
一、人、世、詩合一:陸世儀詩學觀念的核心
身處明清易代之際,一些懷有救世愿望的詩人和有識之士,渴望通過倡導儒家詩教來復興傳統文化。如錢謙益在《施愚山詩集序》中說:“詩人之志在救世,歸本于溫柔敦厚,一也。”[4](pp.760-761)吳偉業也說:“嘗語同志,欲取惠泉百斛,洗天下傖楚心腸,歸諸大雅。”[5](p.1205)三者之間雖沒有聯系,但處于同一時空中的陸世儀同樣繼承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說,提倡的是詩言志的傳統,他在《思辨錄輯要》中說:“詩言志,詩者志之所發也。有志而后有詩,故或直敘其事而為賦,或有所感觸而為興,或有所諷刺而為比,皆言其所志耳。”[6](p. 50)同時,“此一個‘志字須合著‘思無邪三字為妙,若有邪便不是志。”[6](p. 334)又言:“溫柔敦厚四字,詩家宗印,不可易也。”[6](p.336)詩歌一方面要抒發個人之性情;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心性之正,即符合儒家的道德規范,所以在創作手法上就不能太率直,即使是運用“有所諷刺”的“比”的手法也應該是曲折幽微的。
盡管儒家的詩教觀念是陸世儀詩學思想的主線,但是他又強調詩歌是個人真實情感與思想的表達,是社會時事的忠實記錄,這一思想顯然來源于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說。陸世儀在《思辨錄輯要》中說:
嚴滄浪、高廷禮輩分唐詩為初中盛晚,以為晚不如中,中不如初盛,此非篤論也。凡詩只是隨其人為盛衰耳,有其人則有其詩,無其人則無其詩。
如初唐推沈宋,沈宋之為人何如者,其詩亦殊無氣骨。中唐如韓愈、白居易、韋應物詩皆有識而蘊藉,得三百篇意旨,豈反出沈宋下?盛唐之妙全在李、杜,晚唐自是無人物稱雄,如李義山輩皆風流浪子耳。趙畋、韓偓稍勝,然憂讒畏譏,氣已先怯,何能為詩。賢者如聶夷中、張道古又困于下位,即有詩,何由傳。故不論人論世而論詩,論詩又不論志而論辭,總之不知詩者也。[6](p. 337)
陸世儀認為,詩歌水平的高低是由詩人的品質決定的,詩人人格精神和道德品質高尚則詩歌自然高妙,若詩人無氣骨則其詩也必然卑下。同樣,由于詩歌是表達詩人所處時代的所感所遇,故由詩歌不僅可以窺探作者的意志和生命體驗,還可展現所處時代的人事物理與社會風貌,即人、詩、世三個要素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三個要素也是評價一首詩優劣的標準,其言:“漢魏詩人大抵非無因而作,故讀其詩猶可藉以論其人,論其世。至六朝及唐詩則無因而作者多矣,無可借以論人論世,故后來選詩者遂有氣格聲調諸名色,亦不得不如是也。”[6](p.335)在明末清初歷史環境中,詩歌創作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技巧與形式所展現出來的格調,而在于是否包含詩人獨特的真實情感和人生經驗,并且具有紀事功能的詩史意義,而不是空無一物。在此鼎革之際,陸世儀重提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說,整合人、詩、世為一體,通過詩歌以了解“人”(作者)和“世”,這一批評觀念是強調詩歌歷史價值的一種表現,暗合了明清之際“以詩為史”的閱讀習慣[7](p. 164)。結合陸世儀的遺民身份,我們可以知道,他顯然希望后人在讀這些詩歌時能夠體會作者的隱微的思想感情,包括身世之感和家國之悲,而不僅僅被作為美文來欣賞。
作為詩人創作背景的“世”是由具體的“事”組成的,人、詩、世在陸世儀看來就是人、詩、事,因此,他認為:“選詩必欲人與詩合、詩與事合乃可入選,不然詩雖佳,皆偽言也。”[6](p. 338)其子陸允正在《府君行實》中說:“著《詩鑒》一書,以人取詩,以詩取事,每篇之首,采史傳為序,各附小論,不合于三百篇之旨者不錄也。”[8]惜此書不傳,但從上述言論中可以看出,陸世儀追求的是詩歌內容之“真”,而非僅僅吟風弄月或無病呻吟的“偽言”,只有這樣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這就把情感的內容作為詩歌創作和評價的關鍵,而將情感的表現手法放在次要位置,無論這種手法是含蓄的還是直露的。因此,可以說“以人取詩,以詩取事”這一選詩標準,在一定意義上,是“把‘溫柔敦厚這個命題原本由道德修養出發的要求情感含蓄蘊藉改換為要求情感真切醇正”[9](p.517)。然而,易代帶來的痛苦并不能保證情感是平和的,也有無法遏制而噴發的情況出現,這時詩歌的風格就會突破“溫柔敦厚”而呈現出怨憤激烈的一面。陸世儀的詩歌就集中展示了詩人情感表達的兩面性,并將其整合為一體:他的詩既展示了他的性情與學問,又突顯了他民胞物與、悲天憫人的儒者胸懷,這些詩歌全面記錄了作為一個個體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榮辱浮沉,詩歌是其個體生命在黑暗的時代里留下的一點余光。在閱讀過程中我們發現,盡管他強調詩歌的內容,但詩歌的審美特質并沒有被淡化,在展現作者人格胸懷或是記錄現實苦難的同時,也同樣講求詩歌表達的技巧,這樣才形成了清新恬淡與沉痛隱微兩種詩歌風貌。
二、性情與學問:陸世儀主體人格精神在詩歌中的表現
所謂“有其人則有其詩”,陸世儀的詩歌集中展現的是他作為理學家的性情與學問。周西臣在《陸桴亭先生詩序》中說:“執詩以求陸子而陸子存焉,必執詩以求陸子而陸子不存焉。然則陸子安存乎?亦存乎淵然浩然之際而已矣。” [10](p. 531)“淵然浩然”是形容陸世儀“羅絡古今,囊括天地”的大氣魄和立志成圣成賢的人格精神。正是由于具有這種浩然灑落的人生境界,因此,不論其處于何時,總能使其心境保持中正平和,表現于詩歌中形成一種恬淡清幽的詩歌風貌。尤其是當經歷了明朝滅亡這一歷史事件之后,他并不像其他士人那樣僅僅是為了抒發一己之悲痛而放聲歌哭于山水之間,陸世儀是要通過寄情山水,發為歌詠,獲得自我境界的提升與自我生命之受用,山水真正能讓其心靈獲得平靜。如《和盛傳湛一亭詩二律》:
疏林落落竹森森,中有幽亭貯素琴。馮檻小花供雜綺,隔溪高樹散輕陰。
縱觀萬物皆生意,靜對淵泉識道心。一室自饒千古樂,不知人世有升沉。
湛一亭前竹樹森,主人終日坐鳴琴。清晨習靜貪朝氣,永夜焚膏惜寸陰。
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見天心。此中旋轉須教猛,不信神州竟陸沉。[10](p. 541)
此二律作于崇禎十六年癸未年(1643年),第二年即甲申,陸世儀已經感到神州即將傾覆,而人世也浮沉,但是此詩主要表現的是作者面對幽靜環境時流露出的風流自在的“道心”。
即使是表現對明朝滅亡的幽憂沉痛之情,作者的感情歸宿也是陶淵明式的和諧,如《春日田園雜興》這組詩,作者在自序中說:“遭時不偶,避世墻東。春日傷心,無聊獨嘆。偶過異公齋,示我《春興》六首,已又出《月泉吟社》一冊,曰:此至元丙戌浦江吳潛翁所輯也。時元易宋已五載,翁隱石湖,集諸隱流,吟詠寄志。一時屬和,幾及三千。嗟乎!屈陶異世而同情矣。雖時事尚未可知,而丙戌奇合,深用足嘆。亦成六首,聊志鄙懷。不敢曰首山之吟,亦用代曲江之哭耳。”其一:
墻角春風吹棣棠,菜花香裹豆花香。看魚獨立小池影,數筍間行竹筱長。
白眼望天非是醉,科頭混俗若為狂。莫嫌世外人疏放,彭澤情深勝沅湘。[10](p. 548)
這組詩寫于丙戌(1646年),而同樣是在丙戌之年(1286年),隱士吳渭以范成大《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向各地詩社征詩,隨后即有《月泉吟社》這部詩集,集中的詩歌表達的是亡國后,“廣大南宋遺民的無奈與痛心,悲苦與憤慨,絕望與反抗”[11](p. 20)。情感是相通的,宋元易代和此時明清易代又何其相似,亡國之痛因這樣的一本詩集而勾起。最能代表這種易代情感的詩人是屈原與陶淵明,而在陸世儀看來,“彭澤情深勝沅湘”,屈原離鄉去國,并最終自沉而死,雖說完成了自己的氣節堅守但卻放棄了生命和社會責任;與此相比,陶淵明雖然選擇隱居,但仍能堅守氣節,并勇于承擔人倫物理,也許他的走向田園是比屈原更為艱難的選擇。作者雖然在這組詩中表達了堅持作遺民的氣節,但從詩中所描寫的一片祥和自在的景象中可以看出,他最為欣賞的是陶淵明歸隱田園的處世方式和其真率自然的人格精神。陸世儀真正像陶淵明那樣融入到田園生活當中,他的詩表達出對自然萬物的一片深情,如寫景抒懷:
濕雨細如塵,林塘百草新。輕寒頻試酒,薄醉自宜人。柳色閑看好,梅香靜嗅真。田園滋味別,似接古風淳。[10](p. 583)
遠俗非違俗,離群更樂群。感時歌雨雪,懷友寄停云。戶有煙霞入,窗憑水竹分。晚涼無一事,倚檻待南薰。[10](p. 595)
除了對陶淵明等晉宋詩風的一種向往外,其詩歌所展示的心性之灑落和清新自然的風貌主要來自于對理學家詩歌的推崇與模仿。陸世儀認為在傳統的詩歌史中,除了合于興觀群怨的詩歌外,還有理學家所作的自成一脈的性理詩,他最為推崇的在宋為邵雍,在明則陳白沙,曾說:“邵康節《擊壤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語錄讀,然猶未免頭巾氣,至白沙之詩則合道理與風雅為一矣。其所作詩有‘子美詩之圣,堯夫更別傳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為一人也。”[6](p. 50)“詩人自唐五百年至邵康節,康節至今又五百年,敢道無一人是豪杰,只為個個被沈約詩韻縛定……詩人之無識無膽也,康節起直任天機,縱橫無礙,不但韻不得而拘,即從來詩體亦不得而拘,謂之風流人豪,豈不信然。”[6](p.339)康節的詩妙處在于從不為韻律和詩體所限制,皆從心中流出,縱橫自在,詩歌是其性情和學問的自然流露,但是他喜歡在詩中講道理,發議論,因此其詩有倫理教化的氣息。而陳白沙則能主動避免頭巾氣,其言:“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12](p.72)就是能從“個體感悟的角度言理”,在注重性情發抒的同時能保持“情感的平正含蓄,品味的超拔脫俗,也包括遣詞用語的不落俚俗”[13](p.372),即雅正的一面。白沙詩歌這種合“道理與風雅為一”的特質對陸世儀詩歌清新恬淡風貌的形成有很大影響。讀者也能從陸世儀的詩歌中體味到這種性情與學問來,如他的《立春日五鼓,夢駕舟泛大海,波濤不驚,水天一色,覺而此心曠然有自得之樂,成一絕句》:
十二年來淺水中,每嫌溪曲又多風。今朝忽得輕帆便,大海波濤一鏡同。[10](p. 559)
此詩與朱熹《觀書有感二首》其二比較相似:“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14](p.286)這兩首詩不僅押相同的韻,而且都表達了一種自身學問積累之至、一通百通的豁然開朗的得道境界。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借此詩歌表達的是一種“自得之樂”,所謂“十二年來”指明崇禎九年丙子(1636年)到創作此詩的明永歷二年戊子(1648年),這是陸世儀對傳統理學中關于主體修養和人性論問題探索的重要階段。無論是修養論還是氣質論,陸世儀憑著自我探索,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最終獲得高深悟理,所以他在上述詩歌中表達了這種不斷探索,歷經曲折并最終有所得的喜悅和滿足感。陸世儀的詩歌中這種由學問和性情的體悟而獲得某種獨特體悟的句子很多,如《昆陵讀易十絕句》:
萬象森然盡偶奇,羲文周孔漫施為。畫前有易人皆信,畫后原無世莫知。
圣人作易參天地,天地原來只此心。不向此心分黑白,韋編三絕未知音。[10](pp.642-643)
隨著性情學問的培養和人生閱歷的增長,詩歌越發成為陸世儀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期雅正平和的詩歌觀念轉變為“清吟”,注重抒發一己之胸懷,他在《詩》一詩中說:“杜公詩律老逾深,陶令風流亦可尋。豈必嘔心成絕搆,總憑天籟發清吟。長歌梁父時搖膝,漫賦猗蘭獨援琴。此道今人無可語,江間漁父是知音。”[10](p.641)無論是與朋友寒夜獨坐,賦詩酬和,還是在山水田園中徜徉,作者在詩中展現的是一種高雅的審美情趣。尤其是寫景和詠物詩貴在自得,能從景物中或日常事物中真正體會到一種美妙和愜意,并能抓住事物的特點將其表達出來,如:
不盈不竭幾千年,一掬渟泓海內傳。恰是至人方寸地,涵濡萬古只淵然。[10](p.604)
松風颯然至,山雨霏微集。此景誰不聞,妙領在心得。[10](p. 606)
即看此夕清光滿,已覺人間海宇秋。[10](p. 615)
這些詩句皆清新自然,意境高遠,灑脫有致,是其人格上博雅與通脫的一種體現。正如錢穆先生評價其理學一樣,其詩歌也同樣“使讀者惟見其言人生日常,而不見有理窟之勃窣”。[1](p. 22)
三、生存困境與生民苦難:陸世儀詩歌中的“事”與“世”
追求清新幽美的超功利境界確實是陸世儀詩歌的主要風貌,但個體生命是與世與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面對易代之際戰火不斷、滿目瘡痍的世界,作為一個儒者,陸世儀同樣用詩歌作為悲憤激烈情感宣泄的工具,他用詩歌記錄下了人民的痛苦以及個人生活之艱辛,展現了沉痛哀怨的一面。這類詩在寫法上也多模仿漢魏五言,呈現出慷慨悲涼的特點。如明亡后第二年(1645年),陸世儀寫下了《感遇詩》30首,他在序中說:“乙酉之遇,天下古今所未有也。所遇為古今未有,則所感亦為古今未有,何詩之足云。然以不生不死之人,處倏安倏危之地,欲歌不能,欲哭不可。悲愁郁憤發而為詩,固亦屈之情,陶之思也。”屈原與陶淵明成為作者效仿的對象,借詩歌表達作者面對家國破滅的悲痛心情,并表達了自己堅持做逸民的氣節,第二首寫道:
冒辱既非易,殺身良獨難。高唐有白發,稚子未知餐。攬衣起嘆息,輾轉不能寬。思欲批緇衣,寄跡空門端。君臣義已廢,棄親殊未安。俯首混儕俗,流涕傷心肝。[10](p. 543)
這首詩寫出了明亡后士人的幾種選擇:“冒辱既非易”,是指跟隨南明小朝廷的士人,事實證明這些人在新的朝廷中仍舊受到奸臣的排擠和君王的屏逐(見此組詩第六首,作者用妾與夫的關系來比喻新朝廷中君臣之間的關系:“南國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傾城令人妒,屏逐不遺力。艷去眾丑歡,妖魔斗顏色。窮巷有幽姿,聞之捧心泣。”自注:賢者見辱于時君,子為之痛心焉)。“殺身良獨難”,是寫身死國難的那些人,作者對這些人的做法表示理解但無法去效仿,因為自己有人倫的責任與道德在身,故“勿得輕死生”。也同樣是因為留戀這種親情并勇于承擔儒家的道義,以繼承圣賢之學為己任,因此也不會像其他一些士人那樣選擇遁入空門。于是不得不混跡于世俗當中,當然這種選擇也實屬不得已,“仲雍避荊吳,斷發文其身。殷箕篝昏亂,佯狂受奴髡。少連柳下惠,降辱稱逸民。微服過宋都,去衣入倮人。在昔大圣哲,處困皆有倫。區區卑賤子,含垢安足嗔。”想象一下古來圣賢都有降志辱身的遭際,因此,自己堅持做逸民的選擇又是比以上三種選擇更為合理的。整組詩承載的是詩人的“悲愁郁憤”,展示了作者面對易代現實的艱難選擇。
陸世儀改號為“桴亭”就是堅持自己人格精神的一種表現,其在作于己丑年(1649年)的《桴亭八詠》序中說明這一來歷:“桴亭,予所居讀書處也。世衰無徒,四方靡騁,聊乘此桴,當浮海爾。平居往還,惟石隱、寒、溪確庵數子。”[10](p. 560)而這亭外也不過一座危橋、一池清水、池中有荷,池邊有老梅、瘦石、古桂、修竹。這種刻意營造的自足的生存空間,隱含了對現實政權的抗拒。而其以“桴亭”為號,也是對易代這一事件的反應,是一種特殊的遺民表達,體現了作者無所歸依、暫為寄身的處世態度。在這亂世的桴亭中讀書,猶如漂浮于大海之上,自我的命運無法把握,所能做的唯有堅持讀書與著述,與此同時可以欣賞這周圍的景色以愉悅自我性情。經歷了人世的劇變,仍能從容其間,這確實是一種境界。但是,身雖隱,心卻仍系天下蒼生,其言:“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心切耳。”[8]可以說陸世儀隱居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但是他從來都以繼承圣賢之學為己任,儒家的仁民愛物的精神是其人格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憂民”是作者終身之心事,不以朝代更替作為退縮的理由。他在詩歌中寫道:
諧世自無違俗累,濟時常有活人權。[10](p.639)
黃葉丹楓秋漸深,漫勞佳客遠相尋。三更明月千秋語,一夜清燈萬古心。
絕俗何妨終遯世,救時只合在知今。堯夫有語須同勉,磨礪當如百煉金。[10](p.656)
“施為欲似千鈞駑,磨礪當如百煉金。”[15](p.243)陸世儀引用邵雍的詩是勉勵自己,不僅要有救世之志向,還要有一種不怕苦難,不斷砥礪獨立品格的勇氣,這樣才能有所作為。濟世情結與陶淵明的隱逸情懷,這兩種相悖相生的意識情緒在陸世儀身上得到了結合。因此,諧世并濟時而不是遁世違俗,才是作者的人生態度。
由于濟世心態的影響,又面對順治、康熙年間饑民的慘狀,作者于晚年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詩風也由前期的清新變為刻露。“康熙六年,作《大雪口號》十首,小注系婁中賦役之苦,皆當詩史。‘遙看美酒羊羔客,盡是磨牙吮血人,句尤奇警。”[16](p.90)作于康熙九年(1970年)的《水沒頭歌》,記錄太倉、嘉定等沿海一帶被水淹沒的慘狀,作者感嘆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官員竟然瞞報災情,趁機索取賄賂,欺壓百姓,詩中“干戈寧息四海平,反使斯民重罹禍”一句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第二年(辛亥,1671年)太倉一帶又大旱,作者作《前旱》《后旱》,語語悲愴,顯示了作者面對人民災難,悲憫沉痛的思想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依靠像自己一樣的士人來組織百姓從事抗災活動,但是,作者此時的處境也同樣不堪,救世的愿望遭遇了現實困境。其晚年坎坷潦倒,因貧困不得已為人幕僚(51歲時游幕于安義令毛如石,又于59歲時入丹陽荊氏館講學),其作自傷之詩以紀之:“十年講論共艱辛,一夕風塵盡隱淪。豈料鵝湖爭座客,盡如馬隊校書人。”[10](p. 628)本想通過著述講學來拯救世人,但最后淹沒于一己的貧困當中,其內心的失落可想而知。此時詩歌中個人身世之悲與人民之苦相交織,感情沉痛而哀怨,如:
讀禮逾年歲月悠,白頭渾欲不勝秋。良辰似水堂堂去,俗累如膠故故留。
不但時窮兼歲惡,此皆天意豈人謀。吾衰已矣蒼生病,誰為斯民進一籌。(自注:時婁中春夏大水秋冬復大風雹)[10](p. 673)
顯示出作者滄桑的心境以及面對動亂現實的悲痛與無奈。
但是即使是歷經背井離鄉、朋友之間的死生患難、亡子之痛、伴隨疾病呻吟之苦等種種困窘局面,作者仍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其言:“豈不謂愁惡,其如百慮煎。上供難暫緩,天意不吾憐。(婁中疊荒)俯仰尚多媿,(母未葬,子未娶)饑寒且勿宣。此肩方任重,降罰定何愆。”[10](p. 677)生命越痛苦就越要執著于肩上的這份責任,這份堅持貫穿了作者終生,這些沉痛隱微的詩歌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堅持隱忍而又始終如一、通達灑脫、涵養健全的陸世儀形象,這一形象是理學家、詩人、遺民等復雜身份的結合體。因此,陳瑚在《陸桴亭先生詩序》中說:“桴亭之人,可自傳其詩;桴亭之詩,可自傳其人。”又說:“如以詩人目之未為知桴亭者也。”[10](p. 530)
由上所述,陸世儀詩學思想的價值在于將人、世、詩三者整合為一體,確立了“論人論世”的詩歌批評觀念,使個人情感的表達與社會時事的記錄成為詩歌創作的主要任務。盡管陸世儀的詩歌在當時詩壇上并不突出,但對于一個生于易代之際而又能保持修齊治平精神的理學家而言,他的詩歌就和那些堅守本性的詩人一樣,“保持了較為真實的創作情狀,使后人能夠通過他的詩作認識到那一時期的文人是如何滿足其精神生活需求的。”[17](p. 5)陸世儀的詩歌是其個體生命與亂亡的社會現實相碰撞所產生的火花,集中表現了他的性情與學問、經歷與體驗,是其獨立人格、抗爭精神和情感宣泄的載體,展現了詩歌對于一個遺民的意義。
[參 考 文 獻]
[1]錢穆.中國文學思想史論叢·八[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2]錢穆.理學六家詩鈔[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時志明.陸世儀的山水詩簡論[J].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6(3).
[4]錢謙益.牧齋有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吳偉業.吳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陸世儀.思辨錄輯要[M].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2004.
[7]張暉.中國詩史傳統[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8]陸世儀.陸子遺書[M].光緒乙亥刻本.
[9]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9.
[10]陸世儀.桴亭先生詩集[C]//續修四庫全書:第13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鄒艷.月泉吟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陳獻章.陳獻章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3]左東嶺.中國詩歌通史·明代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14]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二十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6]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
[17]左東嶺.論于謙的詩歌創作與詩學史地位[J].北方論叢,2010(4).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洪 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