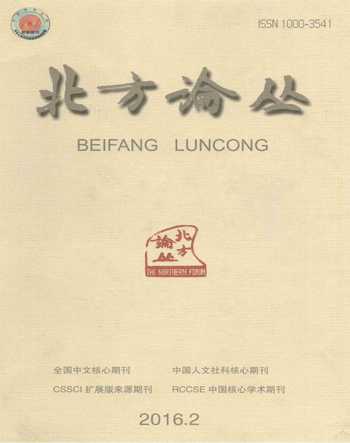黨·政·軍三者之博弈
李曄曄 劉俊梅
[摘要]國民大革命過程中,國民黨的黨治模式從廣東一隅推向南方數省,在此前后隨著國民黨內權力結構的持續變化,“以黨治軍”“以黨統政”等黨治原則逐漸被修改。長沙《大公報》在北伐期間的大量報道,以輿論的角度呈現了湖南地區黨政軍三者之間的博弈,展現了黨治模式推廣過程中多種矛盾的交織,以微觀視角再現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面貌。
[關鍵詞]國民大革命;長沙大公報;黨治模式;國民黨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2-0116-05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黨治模式是孫中山等人“以俄為師”的結果。北伐前,黨治模式即已充分運用于廣州國民政府的政治運作之中。北伐開始后,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黨治模式也順利地運用于湖南、江西、福建等新占地區。目前,學界對于國民黨黨治模式的考察,多局限于制度、理論上的靜態考察,著墨于南京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對于北伐時期的黨治模式推廣的動態研究較少。筆者認為,黨治模式的推廣必須置身于北伐具體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因此,從輿論視角出發,對黨治模式在湖南地區的推廣進行歷史還原,顯得尤為必要。
長沙《大公報》創辦于1915年9月1日,李抱一、龍兼公、張平子等人一度擔任主編。1927年3月2日停刊前,該報注重對時事進行評論報道,多以獨立姿態呈現。1926年7月北伐開始后,長沙《大公報》對于北伐時期湖南的社會、政治變化情形報道全面,特開設了《各地特約通信》專欄,將湖南基層各縣的情形做長時期報道,較為客觀地展現了湖南地區黨、政、軍三者的矛盾沖突。本文主要通過長沙《大公報》在北伐時期對湖南情形的報道,就國民黨黨治模式推廣予以考察。
一、“以黨統政”與基層黨政矛盾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北伐軍迅速進入湖南地區。隨著軍事上的勝利,湖南各地國民黨黨部紛紛建立,組織迅速侵入地域社會之中,并很快建立一套新的權力機構、社會政治秩序。在此之前,國民黨黨部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就頗為微妙,在“以俄為師”,國民黨實行改組后,廣州國民政府的黨政關系呈現出二元性的特征:一方面是在中央層面采取以黨統政的策略;另一方面,在省以下卻明顯不同,采取了平行的雙軌制,地方黨部的功能大多停留在主義的宣傳、民眾動員組織、民眾運動推動三個方面,遠未實現一元化的領導,實際權力仍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北伐軍剛進入湖南之際,湖南省國民黨黨部對于基層黨政關系曾有明確解釋:1926年7月23日,湖南湘潭收復不久,湘潭國民黨黨部曾致函該縣縣長,提出縣政府應受國民黨黨部的指揮,“省黨部聞悉,特于昨致電制止,并申明黨部與政府之關系,其文曰,湘潭國民黨縣黨部覽,聞報載該黨部致函縣長,有縣政府須接受的指揮云云,查縣政府系直接歸省政府指揮,而省政府又系直轄于國民政府,黨部與政府實各有組織系統,若縣政府受縣黨部之指揮,或省政府受省黨部之指揮,有礙政府之組織系統,殊屬不合,以后該縣黨部如有須與縣政府商決,或互有關系之事件,可與縣政府商議,不可以命令行之。”[1]
北伐軍軍事上收復湖南等地,并不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徹底轉變和基層政治生態的根本變化,在縣以下廣大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未有大的變化,也沒有撼動地方的權力格局。國民黨黨部成立之后,面臨著如何處理與原先地方精英關系,復雜的社會階層矛盾既影響了當地政治生態,也對國民黨黨政關系造成嚴重影響。湖南石門地區的黨政沖突從整個湖南地區的視域來考察比較有代表性。
湖南常德石門縣地處湖南西北,離湖南政治中心長沙較遠,即使如此,在國民大革命的風潮下,石門境內的政治生態也掀起極大波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培訓中,自1925年4月第四期開辦始,湖南籍學員明顯增多,其中即有湖南常德籍學員,常德石門境內國民黨黨部也在逐漸建立,籌建經過,最早可上溯到軍閥趙恒惕統治湖南時期,“趙恒惕在湘的時候,我們的黨,雖不能公開活動,但是我們黨的主張,都在群眾中充分的宣傳出來!黨的組織,卻隨著趙恒惕壓迫的程度而日益發展了!”[2]1926年5月,石門縣設立了國民黨縣黨部籌備處[2],9月北伐軍進抵石門[3],石門縣國民黨黨部正式成立。僅僅數月之后,至1926年底,石門縣縣黨部與縣政府就產生了嚴重矛盾,甚至于縣政府將縣黨部兩名人員拘捕、監禁,縣黨部其他黨員紛紛逃散,石門當地駐軍甚至要求“確實鋪保出具切結,方允釋放。”[4]
縣黨部與縣政府紛紛向上級反映,互相攻擊。縣黨部指責該縣土豪劣紳“聯合縣長彭石渠、團長劉珊,盡力破壞黨務,摧殘農運,且嫉吾同志奮斗。唆使已撤農特員熊潤民,伙同熊輪傳、陳拔萃等,組織非法偽黨。發出打倒縣黨部,解散農協,取消各學校……傷農協二人,封鄉農協會,更按冊緝捕黨員。”[5]石門縣縣長彭石渠、駐防軍九軍一師八團長劉珊則宣稱:“陳峨、熊彥明等假縣黨部名義集眾鬧署、逼印,業迭電呈在案,唯伊等投機入黨,違反民意,種種行為不啻為新土豪劣紳。”[5]
兩者對比可以發現,黨部與政府之間矛盾尖銳,當時的看法是“外間有傳黨部人員,擬捉王立齊(乩壇掌壇者),盛再生游街(亦文壇中人)之說未見實行。惟將乩仙壇改為第一高小校址,將同善社取消而已,此縣黨部人員與舊紳士不相融洽之大原因也。”[6]其中還夾雜著原有的社會矛盾和權力斗爭,“省特派員農民協會長熊潤民,系王立齊之女婿。與舊紳士較為接近。本擬將乩仙壇改為農民協會會址,兩次召集農民歡迎熊會長,均被阻未成,后經彭縣長石渠從中調解,始未釀成事端。黨部中以農工部長吳協眾最為激烈,熊潤民之不能履行職權,吳頗有力。”引發此次黨政風潮的直接原因是“最近新關區,搗毀團局事發生。駐石團長劉玉珊,縣長彭石渠奉警備司令陳昆化令,緝捕新關區農協委員長閻于榜及吳協眾。迨閻就捕,黨部熊彥明、陳廷謨等十余人前往縣署要求釋放,并取消捕吳令。熊、陳二人語言激烈,劉團長、彭縣長遂將二人收押。”[6]
黨政矛盾爆發之前,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有意在湘西地區設置黨務專員負責協調黨政關系,1926年9月23日,省黨部執行委員王基永被任命為湘西黨務專員[7],“特電湘西各軍官,各機關請予保護。”[8]其實,在此之前,王基永就在湘西視察黨務工作[9]。同年10月,湖南省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關于縣市黨部與縣長關系之決議案》對基層黨政形態作為規范,提出“縣長與市縣黨部立于同等地位,遇事以協商方式解決”;“縣長須尊重市縣黨部之地位,接受其指導監督。”[10](p.50)即使如此,黨政矛盾仍無法避免。石門地區國民黨黨政矛盾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
第一,從政治生態的演變角度考察,國民黨黨部的建立與黨治模式的推廣、國家權力的重構有密切關系。基層黨部的建立是國民黨欲借黨治模式來重構國家權力的基本步驟,意圖將國家意志透過國民黨基層黨部直接貫徹到地方。但國民黨在北伐途中軍事上高歌猛進,僅將北洋軍閥勢力擊潰、驅逐,并未對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的政治生態根本改變,尤其是未能將縣以下廣大地方精英把持的政治體系摧毀、重構,這也導致上層的軍事——政治集團雖然瓦解,但下層的政治基礎仍然頑固存在。這是國家權力重構過程中,國家意志與地方勢力的沖突,也是國民黨難以解決的政治難題。
第二,社會矛盾的沖突的形式演化。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原先政治權力體系中,并無國民黨黨部的一席之地,國民黨黨部是建立在國民革命軍軍事勝利的基礎之上,國民黨黨部的出現嚴重影響了當地的政治體系,使得原先在社會中尋求政治參與、政治權力的社會階層找到了新的平臺,社會階層的沖突以黨政矛盾的形式表現了出來。考察石門縣的黨政情形,其黨部人員多是以青年學生等在原先政治結構中,未占主導地位的激進分子組成,“石門縣黨部成立以來,黨員分子以學界青年為最多。一班舊紳士較有實力者如盛再生、王渠吾、王立齊、郭東史、熊輪才、龔星伯等概未加入。”[6]
近代以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二元特征日益明顯,相對于城市中工人階級的成長,廣大鄉鎮仍是農民階級占據絕大多數,縣以下的社會沖突大體集中在農民與地主之間。而在清末以來社會結構、社會政治發生變化過程中,隨著科舉廢除,縣以下的鄉村中青年學生、教師為代表的中下層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系統中,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地位,渴望通過新的途徑,越過當前政治體系重獲得政治參與與政治權力。國民黨黨部甫一建立,為履行使命并確立權威,往往立即展開民眾運動,民眾運動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除了激動人心的政治口號,更多的是民眾運動帶來的資源再分配和權力結構調整,而在政治體系中失勢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憑借國民黨黨部平臺深深地介入這場沖突之中,也致使一般的士紳及既得利益者與國民黨黨部極易產生沖突。
湖南省國民黨黨部及湖南省政府對石門黨政沖突的處理意見是:“陳廷謨等,以代表資格晉署陳詞,尤不宜擅予拘押……政府查核情勢,當將該縣長彭石渠免職,改委劉夷同志接署,藉平民憤。而尊黨紀。”[11]但這種處理方式治標不治本,僅將縣長免職、黨部被羈押人員釋放,并沒有解決石門地區的黨政矛盾、社會矛盾。僅僅過了一個月,石門地區矛盾更激烈地表現出來:1927年2月26日,石門縣國民黨黨部采取了更大的行動:“本月十三日,據屬縣新關區農民協會委員長閻昌奎、副委員長鄧恒泰等率同區農民協會會員二百余人來署,口頭報稱本縣土豪龔星伯、曾茂齊、王告吾等,業于今日同時捕獲,當經民眾公決,立予就地擊斃。”[12]
從湖南石門一隅的黨政矛盾來考察北伐期間的基層黨政矛盾,可以看出國民黨黨部被卷入地域社會原有的矛盾、沖突之中,并由于國民大革命的推進和黨治模式的推廣,使得原先暗潮洶涌的社會矛盾激烈迸發,作用于國民黨基層黨政之間原先就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最終以黨政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
二、“以黨治軍”與黨、軍糾紛
如果說國民黨基層黨政矛盾的爆發存在社會原有矛盾演繹的痕跡,那么國民黨黨部與軍隊之間的糾紛和湖南地區原有的社會結構沒有太多的聯系,國民黨黨部與國民革命軍均是外源性的政治力量,雙方糾紛是在原有體制框架之內的沖突,其源于“以黨治軍”原則的不斷弱化。而且在基層政治生態中出現了大量的黨、軍之間的糾紛沖突,這與國民黨黨治模式在基層上的運作和國民黨權力結構的變化有密切關聯。
就湖南地區而言,湖南南部的衡陽地區發生的駐軍搗毀縣黨部事件比較集中反映了這種矛盾。衡陽縣黨部原在農民協會處辦公,“因學前街舊奉祀官署駐軍退出,商承八軍軍部留守處唐副官丙炎許可,將部移設該處。”僅過兩日后,“八軍四師三六營胡營長率劉連長、全部械兵,捧令馳至將黨牌折倒,監察委員胡光煊與之交涉,毒毆垂斃。常委等趕向軍部留守處劉副官求救,到時全街交通斷絕。青委戴俊、組委蔣琨,均被捕去。同時并將市部、縣部、學聯會、雪恥會、慶祝北伐勝利大會籌備處、縣農協會概行分兵圍住搜毆。”[13]“農民協會陶慕衡被毆,市黨部王陽被毆,右手已斷,萬先賢被刺刀傷目,已盲。”[14]事件發生后,衡陽縣國民黨黨部及各團體紛紛向廣州國民政府、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及湖南省政府、省黨部申訴,要求“嚴辦胡營長、槍決劉連長,因傷致死者撫恤金二萬元,成廢疾者撫恤金一萬元,警廳布告肇事原因。”[14]衡陽縣國民黨黨部特派人員赴省城長沙制造輿論,“前日下午四時,衡陽特派代表羅松濤假省教育會幻燈場開招待各界茶會,各團體各學校代表到場約百余人。”羅松濤向各界報告衡陽事件的經過,各界代表紛紛表示“此系反動派之結合向我們進攻。”會議結果是:“一、以代表大會名義發表宣言;二、電請唐軍長劉師長嚴辦;三、請愿。”[15]
此事事實清楚、證據充實、責任明確,但處理的過程及結果卻耐人尋味。湖南省警察廳周廳長提出:“對于懲辦兩條,要求刪去,以后各條尚可商量。”[14]湖南省政府及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認為此事影響重大,必須派員調查,“現省黨部已推何叔衡、吳鴻騫二人為查辦員,省政府派副官王炳南為查辦員,即日會同赴衡查辦。”[16]
在派員調查的同時,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數次召開會議討論此事,反應激烈,認為該事件“非單純的偶然的無知士兵不諳軍紀、黨紀之沖突,實為當地土豪劣紳及反革命派暗中挑唆,致釀成該胡營長劉連副等帶兵搗毀毆捕之蠢動。”“此事即反革命派向革命派反攻之始。”在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及湖南省政府發出通電要求三項處理原則:“(一)請將帶兵行兇之工兵營營長胡德春及該營劉連副等主要犯逮解來省。聽候查辦。(二)分別撫恤毆傷職員。(三)請通電各軍長官保障黨部安全,嚴禁與當地土豪劣紳反動派分子勾結,并加意政治訓練,使軍隊認識黨之尊嚴,與黨部發生爭執時,須呈候上級長官咨請省黨部核辦,不得有越軌行動。”[17]很快省黨部特派員何叔衡將“調查報告書,郵寄來省”,“昨省政府又特派軍事廳少校副官(原軍事廳少校科員),調查此案真相,以憑辦理。”[18]
湖南省國民黨黨部的處理要求與唐生智、蔣介石等軍事主管的處理的意見并不一致,10月12日,唐生智向衡陽縣黨部發出慰問電:“具悉敝軍工兵營,與黨部發生沖突,毆傷同志,事出敝軍,深為抱歉,已令軍事廳,迅事查明嚴刑懲處,對受傷諸同志,優給醫藥費,并飭軍隊,加意軍事訓練矣。”[19]13日,唐生智為此事向留省部隊發令訓誡:“各部隊務須尊重黨部,密切聯絡,與民眾團體竭誠合作,如遇有爭執之處,須呈報上級長官核辦,不得發生沖突。尤不得袒護當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非法行為,致妨軍譽,并須加緊爭執訓練,使官兵均能深明主義,確守黨紀軍紀保證我八軍愛護民眾之光榮歷史。”[20]作為總司令的蔣介石發電指示:“如果屬實,殊屬非是,除飭唐總指揮查辦具復外,特此電聞。省政府前派軍事廳副官王炳南赴衡調查,昨已查竣回省,當具報省政府核辦。”但蔣介石對于該事情的處理定了基調,認為“該案大致系由誤會釀成。”[21]蔣介石的電文對最后的處理結果有重要影響,以誤會作為事件的定性,將一個影響較大的黨軍糾紛就此消于無形,肇事者并未受到嚴重處分。
從湖南全省來看,衡陽事件、石門事件絕不是個案,僅是其中影響較大,波及較廣的典型事例,長沙南部的株洲攸縣、北部的岳陽湘陰縣等地也出現國民黨黨部被搗毀事件:攸縣“團防局局長王浩突派團丁多名,搗毀新市區黨部。”[22]攸縣縣長廖晉卻置之不理,“激全體黨員公憤,勢將暴動。”[23]湘陰縣永豐區黨部控訴“謝湘頻搗毀黨部”“以打倒永豐國民黨為口號”“非將永豐國民黨員一網打盡不止。”[24]從北伐過程看,國民黨基層黨部在黨治模式推廣過程中,并沒有強有力的支撐,以至于國民黨基層黨部在黨政、黨軍沖突中屢屢成為弱勢的一方。早在廣州國民政府奉行黨治模式之初,在省以下的黨政之間的權能劃分中,隱藏了雙方必然發生沖突的因素:沒有行政資源可供汲取的國民黨黨部對同級政府沒有真正制約手段,在政治運作過程中,只能依賴于民眾運動在政治格局中獲得一席之地,通過對民眾的組織、動員,對民眾運動的規模、方向的把握,實現對民眾運動的領導,同時,國民黨黨部在民眾運動中,沖擊原有的秩序來獲取與同級政府并駕齊驅甚至超越的權威。與廣東地區不同的是,北伐時期的國民黨政權是憑借武力來實現對湖南地區的占領,因此,在廣東普遍存在的國民黨基層黨部與原先地方政治精英共享政治資源的局面在湖南地區很少發生,在北伐過程中,原先的統治機構、統治形式被推倒,如省、市、縣議會均被明令取消,“湖南省議會系根據舊省憲法產生,與現行制度不合,省憲既已消滅,議會無從附屬,應即明令取消,以杜假借。”[25]黨、政雙方都迫切要在這一片剛收復的土地上填補權力的空白,因此,國民黨黨部主導的民眾運動的發展往往超出界限,也造成基層黨政矛盾的叢生。對行政體系無法制約的國民黨黨部,在與軍事機關沖突時更無法獲得行政機關的支持,獨立面對二者的攻擊,尤其在矛盾解決時候突出反映。
三、權力結構運行中的復雜面相
在國民黨標榜的黨治模式中,處于中心位置的是黨權,其原則在于“以黨統政”“以黨治軍”,黨政、黨軍的關系矛盾的源頭在于國民黨的黨治理論中,國民黨黨權對政府、軍隊二者的制約。在政府與軍隊之間則沒有這樣的困擾,在長沙《大公報》的報道中,甚少見到國民黨地方政府與駐軍之間的激烈矛盾,反而在一些具體事務上存在合作跡象,在前述石門黨政風波過程中,石門當地的駐軍即與石門縣政府合流。甚至于在政府舉辦公債時,積極予以協助[26],雙方對某些具體事務也能予以協調,如賀龍、楊其昌兩師長在常德設立的軍資統籌處“與省方之軍資處相違,昨特令兩師長即日撤銷,并飭令常德縣長查明辦理。”[27]即使有駐軍滋擾政府部門的事件,一般都能很快處理,比如,長沙地區1926年9月3日,曾有傷兵搗毀縣署、毆打職員的事件,衛戍司令部處理極嚴:“除將首犯周勝春槍決外,其余劉自新處徒刑一年,羅金生處徒刑一月,寄押陸軍監獄署。”[28]有效制止了此類事件的發生,與黨軍、黨政糾紛的處理相比明顯堅決果斷。
軍政之間主要在于軍權逐漸凌駕于黨權、政權之上,形成以軍控政的格局,前文已述;另一方面,軍政矛盾來源于客軍的存在和對行政體系的牽制與控制。
從1926年7月北伐軍進入湖南地區,至9月湖南各地相繼收復,這一時期軍事戰爭激烈,“每克服一縣,即設置縣長一員,以執行全縣之政務,縣長由前方軍政治部主任選委之,選委之后應即呈報總司令部政治部備核,轉呈總司令部察核,加委或改委”[29]: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委任姚炳麟代理靖縣縣長、張化球代理黔陽縣長,“又慈利縣長隨軍出走,經賀師長龍委任李龍飛代理。”[30]“第九軍彭軍長委任陳萬鐘為鳳凰縣長”,“賀師長龍委任符學鵠為臨澧縣長。”[31]軍事長官出于形勢需要在占領地實施管制、處理行政事務仍屬于情有可原。但到12月份,湖南省政府成立后,軍人干政的情況仍愈演愈烈,相繼發生數起軍事長官隨意任免縣長、將省政府委任縣長驅逐情形,湖南民政廳發電痛斥“縣長既經省政府任命,職責所在,關系非輕,何得與他人私相授受,來去自由,殊為悖妄。”[32]雖然湘西的將領王天培、彭漢章等曾公開聲明不干涉行政權力:“為尊重湘省政府政權起見,承認湘西一帶縣長、局長等行政司法各官吏統由湘省政府委任,以統一政權。”[33]但事實情形又與省政府所言絕然不同,湖南省民政廳馮廳長即指出:“湘西客軍自由任免行政官吏,不獨常德一縣為然,如王天培委任楊梅珊為縣長,毛鴻翔又委陳開鈞……又如芷江王天培委任張朝升,袁祖銘又委張永松,湘政府委任之錢唯麒,被拒返省。又如黔陽,王天培委任張化球,袁祖銘又委申思,湘政府所委之劉則愚被拒返省。又如麻陽彭漢章委任鄭赫,袁祖銘又委顏瑜,霸據縣印……總之,如該軍勢力所到,民財兩政無不恣意把持,湘政府屢與協商,迄無效果,不徒破壞湘省政權之統一,阻礙訓政之進行,且似此擾亂黨軍后方,違反鈞座命令,對于大局障礙尤多。”[34]
有礙于軍人干政現象嚴重,12月16日、17日北伐軍前線總指揮唐生智相繼兩次通電,嚴禁軍人干政:“政治敗壞,原因不一,而軍人蔑視行政威權,紊亂行政系統,實為主要原因……一切用人行政,悉由政府主導,吾輩不當過問……凡屬軍人以外之事,絕對不聞不問,征收機關人員,尤不可輕易舉薦,如其實有賢者,亦只可函達主管機關,請其考察存記,絕不可指缺薦人。”[35]“文武官吏,各有職權,用人行政,不容紊亂,乃者軍閥割據,舉民財各政,悉納于軍權之下,以達其任用四人營謀私利之心……凡我武裝同志,急宜脫離舊習,自今以后,其各恪守范圍,尊重行政系統,軍隊所至地方,一切民財政務絕勿干涉。”[36]但其效果并不彰顯,僅數日之后,就發生第九軍軍長彭漢章任意更換綏寧縣長一事,湖南省政府向彭漢章發電“請尊重湘省主權”,湖南省民政廳“電綏寧各團體拒絕更委。”[37]而彭的部下鐘靈攜所部駐扎桑植,“霸管全縣民刑訴訟,派員設置種植局,收取苗捐。政府命令,既被阻撓,地方官吏,不能行使職權。”[38]惹起糾紛不斷。
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收編了大批湘軍、黔軍等軍閥部隊,一度軍隊數目急劇膨脹,但在軍令上并未做到一元化,收編的將領仰照此前政治運作方式,以軍權為后盾支配政權,進而有割據地盤趨勢,由此產生軍政之間矛盾,但這類型的軍政矛盾,隨著彭漢章、袁祖銘等人或死或囚逐漸平息。北伐過程中,蔣介石依靠軍權逐漸成為國民黨人的強人,在內部,更是軍權日益超過黨權,集中表現在軍隊中的變化。同時權力結構的持續變化,使得蔣介石逐漸以軍權凌駕于黨權之上,更加徹底腐蝕黨治的基礎,這也影響基層黨政關系不斷出現新的矛盾。
四、余論
黨治模式并不是中國自身政治發展自然形成的結果,是一種外源性的政治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引進是為了克服此前國民黨黨力不足的弊端,解決國內軍閥割據、國將不國的混亂狀況。在引進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資源、權力的相對集中,但這種體制雖然以蘇聯為模板,在國民黨初創時期就與蘇聯有諸多不同。至國民大革命發展的短短幾年中,以黨統政、以黨治軍原則雖然建立,但沒有在政治實踐中反復錘煉,黨治模式沒有形成權能明確、結構穩固的政治體系,在國民黨主要領導人的動搖下,終究會回歸到政治傳統。北伐期間,黨、政、軍三者在政治格局一直處于博弈地位,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之間的權力、地位的沖突,社會階層矛盾的演化,更是三種政治力量在即將到來的更大的政治舞臺的權力斗爭預演。
[參 考 文 獻]
[1]省黨部致湘潭縣黨部之要電[N].長沙大公報,1926-07-23(7).
[2]王基永.最近湖南之政治概況和黨務概況[J].政治周報,1926-05-24(13).
[3]常德通信中之湘西軍訊[N].長沙大公報,1926-09-04(6).
[4]石門[N].長沙大公報,1927-01-07(7).
[5]石門縣黨部與縣署之大糾紛[N].長沙大公報,1926-12-31(6).
[6]石門公法團全體離職之大風潮[N].長沙大公報,1927-01-06(7).
[7]湘西設立黨務專員[N].長沙大公報,1926-09-23(6).
[8]省政府請電保護黨務專員[N].長沙大公報,1926-10-10(7).
[9]各縣特約通信(湘鄉)[N].長沙大公報,1926-09-16(3).
[10]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Z].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秘書處,1926.
[11]省黨部解決石門黨部大風潮[N].長沙大公報,1927-01-14(6).
[12]石門農協會處決三大劣紳志[N].長沙大公報,1927-02-26(6).
[13]衡陽駐軍搗毀縣黨部[N].長沙大公報,1926-09-25(3).
[14]衡陽駐軍搗毀縣黨部三志[N].長沙大公報,1926-09-28(3).
[15]衡陽代表招待各界茶會記[N].長沙大公報,1926-09-30(6).
[16]衡陽駐軍搗毀黨部之續聞[N].長沙大公報,1926-09-27(6).
[17]衡陽黨部被搗毀案之近訊[N].長沙大公報,1926-10-02(2).
[18]省政府派員調查衡案[N].長沙大公報,1926-10-06(6).
[19]唐軍長對衡陽駐軍搗毀黨部案之來電[N].長沙大公報,1926-10-12(6).
[20]唐軍長訓誡留省部隊[N].長沙大公報,1926-10-13(6).
[21]總司令對于衡陽駐軍搗毀黨部之來電[N].長沙大公報,1926-10-13(6).
[22]攸縣團防局搗毀新市區黨部[N].長沙大公報,1926-09-29(6).
[23]攸縣搗毀區黨部之糾紛[N].長沙大公報,1926-10-07(6).
[24]永豐區黨部被人搗毀[N].長沙大公報,1926-10-09(6).
[25]取消省議會之明令[N].長沙大公報,1926-08-09(6).
[26]湘西將領協助舉辦公債[N].長沙大公報,1926-09-25(3).
[27]常德軍資統籌處撤銷[N].長沙大公報,1926-09-29(6).
[28]衛戍司令部處置傷兵搗毀縣署案[N].長沙大公報,1926-09-03(6).
[29]總政治部重要文件公布[N].長沙大公報,1926-08-20(6).
[30]關于縣長新換委[N].長沙大公報,1926-09-11(3).
[31]彭賀兩軍官改委兩縣長[N].長沙大公報,1926-09-27(6).
[32]民政廳電斥私授官職縣長[N].長沙大公報,1926-12-16(7).
[33]湘西將領不干涉行政[N].長沙大公報,1926-09-20(2).
[34]馮廳長電呈客軍把持湘西民財兩政情形[N].長沙大公報,1926-12-17(3).
[35]總指揮嚴禁軍人干政[N].長沙大公報,1926-12-17(3).
[36]總指揮嚴禁軍人干政又一電令[N].長沙大公報,1926-12-16(6).
[37]請客軍尊重湘省主權[N].長沙大公報,1926-12-25(6).
[38]省政府電請撤懲九軍干政軍官[N].長沙大公報,1926-12-21(6).
(李曄曄:長春大學講師,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歷史學博士;劉俊梅:長春大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