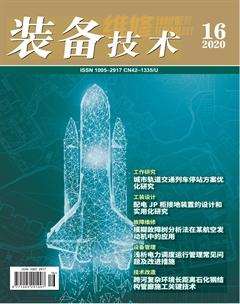汽輪機快冷新方式在實踐中的成功應用
姚國杰 姚金成

摘要:我廠4號機組為哈爾濱汽輪機廠提供的NZK660-24.2-566/566型汽輪機,配套哈鍋生產的HG-2110/25.4-HM15型鍋爐。機組設計中未配備停機快冷系統。為了停機后盡快達到檢修條件,決定在打閘停機后利用排汽裝置中的負壓將空氣經鍋爐頂棚管入口放空氣閥、低溫再熱器入口集箱疏水閥吸入鍋爐,利用鍋爐余熱將空氣升溫后再經主蒸汽管道、再熱蒸汽管道吸入汽輪機高中壓缸,對汽輪機缸體進行冷卻。通過科學計算并控制各設備溫降速率,達到了優于快冷裝置的效果。
關鍵詞:快冷;溫降;冷卻速率;缸溫;壁溫
1安全性分析
利用鍋爐余熱冷卻汽輪機缸體的方法在實施中主要以控制汽輪機轉子冷卻速率為基準,在保證轉子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實施。經國內電科院等科研單位對600MW級超臨界汽輪機、1000MW級超超臨界汽輪機轉子冷卻速率研究,基于ANSYS有限元方法計算高壓內缸及高壓轉子溫度場及熱應力場研究結果表明,在7℃/h的冷卻速率下,高壓內缸及高壓轉子的熱應力峰值遠小于材料的屈服極限,對轉子壽命的影響微乎其微。鑒于電科院的研究成果,我廠決定在4號機組停機過程中利用鍋爐余熱對汽輪機缸體進行冷卻。
為確保絕對安全,在4號機組停機快冷中以鍋爐受熱面壁溫溫降速率不超過1℃/min,汽輪機轉子溫降不高于3.5℃/h為基準控制。
2新快冷方式實施方式
本次停機快冷以鍋爐外空氣為氣源,通過排汽裝置中建立起的負壓將空氣通過鍋爐頂棚管入口放空氣閥、低溫再熱器入口集箱疏水閥吸入鍋爐,經鍋爐余熱加熱后通過主汽閥、調節閥進入汽輪機。高壓缸冷卻空氣經高排通風閥、缸體疏水閥至排汽裝置,中壓缸冷卻空氣經三段抽汽逆止閥前疏水閥、四段抽汽逆止閥前疏水閥、聯通管、低壓缸至排汽裝置。溫度變化由調門開度進行控制。
3冷卻流程
4 新快冷方式實施過程
⑴ 自然冷卻階段
利用滑參數停機時應盡量將調節級金屬溫度降低(本次滑參數至316.4℃),打閘后盤車投入,在停機后24小時內(鍋爐受熱面烘干),保持軸封蒸汽投入,保持真空泵運行,維持排汽裝置背壓在50~60KPa 。
監視調節級后金屬溫度下降速率≤3.5℃/h。
⑵ 快速冷卻階段
鍋爐受熱面烘干結束后,即開始用熱空氣對汽輪機高中壓部分進行冷卻。
高壓調節閥全開利用左右側高壓主汽閥進行手動調節,中壓主汽閥全開,左右側四臺中壓調節閥手動調節,注意高壓和中壓的左右側閥門開度必須一致,以確保進入汽缸的氣流均勻,調節進入高壓缸和中壓缸的空氣流量,保證汽缸調節級后金屬溫度下降速率≤3.5℃/h。
高壓缸冷卻:開啟爐側頂棚管入口放空氣閥,緩開高壓主汽閥,緩開高排通風閥,打開缸體疏水閥,監視高壓缸調節級后金屬溫度變化速率≤3.5℃/h ,上下缸溫差≤35℃。監視鍋爐側低溫過熱器入口、出口、屏式過熱器出口、高溫過熱器入口、出口及各管壁溫的下降速率≤1℃/min。
中壓缸冷卻:在高壓缸冷卻同時進行中壓缸冷卻。開啟爐側低溫再熱器入口集箱疏水閥,打開三段抽汽、四段抽汽逆止門前疏水閥,同時緩開四臺中壓調節閥,以高中壓外缸上下半金屬溫度(中排處)和中壓排汽溫度做為中壓轉子的溫度監視點,保持溫降速率≤3.5℃/h 。監視爐側低溫再熱器出口、末級再熱器入口、出口溫度及低溫再熱器、末級再熱器壁溫的下降速率≤1℃/min 。
⑶ 快冷結束階段
當高壓缸調節級后金屬溫度<150℃時(本次檢查盤車),快冷工作結束,破壞真空,恢復各閥門原始狀態。快冷結束后應對高壓缸調節級后金屬溫度觀察四小時,無異常后汽輪機盤車裝置停運轉入檢修階段。
5新式快冷方式中的參數控制
⑴ 軸封蒸汽溫度控制
自然冷卻階段和快速冷卻初期,高中壓軸封供汽溫度低于高中壓缸外壁金屬溫度(高壓側)60~80℃。
快速冷卻后期可以停止軸封系統運行,在停運軸封系統前將排汽裝置背壓維持在60KPa,各部位溫降無異常后,排汽裝置背壓可以正常調節。
⑵排汽裝置背壓控制
排汽裝置背壓是控制進入汽缸的空氣流量的手段,可以根據溫降速率進行調整,調整范圍:35~60KPa。
⑶進入汽輪機的冷卻空氣溫度控制
空氣經鍋爐余熱加熱后進入汽輪機高中壓缸,高壓缸進氣溫度控制以調節級后蒸汽溫度與調節級后金屬溫度差為監視點,兩點溫度差≤56℃。
⑷轉子冷卻速率監視
轉子冷卻速率監視點以高壓缸調節級后金屬溫度、高中壓外缸上下半金屬溫度(中排處)和中壓排汽溫度做為溫度下降速率的監視點,下降速率≤3.5℃/h 。
⑸上下汽缸溫差監視
上下汽缸溫差≤35℃。
⑹其他監視參數
停機冷卻階段還需對轉子偏心、高低壓脹差、主汽閥內外壁溫差、盤車電流等項進行監視,如其中某項參數超過規定值,則立即停止快冷工作。
6實施效果
汽機滑參數打閘,調節級金屬溫度316.4℃,24小時后(鍋爐受熱面烘干后)投入利用鍋爐余熱進行汽缸缸體的快冷方式,至調節級金屬溫度<150℃(本次檢查盤車),快冷結束。自機組打閘至具備盤車停運條件僅歷時4天16小時27分鐘,與3號機組A修從機組打閘至盤車具備停運條件相比(7天21小時40分鐘)節約時間3天5小時13分鐘。由于各監視部位參數安全裕量充裕,機組快冷期間各項參數均未出現異常情況。
參考文獻:
[1]李帥,陳連舉.超超臨界1000MW汽輪機快冷方法應用及研究[J].電力科技與環保,2018,034(002):47-48.
[2]吳昕,李磊,王爭明,等.1000MW汽輪機快速冷卻的應用與分析[J].中國電力,2019,52(02):163-169+176.
[3]張磊,樊希林,劉書元,等.國產660MW機組汽輪機強制快速冷卻技術的應用[J].發電設備,2019,33(4):289-292.
[4]何偉男,王兆彪,吳曉東,等.核電站1000MW汽輪機快速冷卻方案探究[J].熱力透平,2019(4):254-259.
[5]畢治功.汽輪機啟動過程優化分析[J].輕松學電腦,2019,000(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