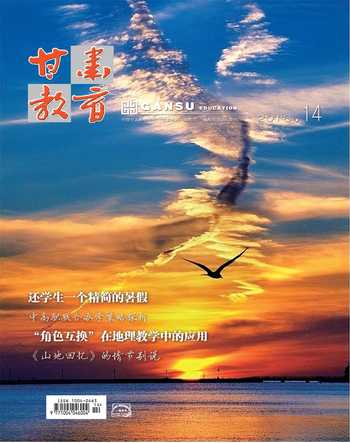系列寫作
霍軍
課堂是教師研究的最大對象。怎么研究課堂,方法千千萬。比如研究課堂細節,就有無限文章可作。這種研究必然體現為種種寫作,或者叫教育敘事。我們在研究教材、課堂方案設計、課堂過程以及課后的反思中,如果都能留下相應的文字,這些文字的寫作就會因為語言的積累和反省變成對今后教學實踐行為最好的提醒和約束,變成了進一步優化了的課堂教學資源。一句話,課堂研究其實應該體現為一系列與課堂教學相關的寫作,并用這種寫作行為指導教師的教學實踐。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經過長期課堂教學研究寫作而形成了“文本解讀寫作——課堂教學設計寫作——課堂案例寫作——課后反思寫作——學生作業收集寫作”的系列“寫編”研究格式,并自己命名為一種實用的“微課題”研究活動。說這是“微課題”,乃是因為這個系列寫作行為是圍繞某一篇具體的課文而展開的。整個系列的研究文章,從教材解讀開始,到收集學生作業(主要是作文)終止,在一個教學時段里,整體地、系統地記錄、觀察和反思自己在一篇課文上的所有教學行為。這樣的研究既具體,又有某種宏觀的價值。筆者曾大力倡導教師的文本解讀能力的強化。說到底,這個系列寫作,就是想要從教師獨立的教材研究能力開始,審查教師自己深入細微的、抓住教材關鍵的教材解讀給自己的備課能夠帶來的啟發,從而使課堂教學產生思維的深度和廣度,不僅更適應學生的學習,而且讓他們確實能夠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知,并通過作業訓練的方式,催生優良的思維,產生自己的作品。
這個微課題研究極為看重教師獨立的教材解讀能力訓練。每篇教材都不缺乏豐富甚至是海量的解讀資料,但是,真正想讓自己的教學擁有高質量的教師,必須明白,自己對教材的“裸讀”——不依賴任何他人解說而只靠自己的學科能力進行的解讀,會讓自己親切可感地抓住教材的靈魂和思維價值。自己解讀中的發現雖然不過是得出跟別人大致相同的關于某個教材內容的基本看法,這篇課文在整個教材系列中的學理體現,也并不由此發生基本的更動,但是,經過教師自己的咀嚼,就能再次體驗到教材知識發現者的創造喜悅和思維樂趣,就會擁有教材學理和文本創造者類似的思想領悟。這與人云亦云地照搬一些解讀意見有天壤之別。經常習慣于自己“裸讀”教材的教師,其實是最急于將自己研讀的細微體驗和創造性發現拿來與他人分享的人。這種情感體驗最有助于教師寫出最有創意和巧思的課堂設計方案。教學當然可以按部就班地開展,步驟齊備,但是“知識灌輸”和“教育”的微妙差別,就在于前者是照本宣科地“轉運”,后者是人與人的對話,是教師和學生借助某一知識片段和學理內容或精彩的文本藝術而進行的生命和生命的相逢與融合。如果非要說應試教學與素質教育有什么差別,筆者認為它們的不同并不完全在于“教什么”,而正在于“怎么教”的問題。怎么教才好?筆者認為,在具體的教學行為中,教師應用自己獨立思考獲得的教學內容的再發現和充滿個性的生發,去設計屬于自己的教學形式。這樣的教學形式必定因為傾注了自己的個性生命而成為在課堂上啟迪學生用生命熱情學習的良助。
同樣,由此產生的課堂進程就會有很多沿著學理和文本展開的激活思想的講授與對話,就會有新鮮豐富的生成,就有了師生共赴真理時的各種思維火花閃現。必須記錄這樣的課堂,哪怕是一個片段,也必定有切片觀察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會發現,課堂總是有一些小小的細節里邊體現著推動教學的奧秘,它們不是產生于案頭冥想,而是來自透徹鉆研教材內容進行的精心設計,與教學對象發生活生生的現場交流時產生的理解妙境。這樣的細節才是教師繼續備課的根本依據,才是進一步找到師生交流最佳契機的竅門。而正是這樣一些借助被師生共同解析、梳理、揣摩和玩味的教學內容,才會真正啟迪人的心靈和精神世界,助長學生的智慧,促進師生共同在課堂上成長。最后,必會呈現為學生得到新的呼吸之后完成的個人作品——作業。比如,有創意的作文,有全新角度的闡釋,能結合自身生活體驗的鮮活敘述和議論等等。而把這樣的作業收集起來,與整個教學活動中誕生的其他教師作品(文本解讀、教學設計和教學案例)放在一塊兒分析比照,這時候寫出的教學反思,立足課堂,有本可依,研究具體,脈絡清晰。這樣構成的一個“教學標本”才足以產生推動下一步教學活動的力量。
編輯:謝穎麗